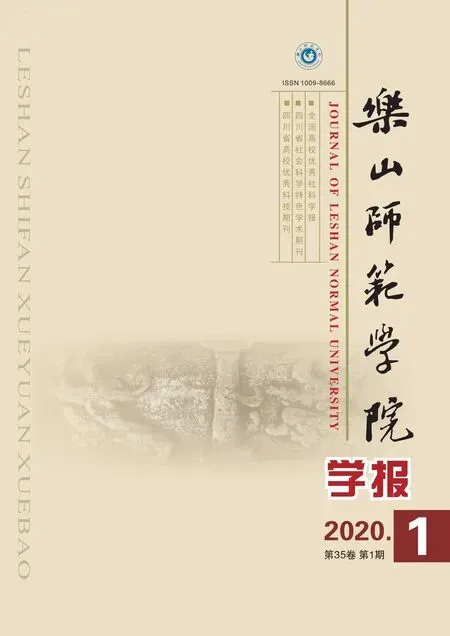福克納象征創作的隱匿性研究
周 博,王夢圓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威廉·福克納作為20世紀美國南方文學乃至西方現代文學界的一代大師,“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而且幾乎在其每一部新作中,福克納都在越來越深刻地挖究人的內心世界,人的偉大及自我犧牲精神……”[1]譯序5。在文學創作生涯中,他積極吸收借鑒馬克·吐溫、霍桑、托爾斯泰等大師的創作理念與藝術精髓,并通過獨特的藝術稟賦和冒險精神在自己的文學故事中進行再創造、再探索。其中,作為大多數創作者在文學敘事中慣用的象征技巧,福克納也毫無例外的從中尋找到奧義。然而,針對福克納創作中具有的象征性研究,已有的研究者多關注于小說篇名和文本故事中所體現出的《圣經》原型意象,以及自然事物所具有的多義象征解讀,忽視了對福克納象征創作的歷史關照,以及這一系列象征創作背后存在的隱匿性特質。
一、象征主義的學徒身份
盡管福克納在眾多文學作品中采用了象征創作,但其本人卻從未承認這一創作屬于刻意而為,然而根據1987年亞歷山大·馬歇爾三世在其文章中的論述顯示,“在1919年的8月6日,威廉·福克納就第一次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了文學作品《牧神的午后》,這是首威廉·福克納從法國象征主義作家斯特芳·馬拉美杰出的田園詩牧歌中得到借鑒而完成的詩作。”[2]389并且,“在接下來超過十個月的時間里,福克納又在《密西西比人》雜志上發表了13首詩,其中1首是馬拉美詩歌的修正版本,4首從保爾·魏爾倫作品中翻譯或者改編而來,另外還有8首本人的原創詩,它們都清楚地帶有象征主義的印記。”[2]389亞歷山大·馬歇爾三世在同篇文章中還提到,“任何對于文學影響的討論都應盡可能復雜多樣一些,并且當處理像福克納這種逃避和不表意見的作家來說甚至還應該關注更多。”[2]389除此之外,也有文獻表明:“我們知道在他最初‘學徒身份’已經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福克納仍然在讀象征主義的系列作品。他把魏爾倫和拉弗格稱作‘老朋友’,并且一次又一次的返回到他們的作品之中。”[3]217
除了這些指證以外,福克納也常會遭遇一些讀者或者研究者對于他作品中暗含的象征意象是否是其“精心安排”的疑問。“在維吉尼亞大學的一次采訪中,福克納被問及他書中(《喧嘩與騷動》)眾多最令人困惑問題中的一個。然而在他回答本科生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當他進行寫作時他并有在他的創造性驅動力中完全地運用象征暗示。”[4]55當時提問與對答的情景也被記錄了下來:
提問者:福克納先生,我非常感興趣您在《喧嘩與騷動》這部小說中的象征,并且我不能確切地指出在昆丁部分對于影子象征的重要意義。在小說中它被一次又一次的提及:他踩在影子上,影子在他前面晃動,影子經常在他后面尾隨。那么,影子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福克納:這并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象征。我只能說這些影子保持在他腦中如此之多是預示著昆丁自己的死亡,他僅僅是——死亡就在那,我將更靠近它還是更遠離它的問題,我不會逃避它,并且我將接受它或者我會把他延遲到下星期五。我認為在創作中它并沒有任何必須這樣呈現的緣由。[5]235
不管福克納對《喧嘩與騷動》中“影子”意象的象征意蘊含糊其辭,還是他“絕不寫或者說任何關于他以象征主義者姿態寫過與此相關的文學類型與內容”[2]390,“我們也有證據表明他讀過西蒙斯·阿瑟的《象征主義的文學運動》一書,這本著作包含了由魏爾倫和馬拉美翻譯的作品(其中一些很接近福克納本人的翻譯),并且還詮釋了許多生活方式和這些詩歌的理論。”[6]247福克納顯然從這本象征主義的核心著作中汲取了關于象征方面的重要寫作技巧,因為亞歷山大·馬歇爾三世在文章中指出:“福克納通過西蒙斯和那些詩作,對于象征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于那些帶有抒情味的、精巧的、常常是共美的語言雕像,有了充分的接觸。”[2]390而就這一情況,也有研究者撰文論及,“一個作家總是絕對貪婪的,他沒有任何規范的道德,他總是從任何資源中竊取。他是如此的繁忙于竊取和使用它們,以至于他自己可能也絕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從哪里得來……他被他曾經閱讀過的每一個字詞影響。并且他是如此的忙于書寫以至于都沒有時間停下來,并且說,‘現在的這一切我都是從哪里得來?’但不可否認,他確實從一些地方竊取而來。”[3]128換句話說,盡管威廉·福克納本人不曾承認,但這一系列資料恰恰印證了他象征創作中具有的隱匿性。
事實上,作為一種創作方式,象征創作至少應該包含對象征技巧與象征主義的雙重吸納。若為二者進行同異探析,則可知在文學世界中,通常把象征技巧理解為文學創作者以此物指他意的創作技巧,它存在極大的隨意性,并且也理所當然的成為象征主義這一文學流派的核心概念。但通過辨析,二者又存在不一樣的地方。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在其《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說:“曾有人用象征一詞來指語言符號,或者更確切的說,來指我們叫做能指的東西。我們不便接受這個詞……。象征的特點是:它永遠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間有一種自然聯系的根基。象征法律的天平就不能隨便用什么東西,例如一輛車來代替。”[7]3顯然,索緒爾是從語言符號的角度來強調象征具有的一種理據性。而哲學家黑格爾也曾在其《美學》第二卷中論述到:“象征首先是一種符號。不過在單純的符號里,意義和它的表現的聯系是一種完全任意構成的拼湊……。作為象征來用的符號是另一種……象征所要使人意識到的卻不是它本身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義。”[7]5那么,由此可發現,以上二人都主要是把象征理解為一種符號和技法,只是他們尤其強調象征背后存在的理據性與普遍性,而這又恰恰與我們研究象征意蘊問題的核心目標相吻合,即應透過表面的基本人物和故事來挖掘其背后蘊含的深層理據和普遍指事性,它更多關注于如何呈現的問題。當對比于19世紀中葉在法國開始的象征主義文學流派時,可發現二者存在明顯不同。在象征主義者看來,現實世界是痛苦虛幻的,而內心的“另一個世界”才是真的、美的,外界的事物與人的內心可相互感應,并且詩歌的任務就是通過象征、暗示來連接兩個世界,從而誘發讀者的想象、聯想,以領悟作者的思緒。象征主義文學更多地關注于通過象征呈現何種實質內容的問題,它與關注于呈現方式的象征技巧存在著明顯差異。
然而,不管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交叉和差異,這種區分顯然不是給福克納象征創作確立固定的模式,而恰恰為福納象征創作具有的隱匿性特征找到了更多空間,并且基于“福克納對于自己所欠象征主義者的恩情的性質和范圍,卻從未有過只言片語的情況。……我們必須回到他讀過的讀物和他改編、翻譯的作品中去”[2]390。除此之外,從其后期主要的文學作品中尋找到關于象征創作的客觀事實也顯得更為重要。
二、象征創作的文本構建
論述福克納在眾多小說中對自然意象、動物意象以及人物故事中精心安排的象征,能更具說服力地表明他象征創作隱匿性的確實存在。因為,“人們必須記住,象征主義所追求的不是詳盡的敘述,而是暗示,是在讀者心中喚起與直接經歷可比較的感知。”[8]90
在具體創作中,“1922年,福克納寫了一個短篇《小山》(TheHill),此文預示了他在未來的作品中,一定會運用到他所接受的象征主義的知識。”[2]392并且約瑟夫·布羅特納在其大量的傳記文學中指出,“在其早期的基本形式中,有關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風格的這樣一個中心事實,即他在一種現實主義的框架中,運用詩的語言去構思和寫作,這種現實主義的框架使象征主義的技巧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9]332另外,福克納對小說人物慣用非常具有特征性的臉部雕像,從而呈現出小說人物的器官特征與性情,比如“在《圣地》中,失去人性的鮑樸埃的眼睛,‘看起來有點像兩個橡皮瘤’。……在《押沙龍,押沙龍!》中,托馬斯的眼睛‘看起來像只破盤子的碎片’,使人憶起了他真破碎的帝王夢。……而在《小村》中的瓦爾納有張嘴巴,就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一樣’。”[8]90這些以物比物的象征都不僅使得小說中的人物面貌活靈活現,并且特定的表達也蘊含了每個人物獨特的氣質與命運。
在《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曾就小說第四部分的女傭迪爾西這一角色做過具有特殊意味的論述,他說:“她代表未來,她將站在傾圮的廢墟上,像一座傾斜的煙囪,高傲、堅強、不屈不撓。”[10]18這就已經使迪爾西從作為一個小說角色到作為黑人女性代表所具有的獨特精神表達了出來。另外,研究者李文俊也在其著作中指出,“福克納后來說,他足足用了一個多月才寫下開首的那句:‘這一天在蕭瑟與寒冷中破曉了。’故事發生的這一天是復活節,福克納單單選擇這一天顯然有其象征意義。”[10]18那這又象征著什么呢?“福克納認為,能頑強地在美國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必定終究是普通勞動者。”[10]18-19這看似只是對眾多生存群體所面臨現狀的分析,實則卻隱匿地表明了福克納對美國南方社會潛藏社會弊病的揭露,尤其是針對于像康普森家族這樣的社會群體。
在《我彌留之際》中,福克納“通過主人公——在這里是一個群體、一個家庭——的歷險,探討人類種種經驗的一出悲喜劇。外國評論家也普遍認為應把此書看成是關于人類忍受能力的一個原始寓言,是我們這個復雜得多的社會的有代表意義的縮影。”[10]22在《村子》(也譯為《小村》)中,福克納又通過塑造兩類典型的人物來“象征性地預告了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戰勝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資產階級將取代地主階級。”[1]譯序6而在其后期創作的《熊》中,熊“已經成了人必須與之搏斗的‘命運’的一個象征,同時又是人必須依賴才能生存與發展的‘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11]譯序6除以上這些外,小說《八月之光》的篇名都具有深刻的暗含意味,即“象征著人類將賴以‘永垂不朽’的古今綿延的‘人類昔日的榮耀’。”[12]譯序6等等。
這一系列的象征案例,都可確鑿而翔實地佐證福克納在文學創作中的確廣泛運用了象征技巧,或者說吸收借鑒了象征主義創作的某些主張,只是他本人并不希望別人誤以為他的文學創作是依據一些他人的理論而來,或者模仿了前人的一些創作技巧。因為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談及:“作家假如要追求技巧,那還是干脆去做外科醫生,去做泥水匠吧。要寫出作品來,沒有什么刻板的辦法,沒有捷徑可走。年輕作家要是依據一套理論去搞創作,那他就是傻瓜。應該自己去鉆,從自己的錯誤中去吸取教益。人只有從錯誤中才能學到東西。在優秀的藝術家看來,能夠給他以指點的高明人,世界上是沒有的。他對老作家盡管欽佩得五體投地。可還是一心想要勝過老作家。”[13]421由此可以看到,盡管福克納不曾對那些影響過他早期創作的象征主義者表達過只言片語的恩情,也不承認他諸多的象征書寫屬于“精心安排”,但他作品中不可否認地存在包含自然意象、動物意象以及人物故事意象在內的隱匿象征書寫。
三、隱匿象征的多維表達
福克納小說中眾多意象及人物故事的重復與糾葛,致使原本的單一事物隨之產生多維的象征色彩,繼而推動小說的整體思想實現多方位的立體建構。
就《喧嘩與騷動》一書,無論是自然意象還是人物象征都具有極其突出的多維表達。對于自然意象,福克納在班吉部分、昆丁部分都多次運用到“鏡子”“月光”“火”“陰影”“鐘表”等來表達某種程度上的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拿班吉來說,由于鏡中之物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對于完全相信鏡中之物即為真實存在的他,勢必會在認知事物方面產生更多的可能性,從而產生超越于正常人理解范圍的理念世界。而對于這一問題也有研究者提出,“一個鏡子僅僅是一些事物或者一些人的反映,但是它僅僅只作為一種反映,而非一個真實的意象。”[4]49可是,恰恰是這種反映讓人能夠去考量,經過反應前后的事物產生了怎樣的差別,并且真實存在的意象又是否是絕對的真實。另外,在《喧嘩與騷動》這部小說中極具特色的人物故事糾葛,也使得福克納隱匿象征創作具有的多維性得到呈現,突出表現為凱蒂和班吉、班吉和杰森、昆丁和凱蒂的關系象征中。對于凱蒂與班吉,由于康普森夫人在照管孩子方面沒有充分表現出母親該有的責任和義務,因此作為班吉姐姐的凱蒂,在日常生活中對班吉多有照料,甚至有時已經完全展現出一種慈母式的關懷,以致班吉對姐姐產生特殊的情感傾向,并且當姐姐失身時他能即刻聞到不一樣的氣味,表現出超越一般姐弟情感的依賴和反映,在姐弟二人之間產生了一種更像母子感情的象征意味。在班吉與杰森的關系中,二人最為突出的象征糾葛主要體現在杰森對班吉的生理閹割一事。按照常理,癡傻的班吉盡管很多時候行為不能自控,但是我們不應該據此就絕對否認他完全沒有生理需求,所以杰森將其生理閹割的行為恰恰暗含兄弟之間對親情善念的“閹割”,而這又讓我們反思一個生命個體,在人性善念與親情關系的把握方面可能出現的模糊尺度,以及社會異化對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昆丁與凱蒂的關系中,由于昆丁對凱蒂具有超出兄妹的情感,所以當昆丁得知凱蒂懷孕后,這位康普森家族的繼承人內心痛苦萬分,而后又因為一系列的現實事件而投河自盡,即使從哈佛獲取的知識也無法將他拯救,而凱蒂的女兒最后取名為小昆丁同樣深藏了某種特殊關系與情感。由此可見,這一系列的關系糾葛,都使得事實陳述背后隱含的象征色彩變得撲朔迷離。
事實上,無論象征是作為一種創作技巧還是作為一種文學流派的核心概念,它最基本的旨歸都應該是以一種事物來指代另一種事物,這和中國“賦比興”中的“比”有某種相似性,即以彼物比此物,或為某種情感寄托,或為更加清晰地表明某種心境,以及事物的特征與發展趨向。那么,伴隨著象征創作的隱匿特效,創作者隨之具有足夠的創作空間和表達方式,文學藝術的受眾者也同樣會從一個自然事物、一個人物類型或一種話語體系中產生各自不一的認知與理解。拿如何在文學作品中呈現一個“最理想的女性”這一問題來說,福克納本人就給出了相當具有象征意味的回答。他說:“說實在的,我并不能描述她頭發的顏色,眼睛的顏色,因為一旦描述那么她也就出現某種消亡,一個理想的女性應該被每個男人頭腦中的一個字詞,一個句子或者她手腕手臂的形狀來喚醒。即使是那些最美妙的描述也是有所保留的,你最好是舉起手來,并且走進樹枝的陰影之下,從而讓思維去創造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3]127-128換句話說,事物的真相與美丑也并不是通過語言的描繪就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真實。相反,運用更大程度的聯覺、想象或者象征卻使得藝術創造具有更大的描寫范圍和創作空間,從而致使包含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要素”的文學世界形成一個不斷拓展的藝術整體。
毋庸置疑,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可能不去運用一切他可以運用于創作的經驗和技巧,福克納在一次采訪錄中也親口承認:“藝術家是由惡魔所驅使的生物,他不知道惡魔為什么選中了他,而且素常他也忙得無暇顧及其原因。他完全是超道德的,因為為了完成作品,他將向任何人和每一個人進行搶劫、借用、祈求或者偷竊。”[13]416因此,盡管福克納本人否認或者在回答一些問題時,暗示他創作過程中出現的所有象征和意象都不是刻意而為、不是出于一種有意識的方法和策略驅使,僅僅是在創作時本能地進行了意象的靈活投入,這些都恰恰表明其象征創作存在的極大隱匿性,只是作家并沒有把它們歸結為象征創作的范疇。不管作家承認與否,隱匿性特質的確擴大了作家的創作空間,并且也使得一種意象所表達的意指更加多維。
作為一個在文學創作方面極具創新意識的作家,福克納必然不會使其創作落入某種理論或者某種主張的轄囿之中。創作過程中運用到的象征技巧與象征意識,作家更不會簡單的將其顯露,這也就使得福克納象征創作的隱匿性具有研究價值,繼而生發讀者在文學和審美意義層面的思考。
事實上,象征這一概念本來就暗含著極大的不確定性,而福克納從未承認這一創作技巧的精心安排,恰恰表明作家想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增加更寬泛的指事范圍和意蘊表達。對于文本來說,極具隱晦的象征使《喧嘩與騷動》中失去獨立自我身份的凱蒂更為牽動人心,使小說《熊》中的熊暗含人與動物關系的相依相搏,人與自然及動物的關系并非狹義的人為決定論,等等。回到象征本源意味的考量還可以發現,福克納隱匿的象征創作更有力地彰顯了美國南方社會的生存現狀,以及人類在面對現實世界時所表現出的犧牲精神,從而讓作家的文學思想不再局限于一個福克納化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而是關懷整個文學再創造以及人類命運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