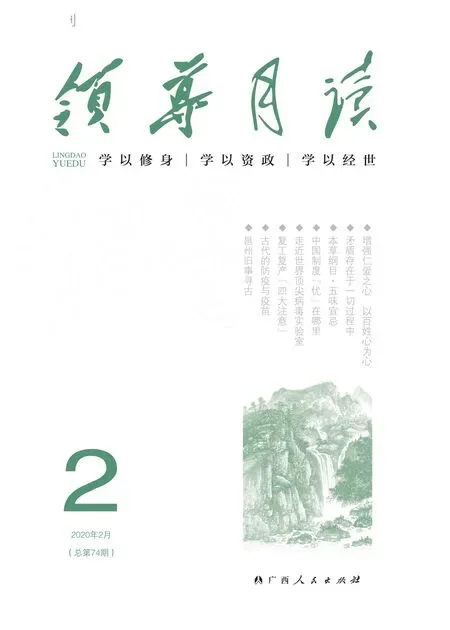用觀點來評判觀點
馬克思
近來,鮑威爾先生把絕對知識改名為批判,而給自我意識的規定性換上了一個聽起來更具有世俗意味的名字——觀點。在《軼文集》中兩個名字仍然并用,而觀點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識的規定性來解釋的。
因為“宗教世界作為宗教世界”只是作為自我意識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職業的神學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想到,竟然有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意識和存在是不同的,而當我只是揚棄了這個世界的思想存在,即這個世界作為范疇、作為觀點的存在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我改變了我自己的主觀意識而并沒有用真正對象性的方式改變對象性現實,即并沒有改變我自己的對象性現實和其他人的對象性現實的時候,這個世界仍然還像往昔一樣繼續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維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在批判那里作為實踐和理論的同樣神秘的同一重復著。因此,批判怒氣沖沖地反對那種還想同理論有所區別的實踐,同時也反對那種還想同把某一特定范疇變成“自我意識的無限普遍性”的做法有所區別的理論。批判本身的理論僅限于把一切確定的東西(如國家、私有財產等)宣布為自我意識的無限普遍性的對立物,因而也就把它們宣布為微不足道的東西。其實恰好相反,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國家、私有財產等怎樣把人變為抽象概念,或者它們怎樣成為抽象的人的產物,而不是成為單個的、具體的人的現實。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說黑格爾的《現象學》盡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還是在許多方面提供了真實地評述人的關系的要素,那么鮑威爾先生及其伙伴卻相反,他們只是提供了一幅毫無內容的漫畫,這幅漫畫只是滿足于從某種精神產物中或從現實的關系和運動中擷取一種規定性,把這種規定性變為思想規定性,變為范疇,并用這個范疇充當產物、關系或運動的觀點,以便能夠以老成練達的姿態、揚揚得意的神氣從抽象概念、普遍范疇、普遍自我意識的觀點,傲然睨視這種規定性。
在魯道夫看來,所有的人不是持善的觀點,就是持惡的觀點,并且對所有的人都要按照這兩個不變的觀念來進行評價;同樣,在鮑威爾先生及其伙伴看來,所有的人不是持批判的觀點,就是持群眾的觀點。但是魯道夫和鮑威爾及其伙伴都把現實的人變成了抽象的觀點。
【題解】
《神圣家族》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第一部著作,其中蘊含著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觀點和論述,本文摘標題為編者所擬。該書最初的書名是《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其主旨是針對青年黑格爾派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進行針對性、回應性的論戰,后來馬克思加上了“神圣家族”幾個字并以此來諷喻鮑威爾及其同道。
選文作為全書的結尾,對鮑威爾及其伙伴們思辨觀點的唯心主義本質進行了辛辣的批判:他們鼓吹以自我意識為基礎的主觀唯心主義,宣稱世界歷史進程中唯一積極因素是他們的理論活動;他們把改造社會的事業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認為純粹的思想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他們堅持敵視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稱群眾為“精神的敵人”。顯然,對鮑威爾及其伙伴們而言,國家、私有財產、法、宗教這些源于實踐的觀念范疇已經被抽象為封閉的概念或觀點,走向了一種“自我意識的無限普遍性”。
然而,世界終歸是實踐的,是要歸結于對象性的感性活動的。愈是將觀念絕對化、神圣化,這些觀念就愈發遠離歷史的真相和人自身,也就愈發與闡明歷史真實過程的歷史唯物主義區別開來。倒退為對現實矛盾關系與運動視而不見的自我循環、自我辯護的精神游戲也只能是魯道夫和鮑威爾及其伙伴的理論宿命。在此意義上,和黑格爾相比,他們無疑沒有取得絲毫進展,同時也表明,再高深、再神秘、再精巧的理論和觀念,一旦脫離實際,也只會一文不值。(古 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