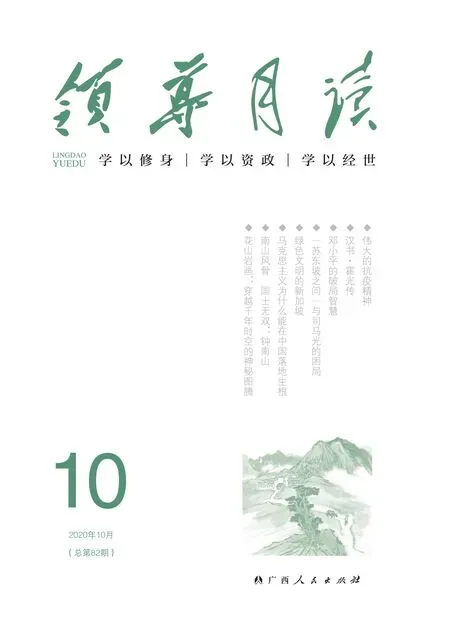“蘇東坡之問”與司馬光的困局
劉后濱
蘇軾(號東坡居士)以自擬策試考題的形式,提出了選官制度中如何做到人與法并重的問題,題為《私試策問·人與法并用》。概括說,就是選官用人過程中如何化解人情干擾與規則約束二者的矛盾,既要保證用人部門長官具有自主選官權,又要防止標準不統一和規則不嚴密而導致的恣擅與徇私。這個問題由來已久,然而蘇軾概括得最為到位,故可稱之為“蘇東坡之問”。
在蘇軾的理解中,唐朝及以前的選官制度,既無禮部“糊名易書之法”,亦未有吏部“長守不易之格”,部門的長官可以按照各自的需要和獨立的判斷來選拔官員。這個判斷未必完全客觀,但是在唐朝前期,確實還沒有出現宋代那種嚴格按照資歷和量化指標來任用官員的情況。到蘇軾的時代,選官制度已經非常完備,但是隨著制度的完備又出現了新的困局。
一個人能否做官,能夠做什么級別的官,不由哪個人說了算,而是要通過嚴格的資歷體系中各項指標的計算得出來的。這個資歷體系,由出身、任職經歷、考績、舉主、年資等因素構成,而且都是有檔案可查的。所以,蘇軾提出了任人與任法的兩難抉擇問題:既要保障銓選部門尤其是用人部門的長官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使選官用人權,又要避免請謁公行、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既要保障選官政務中的機會公平,規避人情干擾,又要保證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兼顧效率。
蘇軾提出,此事應該是能夠找到折中辦法的。我們不知道他想到的辦法到底是什么,但是蘇軾所尊崇的司馬光卻間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資治通鑒》記載,崔祐甫在唐德宗新即位為代宗守喪而“居諒陰”的情況下,取代常袞擔任宰相,在官員任用方面一改常袞收緊的做法,將此前滯留下來的大量等候任命的官員快速加以任用,不到兩百日的時間里,進行了八百人次的人事變動,進而給反對者制造了任人唯親的口實。
在唐德宗為何“多涉親故”的追問下,崔祐甫的回答顯得理直氣壯:既然陛下委任我擔任宰相,令我選擇百官,那我自然要認真對待、謹慎負責,因此只能在有過接觸的人群中加以選擇,以保證諳熟其才能與德行。這個回答得到了唐德宗的理解。
問題是,有選官權的人在選任官員的時候,是否只能在熟識的人中間加以選擇方能保證質量呢?接下來,全國的中低級官員都要由尚書吏部任命,高級或職位重要的一些中低級官員都由宰相和皇帝親自任命,選官權如此集中,有選官權的人又怎么可能對全國的候選人都熟識呢?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直抵“蘇東坡之問”。
無疑,這種“任人”而不是“任法”的做法,確實很容易引起“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司馬光對選官用人給予了突出觀注,并站在治國理政的高度以“臣光曰”的形式發表了一段評論:一方面認為不能因為是親故就不任用,如此亦非出于公心;另一方面更不認同崔祐甫的做法,僅憑一人之力,熟識的人總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于公心,也不可能沒有遺漏。
他提出的辦法是,“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己不置毫發之私于其間”。這是司馬光有關選官用人問題論述中最切近制度設計的議論,也是對“蘇東坡之問”最接近出口的一個回答。這樣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擾,又可免于越來越繁密的規則的束縛。但是,這個議論畢竟還是停留在理念上,在制度設計和具體政策措施中如何做到“舉之以眾,取之以公”,這就不是生活在遙遠北宋時代的司馬光和蘇軾們能夠解決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