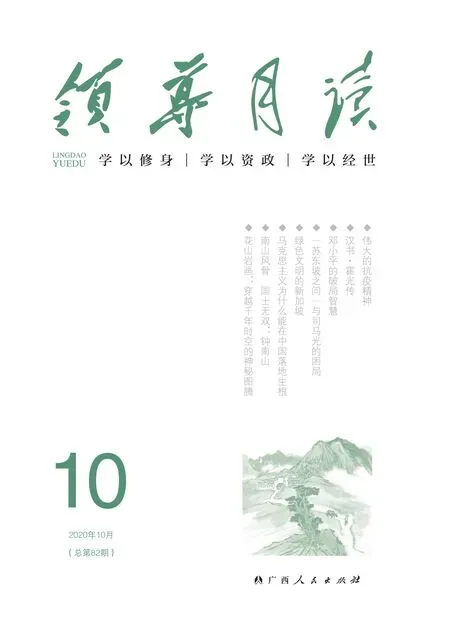扁擔:挑起生活的責任
黃孝紀
村莊無家不用竹,村人無一不吃筍。只是在我的家鄉八公分村,不曾有一片搖曳生姿、高聳云天的南竹林,是我一直深以為憾的事情。
并非這一方鄉土不適宜南竹的生長。江岸溪邊,山林野外,各種野竹恣意生長,十分茂盛。每年出春筍,家家戶戶的大人孩子,常常每天肩扛手提一籃筐滿滿的竹筍從周邊的山野下來。這些筍子都有手指粗,尺許長。不同的時間段,不同的地點,筍的品種有別,形態、色澤明顯不同。我們通常能叫出名字的有早筍、紅花筍、阿打秧、尖尾巴筍、麻子筍諸種。吃筍子,曬干筍子,是這個時節家鄉的日常景象。
而就在我們村莊二三里外的周邊幾個小村,朽木溪、臼林、龍形上、蓮塘、長洲頭,村后村旁無不有一片蔚然成林的南竹。那些比我們的胳膊和腿還粗大的南竹,滾圓筆直,碧綠光滑,竹節無數,一桿桿,密密麻麻,直沖云霄,綠葉如云似蓋,實在美得秀麗,美得壯觀!那里面的大筍,更是長得像碩大的水牛角,黑亮亮,尖突突,到處都是,曾勾起我們幾多眼饞。
南竹生筍,筍又成竹,循環往復。一批一批的老竹砍伐了,在篾匠的巧手之下,做成籮、筐、簍、篩、籠、勺、筒、升、篙、椅、床……種種日常竹器。自然,也包括無家不有的扁擔。
舊時的故鄉,每戶人家都會有幾條扁擔。扁擔的數量與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家庭大,扁擔也就多。扁擔形如細長的柳葉,中間寬,兩端略尖。新買的扁擔,呈現綠竹的本色,不少村人常用鐵絲燒紅,在其兩端朝上的一面燙出名字和記號,以示區別。扁擔用久了,與肩部接觸的地方油光發亮,色澤也由綠轉黃,最后變得橙紅而老舊。
扁擔的兩端可套棕繩或麻繩,也有的不套。不套者,用來挑谷籮、米籮、炭籮、油簍這類本身帶有長繩索的器物。套者,又叫鉤掛扁擔,也叫鉤擔,乃因所套繩索下端系了一副鐵鉤子,用于挑竹篩、竹籃、水桶、潲桶、淤桶……因鐵鉤子常年與所挑器物摩擦,鉤內磨得異常光亮。
山村之人,從小就會挑擔。扯豬草、割葉、撿柴、挑水、殺禾、挖紅薯、摘油茶果,都要用到扁擔。至于成年勞動力,每天干活不是挑籮筐、篩子、淤桶,就是扛齒鋤、板鋤、犁耙,一年四季,無非就是圍繞著田土山嶺打轉轉,謀生計。
挑擔子也有技巧。我小時候剛學挑擔那會兒,經常到井邊挑水,沿著青石板路,上臺階,穿巷子,進屋,一路都不會換肩。沉重的擔子總是壓著一邊肩膀,痛得難受,而另一邊不習慣挑。如此,很是吃力,每走一小段路就得放下來歇歇。更有甚者,挑擔時,我兩手不會壓扁擔,常將伸張的雙臂從身后反轉著搭在扁擔上,勾頭耷腦,跌跌撞撞,樣子十分狼狽。兩只木桶里的水,晃蕩不停,濺一路水漬,等到了灶屋的水缸邊,已所剩不多。村人將這樣子挑擔,叫作挑猴子擔,是常要受到取笑和奚落的。
不過,擔子挑多了,經驗就漸漸摸索出來了。扁擔不能選硬翹翹的,得富有彈性。挑擔的繩索不能過長,過長則所挑之物容易觸底,上坡上臺階時幾乎會擱在地面上,很麻煩;也不能過短,過短則沉,更費力。走長路要常交替換肩,換肩時,腳步暫停,雙掌朝上用力一托扁擔,身子一側扭,就能輕松換過來,繼續前行。走的步伐不能太硬,硬則沉,沉則吃力。需走快步,腳下生風,這樣,兩端的擔子一彈一跳,彈性十足,挑起來就輕松多了。當然,所有這些技巧的前提是,所挑之物不能貪多過沉,需量力而行。母親常說:“輕快輕快,挑輕一點才走得快。多挑幾趟,人不吃虧,挑得還多。”確是經驗之談。
挑擔走長路也是培養耐力和韌性的過程。我年少時從田里挑谷子回家,或者自山嶺挑油茶胚到曬坪,路途很長,擔子很重,感覺無比艱難,腰酸腿痛。即便如此,我總是默默忍受,用目光在前路給自己設定一個又一個短期目標,心里想,只要到了下一個目標,就放下來歇歇。可是過了這個目標,又咬咬牙,給自己鼓勁,到下一個再歇。這樣一而再再而三,一路堅持下來,最終抵達,常令自己都感到驚異。于今想來,人生路上取得成果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條扁擔能用上多年。用習慣了,用久了,人與扁擔之間就相互熟悉了對方的脾性,成了伙伴,于晴雨風雪之中,年復一年,共同挑起生活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