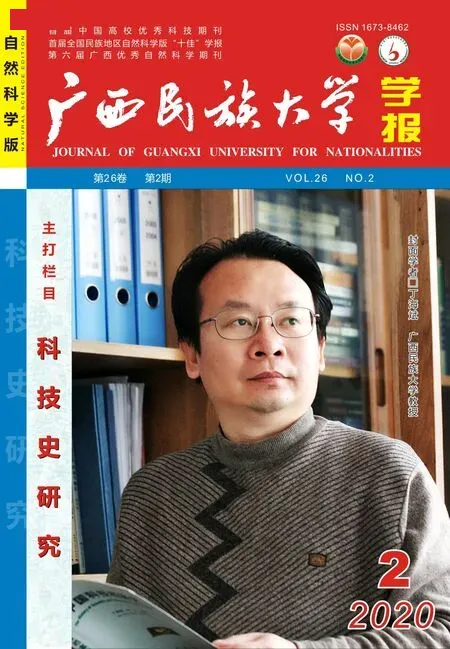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建設中的問題與對策*
田 宇梁宏章
(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廣西 南寧 530028)
0 引言
2004年,經國務院批準,中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根據《公約》第三章第十二條:“為了使其領土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確認以便加以保護,各締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擬訂一份或數份關于這類遺產的清單,并應定期加以更新.”[1]這里所指的清單,在中國是指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①以下如無特殊情況,簡稱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經過十多來年的實踐摸索,廣西也基本構建起符合區情的非遺名錄體系.如今,非遺工作已全面進入“以能力建設為核心,鞏固搶救保護成果,提高保護傳承水平,推動非遺事業可持續發展”②2017年文化部原副部長項兆倫同志在全國“非遺”保護工作培訓班上的講話.的后申遺時代.在此背景下,通過對現有名錄體系系統的梳理和反思,并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進行補充和完善,是進一步做好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前提.
1 廣西非遺名錄體系建設的意義
廣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區,各民族在長期的生存和發展中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非遺資源.這些珍貴的遺產是各族人民勤勞智慧的象征,是維系民族情感的重要紐帶,也是激勵廣西全區各族人民團結奮進的寶貴精神財富,且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學、藝術和科學價值.截至2019年12月底,廣西共有國家級非遺52項,自治區級非遺762項,市級非遺1406項,縣級非遺4052項.實踐證明,名錄制度對遺產項目及所在社區都將產生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1.1 搶救、挖掘與保護非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非遺主要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是各民族千百年來在歷史進程中形成地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系.[2]然而,隨著全球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傳統的社會結構、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生境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面臨“人亡藝亡”的局面,一些依靠口傳心授和行為傳承的非遺正在不斷消失.因此,在非遺工作的早期階段,中國秉承“瀕危優先”的保護理念,將一大批亟須保護的傳統文化納入非遺名錄中.短短十多來年,通過政府、專家、社區民眾等群體的共同努力,廣西也構建起完備的名錄體系.“非遺”從一個陌生、新鮮的外來詞匯變成了受社會關注、認可的熱門文化事項.實踐證明,政府主導下采取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等措施對于非遺的可持續發展是行之有效的.名錄體系的建構無疑為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的搶救和復興豎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1.2 消解了社會長期以來在傳統文化認識上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
長期以來,我們對傳統文化一直存在簡單、粗暴的二元劃分誤區,即官方的與民間的、精英的與大眾的、精華的與糟粕的、科學的與愚昧的,等等.甚至不少與宗教相關的文化事項被貼上“封建迷信”等污名化的標簽,一度被禁止.這種狹隘的文化觀認為,只有官方的、精英的才值得被保護和傳承,而普通民眾的文化是粗俗的、底層的,必須經過改造才能進入國家管理的場所,成為國家認可的文化.[3]非遺的理念和內在機制正是對這一狹隘文化觀的反思與批判.通過名錄建設,大量原本不被認可的民族、民間文化得以正名,并且經政府批準而以此進入官方的文化系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的桂劇、壯劇、邕劇、彩調、桂南采茶戲等地方戲劇得以與京劇、昆曲等,壯族織錦技藝與云錦織造技藝、蘇繡、蜀繡等一道被列為國家級非遺項目.曾經一度被禁止的毛南族肥套、京族哈節、壯族三月三等與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一道被列為國家級民俗類非遺項目,成為今天促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文化名片.
將遺產申報及其進入名錄體系的過程,也正是對傳統文化的再研究、再認識、再理解,最終實現文化自覺.高丙中先生認為,它開啟了新的社會進程,以文化共生的生態觀念和相互承認的文化機制終結中國近百年的“文化革命”.[4]
1.3 使非遺保護更為規范、科學、有序
中國在名錄設計上實行的是國家、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自上而下的四級名錄體系的架構.而在申報實踐中,中國施行的是自下而上的申報制度,即由縣級到市級,市級到自治區級,再由自治區級申報國家級.首先,它保障了不同民族或族群都有申報遺產列入名錄的平等機會和權利.申報主體或群體可以從自身文化中選擇代表性的項目進行申報,由此保證眾多民族文化能得到相對平衡的申報與保護.[5]其次,通過申報、評審、公示、申述、復議、公布等一系列規范的程序,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申報的規范性、科學性、公正性.這樣的制度安排,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對非遺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證明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1.4 為各民族提供了平等、共享的交流平臺
非遺名錄的內在機制強調的是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它倡導不用單一或純技術的價值標準對多元文化進行評判.而文化多樣性正是人類創造力的源泉.如前所述,各民族都有將自身遺產申報并被列入名錄的平等機會和權利.名錄構建優先考慮的是該文化事項是否代表了特定族群的文化認同和該群體是否愿意被這樣的文化事項所代表.[6]遺產進入名錄的過程,是將地方或族群代表性的文化放置于全社會關注的視域和國家認可的文化體系中各安其位,也正是實現“私權”向“公權”讓渡的共享過程.[3]因此,名錄體系也為廣西各民族提供了一個平等、共享的交流平臺,以達到學者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目的.[7]
1.5 搭建起中國與東盟文化交流的橋梁,為實現廣西文化強區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持
廣西地處中國南疆,有三市八縣與越南接壤,陸地邊境線長1000多千米.不少民族與東盟國家的民族同根同源,他們在語言、服飾、生產生活方式、習俗等方面十分接近.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共有55項自治區級非遺屬于跨國、跨境共享項目,如京族哈節、獨弦琴藝術、瑤族服飾、壯族儂峒節等.這些跨國共享非遺在國家重大戰略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和重要作用.以非遺名錄為載體,搭建起中國與東盟文化交流的橋梁,有利于講好廣西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也有利于促進民心相通,經貿往來,更使得非遺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撐和新的亮點.[8]通過名錄體系的構建,就是要促進人民群眾更加自覺、更加廣泛地加入優秀傳統文化的實踐中來,為廣西文化強區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持.
2 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在非遺保護的早期階段,名錄制度在搶救、保護廣西優秀文化中發揮了積極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尚不完善,加上地方保護理念存在偏差、重視程度不夠等原因,致使廣西名錄體系建設上仍存在不少問題.
2.1 政府包辦包攬導致名錄建設政績化、商業化
當前非遺保護的工作原則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9]在非遺保護的早期階段,由政府主導是符合國情的.多年來的實踐也證明,在政府強有力的推動下,廣西在非遺保護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政府主導”在不少地方往往演變成了政府包辦包攬,以至于“社會參與”僅僅成了一個口號.最后只看重非遺帶來的政績和經濟效益,使得名錄建設逐漸政績化和商業化,而這兩者恰恰是當下非遺保護中最致命的問題.[10]
首先,在評審中,為求政績,不少地方單純追求入選的數量,而不注重質量.導致許多并不符合非遺定義或條件的項目混入名錄,使得名錄魚龍混雜.這種情況在市縣級名錄中尤為明顯.其次,政府的包辦包攬導致評審往往只從行政官員或者學者的角度去判斷,而缺乏文化持有者應有的立場,最終導致遺產核心內涵被邊緣化,甚至扭曲化.最后,地方政府考核往往只看重入選項目的數量,而少有人關注申遺之后的保護成效.
2.2 分層級的名錄體系容易導致文化階層化
客觀而言,非遺無法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文化價值本身是相對的、多元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項目進入名錄的過程,就是用他者的眼光和標準對項目進行價值評判的過程.而遺產一旦進入名錄,就會獲得政策、資金、場地等各方面的優勢資源.層級越高,獲得的資源就越多,就越容易受追捧.而未進入名錄或無法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項目卻很少有人關注.
事實上,進入名錄的項目畢竟是少數.例如,廣西縣級以上非遺共6272項,僅占普查資源線索總量的4.66%.未進入名錄的優秀的文化遺產,同樣是各民族在歷史進程中適應周圍環境的偉大創造和智慧結晶,同樣值得我們珍惜、保護和傳承.同時,由于非遺具有流變性和歷史性,許多遺產在傳承傳播過程中會有跨越族群、社區的現象.[11]而遺產進入名錄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社會、經濟效益,容易導致出現搶注遺產的問題.在名錄建設的早期,往往誰就先申報,誰先列入.未列入名錄的地區則失去了被保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導致該地區遺產項目的萎縮,甚至消亡.
這種偏離了非遺保護初衷的做法無疑打破了鄉土社會里原有文化體系的平衡,從而出現文化階層化的問題.可見,名錄體系的構建是一把雙刃劍,當我們對文化進行篩選并將其置于不同層級,尤其是將資源過于集中在進入名錄的項目和更高層級的項目時,客觀上就容易破壞文化的多樣性.
2.3 現行的類別設計容易將完整的項目肢解
《非遺法》將非遺分為六類,①(一)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二)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三)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四)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五)傳統體育和游藝;(六)其他.在名錄評審中,為突出可操作性,則將非遺分為十類.②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美術,傳統體育、游藝和雜技,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這種細化的分類制度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遺分類設計的本土化實踐和理論貢獻.它在框架設計和制定標準時,最大程度地考慮了普適性原則,盡力尋求遺產項目在該類別文化特質上的最大公約數.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突顯遺產項目某方面特征和價值的過程中,必然會忽視或舍棄其他部分的特征和價值,從而出現完整的項目被肢解的問題.
一方面,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是各民族在適應周圍環境的生產生活中的偉大創造.當我們將遺產從整個生境中抽離出來作為某一種藝術或文學項目套進某一類別時,客觀上很容易人為地割裂遺產與環境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大部分文化項目都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完整的文化體系,往往包含多重文化屬性.也就意味著,在官方的現行分類體系中,大部分項目是跨類別的.例如壯族天琴藝術,既有傳統音樂的屬性,也有民間文學、傳統舞蹈,甚至包含祈福儀式的內容,很難說哪一部分的文化屬性更為重要.類似的項目還有壯族末倫(包含民間文學、曲藝、民俗三重屬性)、侗族多耶(包含傳統音樂、傳統舞蹈、民俗三重屬性)等.當為了符合某一類別的申報標準和要求時,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突顯該遺產某一部分的價值和文化屬性,而隱去了該遺產其他的文化價值和天然屬性.這種特質上的“顯”與“隱”很容易將完整的文化項目肢解.
2.4 國家級非遺項目數量嚴重偏少,制約了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
截至2019年12月底,國務院共公布了1372項國家級非遺.而廣西國家級非遺子項目只有52項,僅占全國總量的3.79%,遠遠低于全國100 項的平均值,也遠低于西部省區87項的平均水平.而與廣西相鄰的貴州省為140項,云南省為122項.貴州僅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有國家級非遺72項.顯然,國家級項目數量明顯偏少,無法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關于對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邊境地區傾斜的政策.同時直接影響著廣西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數量、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申報及對中央非遺保護支持經費的爭取.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廣西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不利于民族文化強區的建設和民族自信心的樹立.
2.5 項目定位不準確影響向更高層級的申報
在市、縣級非遺名錄中,部分項目在定名、類別歸屬等方面定位不準確,容易出現錯誤的價值導向,也直接影響了遺產往上一層級的申報.具體表現在:
(1)不少地區為突顯項目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獨特性,在定名時往往采取“民族的某一支系+項目本體”或是“申報地區+民族+項目本體”的方式.如白褲瑤打陀螺、白褲瑤年街、那坡彝族跳弓節、興安瑤族刺繡等.然而,在中國官方公布的五十六個民族中并不包括支系,且在項目前冠以“申報地區+民族”的做法,容易將項目碎片化、行政化,既無法準確地反映項目存續和流布狀況,也不符合非遺規律.
(2)部分項目類別定位不準確.如前所述,在中國現行的名錄分類體系中,很多項目具有跨類別的文化屬性,項目歸類是申報和審批中的普遍難題.例如“梧州龜苓膏配置技藝”是第一批區級非遺項目,申報時主要考慮龜苓膏具有防治熱毒、濕毒的功效,因此將其歸為傳統醫藥類.但醫藥行業并不將龜苓膏作為一種傳統藥方或藥劑來使用.盡管其具有一定的藥用功能,但該項目更側重配置方面的技藝,因此放在傳統技藝類更合適.
(3)部分市縣甚至將物質遺產混入了非遺名錄中,更是混淆了物遺和非遺之間的界限.
3 完善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建設的對策
名錄體系的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需要邊探索、邊實踐、邊總結的文化事業.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筆者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并結合廣西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認為可通過以下措施可加以應對.
3.1 正確處理多元行動方的關系,保障民眾在名錄建設中的文化主體地位
根據《公約》關于非遺的定義可知,社區民眾才是“文化”的持有者,是“文化”的真正主人.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推進,民眾文化意識的覺醒,應該逐步由政府主導向民眾主導轉換.政府在非遺工作中的主要作用應該是組織、參與或引導,專家主要負責咨詢.兩者都不應該越俎代庖,包辦包攬.只有恰當處理多元行動方的關系,實現文化主客位的正常化,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名錄體系建設的政績化、商業化.
此外,要避免“社會參與”的口號化、民眾文化主體的虛無化,必須在法律法規的層面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在名錄構建過程中,不僅要獲得社區民眾的授權,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保障文化持有者的參與權、話語權和監督權.實現遺產申報由“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換,最終實現非遺的可持續發展.[12]
3.2 從自治區級層面做好非遺名錄體系的頂層設計
(1)要從各級層面尤其是自治區級層面控制入選名錄的項目數量.應依據非遺的定義和入選條件,從源頭把控名錄的門檻,提高入選質量,確保名錄的價值導向.應避免為盲目追求入選項目的數量和層級,將遺產拆解或將偽遺產混入名錄的做法.項目入選名錄不僅僅是一種榮譽,更應該是地方政府和文化持有者向全社會做出即將擔負起遺產保護責任的公開承諾.
(2)在名錄評審中,應改變“誰先申報,誰先列入”的做法.尤其在處理跨民族或跨地區的同類非遺申報時可以采取以下三種方式,以避免搶注遺產情況的發生.
一是對于在形式、內涵上均保持相對獨立、完整的同類項目,均可列入名錄.例如同是“打油茶”,但侗族和瑤族的打油茶在油茶配料、工具、制作流程、相關習俗都有各自的民族特點,是當地民眾適應周圍環境的經驗總結和長期形成的民俗.因此,可以同時列入名錄.
二是對于形式、內涵上大體一致的同類項目,可采取列入擴展名錄的做法.例如“壯族打榔舞”是壯族民眾以農具榔、杵為舞具模擬稻作生產的一種傳統舞蹈.廣泛流布于南寧市馬山縣;崇左市天等縣;百色市田陽縣、平果縣等壯族聚居區.各地的打榔舞在舞具、舞蹈形式、內容上大體一致,因此可以將各地整合作為申報地區以擴展項目的形式列入名錄.
三是對于明顯以某地為核心,其他地區為輻射區域的項目,可以采取以核心區域為申報地和保護單位,但同時應公布項目的流布區域.項目保護單位也不僅僅只承擔本地區的項目保護職責,還應作為牽頭單位負責全區其他流布區域該遺產的保護.
(3)建立自治區級急需保護的非遺項目名錄和優秀實踐名冊.過去的十多年來,自治區本級可用于非遺保護的經費十分有限,非遺長期處于“灑面粉”式的保護階段,導致非遺保護工作缺乏重點,保護成效不明顯.有些急需保護的項目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處于瀕臨消亡的邊緣.因此,可以設立自治區級急需保護的非遺名錄,針對性的采取“搶救性保護”.此外,建議設立自治區級優秀實踐名冊,主要側重于遺產保護成效的示范性和推廣性,為其他地市提供借鑒、參考.
3.3 尊重文化發展規律,樹立整體性保護理念
整體性保護的理念早已是國際社會和學界的共識.正如劉魁立先生指出的:世界非遺保護的目的是以全方位、多層次和非簡化的方式來反映并保存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只要是能體現人類在特定時空內的文化形態及其創造力的,都應該給予關注、研究并注意保護.[13]
在名錄建設中要貫徹整體性保護的理念,應當至少從三個層面來考慮:
(1)應著眼于名錄體系外整個傳統民族文化全局性的保護,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少數、特殊遺產的保護.例如,如果壯語消亡了,那么以壯語為載體的眾多遺產如壯劇、壯族三聲部民歌、壯族銅鼓習俗等都將失去生命之源,其傳承發展更無從談起.
(2)注重項目與環境之間的關聯.正如烏丙安先生所說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歌,沒有無緣無故的舞.”[14]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有其生存的、特定的文化土壤.因此,在遺產保護中,既要保護非遺,也要保護其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
(3)注重與非遺相關聯的“物遺”的保護.“物質”和“非物質”恰如一枚硬幣的一體兩面.前者是其載體或具體表現形式,后者是內涵和精髓,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例如壯族天琴藝術,天琴的制作、彈奏、曲譜譜寫、儀式等是非遺本體,但如果沒有了曲譜、家屋、圩場等,天琴藝術也終將失去依托,最終走向消亡.
3.4 聚焦于遺產具有的多重文化屬性,建立更為科學的分類制度
鑒于遺產文化屬性與名錄文化屬性上的沖突,我們有必要重新回歸到《公約》關于非遺分類的認識和思考上來,并在分析、總結現行分類制度的優勢和存在問題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更為科學的分類制度.
如前所述,過于細化的分類容易將具有多重屬性的遺產肢解.而《公約》開放的劃分體系和可以跨類別申報的制度設計恰恰彌補了這一點.例如2009年,中國列入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的遺產——“藏戲”,在中國名錄分類中屬于傳統戲劇,但在教科文組織公布的“藏戲”所屬類別中則同時包含了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顯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考慮“藏戲”所具有傳統戲劇的文化屬性外,還充分考慮了其具有的民間文學、儀式、禁忌、民俗等方面內容.
因此,有必要借鑒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建設的經驗,充分考慮遺產具有的多重屬性,結合具體情況制定更為科學的分類制度.不應為了符合某一類別的申報標準,而舍棄了遺產其他方面的文化屬性.例如壯族天琴藝術,在公布類別時不應只是傳統音樂,還應該包括民間文學、傳統舞蹈和民俗的文化屬性.
3.5 加大國家非遺項目的申報,提升廣西非遺的可見度及影響力
廣西作為非遺資源大省,有著大量與東南亞國家共享的跨國跨境項目.只要做到科學謀劃、合理部署,就能逐步縮短與全國的差距.
首先,應當及早謀劃,可以從現有的762項區級項目中篩選一批具有競爭力的項目,以設立廣西的國家級非遺申報預備清單,甚至是人類非遺代表作申報預備清單.其次,應當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力量,加大科學研究.國家級非遺項目的申報同時也是對非遺項目再認識、再挖掘、再研究的過程.這需要借助專家學者的力量,做好非遺項目基本內容、分布區域、地理環境、歷史淵源、重要價值、主要特征等基礎性綜合研究,為遺產在更高層級體現項目可見度提供必要的學術支持.再次,應當準確把握國家級非遺項目申報的導向,扎實做好國家級非遺項目申報材料.
3.6 打破“名錄”終身制,實施動態的評估、監督和管理機制
為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重數量、輕質量”,“重申報、輕保護”的錯誤理念,有必要打破“名錄”終身制,實施動態的評估、監督和管理機制.2011年8月,文化部公布了《關于加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指出要加強監督檢查,實施國家級代表性項目的動態管理.建立完善的非遺保護效果評價機制,既是對當前非遺保護名錄制度的一個有效補充和完善,更是將有關非遺的各項制度落到實處的重要保障.[15]
從自治區層面采講,關鍵是如何將這一制度細化落實,形成長效機制.首先,應將各級名錄中不符合非遺定義的項目,尤其是偽遺產“清出”名錄,確保正確的價值導向.其次,將定名、定位不準確的遺產項目進行調整.再次,通過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對不具備保護資質,無法履行保護職能的項目保護單位采取警告、摘牌或調整等措施.為更好地開展保護工作,可以依托民間組織、行業協會等作為保護單位,充分發揮文化持有者自身的力量.例如民間文學類項目可以依托文聯,傳統音樂可以依托山歌協會,傳統美食類項目可以依托食品協會,醫藥類項目可以依托醫院、醫藥聯合會等更為靈活多樣的項目保護單位.
4 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脈.非遺保護更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系統工程.非遺名錄體系在非遺保護中發揮了關鍵核心的重要作用.當然名錄體系只是一個工具或通道,最終我們需要回歸到對《公約》精神和非遺保護的理念的再認識、再理解上來.在更加注重保護的后申遺時代,我們更應尊重社區民眾文化主體地位,尊重文化發展規律,樹立整體性保護的理念,建立更為科學的分類體系等,并且恰當處理多元行動方的關系,形成合力,才能有效保障非遺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