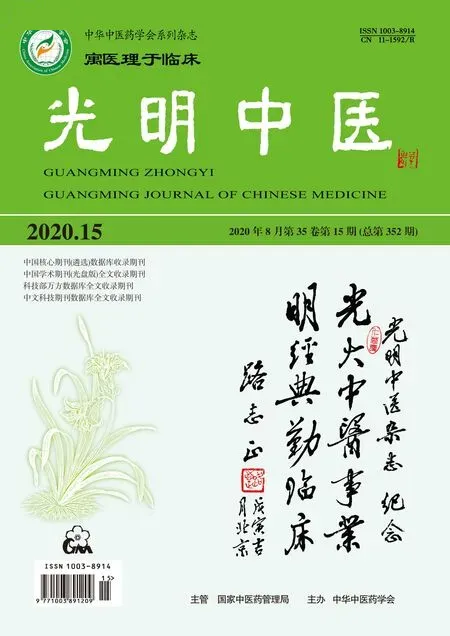張林軍主任醫師抗腫瘤藥物治療肝損傷的經驗
張夢凡
抗腫瘤藥物的合理使用是腫瘤內科治療的重要方法之一,抗腫瘤藥物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可產生不良反應,損害機體內正常的細胞、組織及器官,引起消化道反應、骨髓抑制、肝腎及心臟毒性,其中抗腫瘤藥物引起的肝損傷占藥物性肝損傷的1/5~1/4,為藥物性肝損傷的第二大病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抗腫瘤藥物的應用和療效。肝損傷患者血生化及免疫指標存在異常升高,如轉氨酶、膽紅素、膽汁酸增高,這些指標的降低可以作為評價藥物治療的標準[1,2]。張林軍主任醫師致力于腫瘤的中醫藥防治研究工作30余載,擅長運用中醫藥治療抗腫瘤藥物導致的肝損傷,現將其經驗介紹如下。
1 藥毒直中 傷肝及脾 辨治理應溯根求源
張林軍主任認為抗腫瘤藥物的不良反應為外來之“藥毒”,藥毒戕傷機體正氣,傷肝及脾,肝主疏泄及脾司運化失常,濕濁內蘊,濕郁化熱,濕熱薰蒸肝膽引起肝損傷。臨床多表現為疲倦乏力、納呆、口干口苦口黏、惡心嘔吐、噯氣、脘腹脹滿、脅下不適或脹滿疼痛,甚至黃疸、大便黏膩不爽或便秘、面色萎黃或色黃鮮明、舌暗紅或紫暗苔白膩或黃膩、脈細濡或滑數等癥,肝功能異常。藥毒入里直中傷肝,此為病之本;肝氣郁滯,橫逆犯脾,濕濁內蘊,此為病之始;濕熱壅滯,阻滯氣機,此為病之延。故治療上應肝脾同治,以疏理氣機、解毒利濕為大法。根據其臨床表現將其辨為濕濁或濕熱病,與相關文獻所載之濕濁或熱毒或濕熱相一致[3-5]。
2 柔肝健脾 未病先防 治療先安未受邪之地
腫瘤本是正不勝邪的病理產物,加上抗腫瘤藥物易損傷人之正氣,宗《金匱要略》“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之旨,當先安未受邪之地。張主任常在患者化療1周前,通過經驗方“保肝健脾湯”養血柔肝、理氣開胃、健脾運濕、降逆和胃以增強肝脾抵御藥毒的能力,不僅降低抗腫瘤藥物的不良反應,還能提高機體對其的耐受閾值。保肝健脾湯組成:柴胡15 g,香附10 g,郁金15 g,當歸10 g,白芍10 g,川芎8 g,牡丹皮10 g,生黃芪20 g,黨參10 g,生白術10 g,茯苓20 g,陳皮10 g,山楂10 g,葛根10 g,黃芩10 g,姜半夏6 g。以當歸、白芍、川芎養血柔肝護肝體,柴胡、香附、郁金理氣疏肝助肝用,增強肝臟抵御藥毒侵襲的能力;黃芪、黨參、白術健脾益氣;茯苓、葛根、陳皮、姜半夏降逆利濕,增強脾胃升清降濁及運化水濕的功能,避免抗腫瘤藥物之濕濁或濕熱邪氣與體內痰濕郁熱之病理產物內外合邪誘導或加重不良反應的發生。諸藥合用,有提高肝細胞生存率、抗脂質過氧化損傷、保護肝細胞,減少炎癥因子釋放,降低肝臟炎癥,改善肝功能的作用[6-9]。本方充分體現了中醫未病先防、防重于治的特色。
3 清化濕熱 祛邪當辨證論治
藥毒中肝,肝氣橫逆犯脾,脾運化失司,濕濁內生;或直中脾胃,脾失健運,水濕內停,或脾胃升降失常,濕濁郁熱阻滯中焦。張主任除喜用通用驗方“化濕清熱保肝湯”加減外,常辨證選方用藥。如濕重熱輕者,癥見脘腹脹滿、惡心噯氣為主,則用半夏瀉心湯合旋覆代赭湯加減;或以疲倦乏力、納呆、脘脹為主則以香砂六君子湯化裁。如濕熱并重,癥見口苦胸悶腹脹者,以甘露消毒丹加減;伴情緒波動較大者可用蒿芩清膽湯合黃連溫膽湯加減。如熱重于濕,癥見口干渴、發熱納呆、腹滿脅痛、大便秘結、舌苔黃膩、脈弦數者,茵陳蒿湯合梔子柏皮湯加減。如濕熱彌漫三焦則用連樸飲合茵陳蒿湯、三仁湯等加減。化濕清熱保肝湯組成:柴胡15 g,黃芩10 g,赤芍10 g,郁金10~15 g,杏仁10 g,白蔻仁6~10 g,薏苡仁30 g,蒼術15~30 g,茯苓20 g,澤瀉10 g,陳皮10 g,枳殼10 g,厚樸10 g,蒲公英15~30 g,垂盆草30 g,白花蛇舌草20~30 g,升麻10 g,荷葉20 g,甘草10 g。本方以四逆散、小柴胡湯疏肝理脾、和解少陽以治本,以清震湯合平胃散燥濕除滿、升清運脾以化濕濁,茯苓、澤瀉、垂盆草、郁金、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等利水滲濕、清熱解毒、涼血祛瘀并給藥毒以出路,藥理研究提示以上諸藥有抗氧化、抗炎、增強肝臟解毒能力,改善肝微循環,促進肝細胞再生與修復的藥理作用[7,10-12]。
4 驗案舉隅
周某某,女,40歲,醫生,北京市人,2019年11月5日初診,左乳頭周圍腫物2年加重半年,自幼喜冷而惡熱、煩躁易怒、五心煩熱。現左乳腫物脹痛,夢多易醒,醒后心慌、燥熱、出汗,頭面油大,痰多,納可,大便不成形,每天1~2次,矢氣多,下肢沉重不適,口黏,晨起口苦口臭,化療后引起閉經3個月,白帶可。觸診:左乳外上象限黃豆大小腫塊,雙腋窩可觸及麥粒大小淋巴結。望診:眼圈及下頜青黑,左側乳頭凹陷,指甲凹陷脆裂,舌暗紅苔白厚膩微黃,脈弦細滑。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診斷:左乳浸潤性乳腺癌(luminal B型,中分化)伴淋巴結、骨轉移。自2019年5月21日、6月10日、7月8日、8月6日采用TC方案(多西他賽120 mg、環磷酰胺0.9 g)化療,9月18日、10月16日采用吡柔比星75 mg化療。8月1日查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49 U/L(正常值:7~4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43 U/L(正常值:13~35 U/L)。8月29日ALT 46 U/L,AST 30 U/L。10月10日ALT 72 U/L,AST 60 U/L。11月5日ALT 100 U/L,AST 54 U/L。為了能夠順利完成余下的2次術前化療前來就診。中醫診斷:濕熱病(肝郁脾虛,濕熱蘊結,濕熱并重)。治法:疏肝健脾,化濕清熱。藥用化濕清熱保肝湯加減:生黃芪30 g,當歸10 g,白芍10 g,雞血藤30 g,柴胡15 g,黃芩10 g,虎杖15 g,白花蛇舌草30 g,茵陳30 g,蒲公英30 g,瓜蔞10 g,炒蒼術30 g,陳皮10 g,厚樸10 g,茯苓30 g,梔子10 g,豆豉20 g,山楂10 g,升麻10 g,荷葉20 g,7劑。
11月8日二診,用上藥痰多消失,五心煩熱明顯緩解,燥熱、醒后心慌、多汗、乏力易疲勞緩解,仍睡眠易醒、膝蓋疼痛、小腿不適、足根疼痛、指甲凹陷、矢氣多、頭面油大、大便不成形,舌淡暗苔白膩,脈弦細滑。濕熱彌漫之勢已挫,脾虛血虧有漸復之機,加強清化濕熱、養血柔肝之力。上方茵陳(先煎)加至50 g,加生杜仲30 g,川芎10 g。7劑。
11月18日三診,復查肝功(ALT 23 U/L、AST 35 U/L)已全部恢復正常。為11月19再次化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現五心煩熱消失,頭油大、左乳外上象限腫塊疼痛,出汗癥狀明顯緩解,大便時有不成形,下肢較前有力,但稍活動仍感疲勞、乏力,夢多易醒,醒后時有心慌、燥熱,舌尖紅質暗苔薄白根稍黃,脈弦細。上方減川芎、黃芩、雞血藤、蒲公英、瓜蔞,加赤芍10 g,薏苡仁30 g,黃柏10 g,懷牛膝20 g。5劑。
11月22日四診,19日吡柔比星化療后出現胸悶心慌、夢多易醒、煩躁易怒、多汗、納呆、胃脘滿脹、嘔吐、腹瀉、雙膝疼痛,雙下肢沉重酸脹,但運動出汗后緩解,舌尖郁紅苔黃厚膩,脈細弦。肝功:ALT 65 U/L,AST 45 U/L。辨證:濕熱并重、彌漫三焦。治以疏利三焦、調理中州、清利濕熱,以蒿芩清膽湯合三仁湯加減。處方:茵陳15 g,青蒿10 g,竹茹10 g,黃芩10 g,柴胡15 g,梔子10 g,豆豉20 g,杏仁10 g,白豆蔻10 g,薏苡仁30 g,滑石20 g,陳皮10 g,炒枳殼10 g,木香10 g,赤芍10 g,郁金10 g,生麥芽30 g,法半夏10 g。7劑。
11月29日五診,失眠、食欲不振、鼻塞、怕冷消失,胸悶、心慌基本消失,胃脘脹滿、雙膝蓋疼痛明顯緩解,右中腹部仍時有刺痛,噯氣、大便不成形每天1次,伴有矢氣多、味臭,夢多易醒,醒后心慌煩躁,舌尖及兩邊紅苔薄白,舌根黃膩,脈弦細。上方減陳皮、炒枳殼、郁金。加瓜蔞15 g,蒲黃10 g,五靈脂10 g以加強祛除痰瘀之力。7劑。
12月6日六診,復查肝功恢復正常,為12月18日化療奠定了基礎。現雙下肢沉重酸脹、腹瀉消失,夢多易醒、醒后心慌煩躁、大便及矢氣味臭明顯緩解,胃脘脹滿、噯氣緩解,舌尖紅苔黃膩,脈弦細滑。在上方基礎上減木香、滑石、竹茹、青蒿、生麥芽,合用連樸飲加石菖蒲10 g,厚樸10 g,黃連7 g,郁金20 g,白花蛇舌草30 g以加強清化濕熱之力。7劑。
12月13日七診,胃脘脹滿消失,夢多、噯氣、矢氣明顯緩解,熱則心慌、身燥,偶驚醒,大便時稀,晨起口臭,納可。昨日因著涼出現鼻塞、流涕。舌尖紅苔黃膩,脈弦細。上方減蒲黃、五靈脂。加防風10 g,羌活10 g既祛風寒,風能勝濕以加強化濕達郁之力。
12月20日八診,感冒癥狀消失,18日化療后無惡心、乏力等不適,現癥夢多、怕熱喜冷,煩躁易怒,熱則心慌,晨起口臭,舌尖紅質暗苔黃厚膩,脈弦稍澀細,肝功能檢查未見異常。減防風、羌活。加竹葉10 g,虎杖15 g以加強清化濕熱之力,減輕癌毒濕熱之邪對機體之損害。
12月26日九診,術前化療已結束,復查肝功未見異常,調整治療思路為養血柔肝,化痰散結,解毒抗癌,藥用生黃芪30 g,太子參15 g,柴胡15 g,香附10 g,郁金20 g,當歸20 g,生地黃10 g,玄參10 g,蟬蛻15 g,僵蠶10 g,夏枯草 20 g,瓜蔞20 g,生牡蠣20 g,清半夏10 g,陳皮10 g,連翹30 g,蚤休15 g,合歡皮20 g。14劑。
按:患者應用TC方案化療,第3、4次出現肝功能輕度異常。自第5次采用吡柔比星化療,轉氨酶異常較前加重,第6次化療轉氨酶升高達高峰,本例中轉氨酶升高與文獻報道的TC方案、吡柔比星的用藥劑量和多次給藥成正比的結論一致[13,14]。患者喜冷而惡熱、煩躁易怒、五心煩熱,為陰虛火旺體質,而TC方案及吡柔比星等藥毒與體內之熱內外合邪戕傷正氣、損耗陰血,出現閉經及虛火擾心的夢多易醒、醒后心慌、燥熱汗出的癥狀外,還可見頭面油大、痰多、口黏、大便不成形、下肢沉重不適的濕濁證。經化濕清熱保肝湯加黃芪、當歸、白芍扶正祛邪治療2周則肝功恢復正常。張主任臨床之際,根據藥毒傷肝及脾的特點,提倡未病先防,善用對藥當歸、芍藥各10~30 g,養血柔肝、活血通脈補肝體;加白術或蒼術10~30 g,形成養血補肝、健脾燥濕的肝脾兩補之角藥,藥理研究其均有提高肝細胞生存率,減輕肝組織受損程度,減少壞死肝細胞數量的功效[8,15]。第7次吡柔比星治療后轉氨酶升高幅度較前有所下降,前方已發揮治療作用;此時胸悶心悸、脘腹脹滿、嘔吐腹瀉、大便黏膩不爽、雙膝疼痛、下肢沉重的濕熱彌漫三焦之癥狀明顯,濕熱較重,故采用蒿芩清膽湯與三仁湯加減,雙方共奏宣上、暢中、滲下之能,加強三焦分消走泄之力,則邪熱得清,濕濁得化,氣機調暢[16,17]。1周后復查肝功恢復正常,繼而與治療抗腫瘤藥物不良反應的連樸飲[18]合用,加強苦降辛開、清化濕熱、理氣暢中之功,使中焦脾胃升降有序,發揮脾胃運化輸布氣血津液之功,使藥毒不能與體內濕濁及濕熱之邪相合,勢必力孤,從而提升機體對藥毒抵御能力,方證相對,直達病所。故12月22日最后一次吡柔比星治療后未見肝損傷所致的轉氨酶異常征象的出現。繼而以益氣養血、涼血散瘀、化痰軟堅、解毒抗癌法治療乳腺癌,為擇期手術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