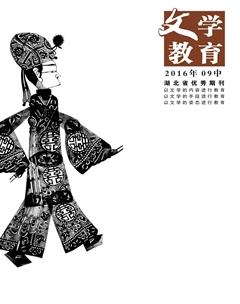中國詩歌格律淺析
張峻榛
內容摘要:格律是中國詩歌的外在要求,不管格律如何變化,其本意,都是希望讓詩歌的水平更上一層樓。本文將對中國古今詩歌的格律特點進行探討。
關鍵詞:格律 古體詩 近體詩 現代詩 三美
中國詩歌的始祖——《詩經》本來是并不講太多格律的,浪漫主義的先河《楚辭》也不講什么“平仄對仗”。可我們一看到《詩經》、《楚辭》的詩便可以判斷出它的大致出處。這是因為這些先秦的詩作,已經有規律可循。譬如《詩經》的常用賦、比、興的手法,或是《楚辭》的常用語氣詞“兮”。
從秦漢至南北朝,前面的三曹,晚些的陶潛、左思、謝靈運均是詩歌上的大師級人物。不過這時,完備的近體詩格律還未形成——近體詩格律是在唐代才完全成型的。
近體詩中,每句的字數、每首詩句數均不可改變。
現代漢語的四聲,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而古時則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后來漢語演變,入聲在現在的普通話中消失,又有一些字的發音變化,才有了現代四聲。平,好理解,就是指平聲。仄,即“不平”,即古時“上、去、入”三聲。一般作近體詩,多按古漢語來分平仄。
在近體詩中,平仄要求較多,首先是在本句中的交替,如“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仄仄平平仄仄平”。又如“蓬門今始為君開”(杜甫)——“平平仄仄平平”。五言的也一樣,如“風正一帆懸”(王灣)——“仄仄平平”。簡而言之,五言句不外乎這幾個形式:“中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中仄仄平平”(中:可用平可用仄),七言句不過是:“中仄中平平仄仄”、“中仄平平仄仄平”、“中平仄仄平平仄”、“中平中仄仄平平”四種。由此易知,平仄在一句中不斷交替。
有時,詩人會打破這些常規,即為拗句。拗句可以通過在本句,或是在同一聯的另一句中調整平仄而形成的“救”,如此“合律”——但格律畢竟是“外”,為了詩歌的內涵。打破格律也是可以的。(關于拗救的知識較復雜,本文以介紹對比為主,故不贅述)
之后,近體詩的平仄還講求“粘對”。粘,指后一聯出句第二字與前一聯對句第二字的平仄需一致。對,則指同一聯中出句與對句的平仄要相反,如:“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除了可變通的字外,其他的平仄完全相對。
至于平仄的變通,有(七言)“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五言中一三不論,二四分明),即偶數字的平仄要嚴格處理,除韻腳外的奇數數字的平仄可變通。這是因為在詩句中,偶數字往往在一個斷句點(以及節奏點)上,如:“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四三結構)、“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所以要重視偶數字的平仄。然此種“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是有條件的,“平平仄仄平”變作“仄平仄仄平”即犯了孤平(可以改作“仄平平仄平”來救),“仄仄仄平平”變作“仄仄平平平”即犯“三平調”,所以在變通時,還要注意是否犯了這一類忌諱。
平仄的規定,一方面是近體詩的“束縛”,限制人們的創作,可另一方面,又給了近體詩一種別樣的美——我們現在讀這些詩時,往往覺得極富音律美,這便是因為近體詩的平仄的交替、相對賦予了它富有頓挫感的風格。
多數律詩,都是在中間兩聯用了對仗的。對仗的運用,也是近體詩——尤其是律詩的創作中所要遵循的格律。
如上面所言,律詩的對仗,多是在中兩聯對仗的。然而也有只用一聯對仗、全詩中三聯對仗,甚至全詩均用、均不用對仗的。但總體來看,這些對仗都符合一定的要求,有它們的共性。
我們現在看對聯時會看到,上下聯平仄基本相對應,上聯仄聲結尾,下聯平聲結尾。而且上下兩聯中的詞一定可以相對。律詩中的對仗也是如此。工整一點的對,要求同一類詞相對——方位對方位,顏色對顏色,諸如此類。除此以外,一些常常并列在一起的字詞,譬如天地,詩酒,花鳥等,也可以算在其中。而同義詞相對,是詩家大忌。如果出句與對句由于用了過多同義詞而句意基本一樣,就是“合掌”相當于多寫了一句無用的話,浪費了一個句子,虛耗了近體詩本來就較小的空間。所以合掌是要堅決抵制的。
寬一點的對,詞性相對,都是可以的,如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更寬一點,兩句半對半不對的,也有。在尾聯對仗,用半對半不對就更好。因為用對仗結尾,易給人未說盡之感。杜甫在一首律絕中,用“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作結,美則美矣,了卻未了。在短小、像一個小片段的絕句中用來結尾尚好,用到完整性更強的律詩中,則給人生硬“爛尾”之感。而杜甫《登高》尾聯,以“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作結,前半句對仗較工,而后半句(斷句應該是“繁|霜鬢”、“濁酒|杯”)不對,則對仗極寬,更加自然。
但要在尾聯以嚴一點的對作結,也是可以的。若真要如此,用流水對來結,最好。流水對,通俗點講,就是上下兩句句意相通,像是一句話分成兩句來講的對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中,“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分成兩句而句意連續性強,像是一句話被分成兩半正是如此。這樣一對,自然而不生硬。
統而言之,律詩在對仗上要求更寬松,不像是平仄那樣嚴。用多少、用什么都是可以由詩人靈活選擇,自由發揮的。至于律絕,對仗更是可用可不用,完全憑詩人來定。
自然,近體詩與其他詩一樣,都是要押韻的。我們現在的詩,用韻更寬松,發音相近,讀著順口的字,都可以用來押韻。但近體詩則不痛。它的韻,必須是平聲,且要由專門的韻書規定。它把各個漢字分類,用韻時只能從同一類的字中選用。在創作中,近體詩的首句可以押“鄰韻”,這“鄰韻”,不一定是書中與之相鄰的一類,也可以用不在同一類中,而發音卻與之相近的字來押。
近體詩的格律,以嚴格的平仄為中心,講求對仗的手法,押韻按韻書來押。凡不合于這些的,都可以說是是古體。然而,古體也不能完全擺脫格律的影響。
雖然多數古體詩不講究平仄,但合乎平仄的格律的句子也是不少的。王勃的《滕王閣詩》中,除六、七句不粘外,其余幾句都基本合乎粘對,平仄在同一句中也相互交替合律。崔顥《黃鶴樓》一詩,則更是一首古風化的律詩、律詩化的古風。前半首是古風的樣子,后半首則是律詩的樣子。(二詩附于后)
古體詩的押韻,也是寬松不少的,律詩一般只在首句用鄰韻,而多數古體卻可以在全詩中通用鄰韻。中間換別的韻,也是可以的。不過古體中的“柏梁體”則特殊一些,不能隔句用韻,必須句句用韻,一韻到底。
古體詩也不要求對仗。是否運用這一手法全由詩人決定。
因此,一些古體詩受了近體影響,用了一些近體的句式。但這種用法不是硬性的格律,不需要詩人遵守。押韻上,也只有柏梁體要求較高。所以可以說:古體詩的格律比近體詩寬松多了。
詞與詩不同的一點是:在剛開始,詞是為了和著曲子唱而專門填出的。后來詞與曲子分離,才成為一種按專門的詞譜所填的詩。
詞有詞牌。詞牌可以看作是詞的格式的名稱。與律詩不同的是,詞的格式有上千種,就是說,有上千個詞牌。詞牌不同,格式自然不同。按長短,詞可以分為小令、中調、長調。按闕數,則有單調、雙調、三疊、四疊之分。詞中的句子與近體詩接近,都講究平仄的交替。
我國固體詩詞中,近體詩對格律要求最高。其次是詞(因為同一詞牌可能會根據不同情況變化,增、減一些字)。至于各種古體,對格律的要求是不高的。而這些格律,基本是以平仄為中心,加上韻書所規定的韻,以及律詩中要用到的對仗而形成的。這種對字音的嚴格要求,對每句字數的規定,對對仗的把控,使近體詩讀起來既有頓挫感,又有整齊之風。而詞則因此既有音律美,又有長短句交錯的飄逸。古體則由于其寬松的格律,常顯得更自由,情感更強烈突出。
中國現代詩則基本放下了格律。連押韻也去除了韻書的限制,不再拘泥于形式。很顯然,當一個人吟著“春天,十個海子全部復活”的時候,那個人是想不到平仄對仗的。然而,現代詩并非不受古代詩歌影響。
這類影響中,最廣泛的,大概是一種“詩意”了。比如“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它既有一定的哲理,又有詩意之美。又比如“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讀來只是淡淡的一個“淺淺”,一個“這頭”,“那頭”,卻似有千鈞之力,不用一句吼叫而道出無限悲痛,與古詩的回味無窮而語言平靜溫雅,不是極相似嗎?
當然,詩意對詩的影響是內在的。現代詩中將古時的格律搬過來的,不多。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代詩也是有自己的格律的。韻要押——但不拘泥于韻書。還要分行分節——雖然這通常由詩人自己處理。這些,本身就是一種格律。但講到現代詩的格律,“新月派”的詩人——如聞一多,則不可不提。
應該承認,聞一多的“三美”主張,在整個新詩的發展中都是舉足輕重的。聞一多本人,也把“三美”貫徹在自己的創作中。“音樂美”的音韻,“繪畫美”的畫面感色彩感,“建筑美”的小節、句式的勻稱,他的很多詩都具備了。比如《忘掉她》,全詩每節開頭,結尾都用“忘掉她,象一朵忘掉的花”一句,中間用兩個押韻的七字句,富有建筑美、音樂美。而全詩情感也像建筑摩天大廈一般,隨著“春風里一出夢”、“夢里的一生鐘”、“蟋蟀唱得多好”、“墓草長得多高”不斷上升,但到最后仍一直壓抑,沒有大爆發,好像沒有封頂竣工,也沒有來一次大的垮塌。因此,作者用一種無聲的痛,一種無淚的哭,把對亡女的思念刻到了骨子里。
又如《死水》。這首詩的“建筑美”、“音律美”且不談,因為在我看來,它的“繪畫美”是極突出的。聞一多反其道而行之,用“翡翠”、“桃花”、“羅綺”、“云霞”等絕美的意象,來描繪“一溝絕望的死水”。用美寫丑是對丑的另一種突出表現,讓讀者看到一潭死水,告訴讀者什么是當年的中國。又用別樣形式描出丑惡,要“看它造出個什么世界”,這又在丑惡中生出一點改變的希望。
所以,中國的現代詩,也是有一定的格律的。
雖然格律只是詩的外在要求,但它也是不容忽視的。不管格律如何變化,其本意,都是希望讓詩歌的水平更上一層樓。如果合理運用格律,詩歌的光輝將更加耀眼。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