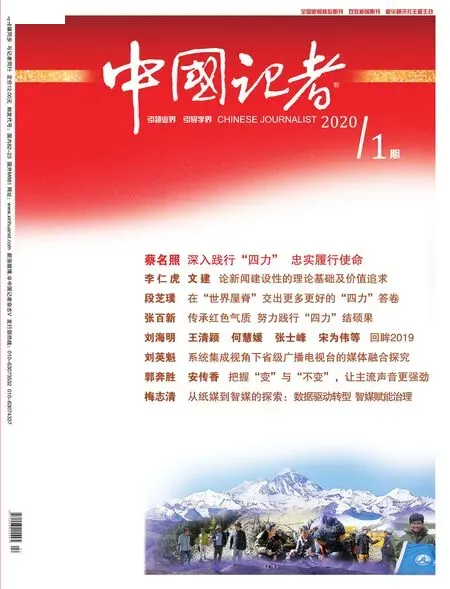在“雪山孤島”踐行“四力”的190天
□ 陳尚才
2018年11月下旬,新華社西藏分社分黨組選派我前往阿里地區札達縣楚魯松杰鄉掛職黨委副書記、副鄉長,進行蹲點調研。楚魯松杰“遠在天邊”。這里是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最偏遠的一個鄉,距離縣城313公里,距離拉薩市2000余公里,越野車需要在深山里開上7個小時。期間,需翻越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其中夏讓拉雪山達坂海拔5800多米,人在山頂,頭暈目眩;楚魯松杰清苦,這個中國陸地版圖上最西南方向的“幾”字型地方,生活著129戶472名群眾。境內雪山聳立,每到冬天,山中風雪呼嘯,連月不開。
一、蹲點“世界屋脊的屋脊”,以堅強意志扎根基層。接到掛職通知,我提前結束休假返回拉薩。去之前,札達縣委組織部領導告訴我,楚魯松杰即將大雪封山,山里條件十分艱苦,一旦患上突發急性疾病,即便用直升機接送都來不及。他好心勸我留在縣城,不要下去,他甚至不解地問:“你們單位怎么選這個時候送你去楚魯松杰呢?”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下基層掛職,就是為了蹲點調研,留在縣城還蹲什么點?調哪門子研?了解情況后,我由剛開始的一頭霧水變成了信心滿滿:我是農村出生長大的孩子,不怕吃苦,只要能學到東西,再艱苦的環境,我都能克服。可以說,到基層去吃苦,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是帶著使命感和榮譽感去吃苦的。但到達楚魯松杰后,才發現大雪封山后的艱苦,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里就是一處孤懸于世的風雪邊陲。降雪從12月份開始,一直到來年2月底才結束。儲備米糧,制作風干牛肉,蘿卜、白菜、土豆“老三樣”配牦牛肉,這就是我們過冬的基本食物。鄉干部職工住的樓房里沒有上下水,只能自己生火取暖;最擔心的是下雪天光伏的積雪、討好店主購買高價零食飲料、下鄉睡藏式沙發吃生牛肉等,還要承受那揮之不去的“高反”。楚魯松杰鄉有半年時間是大雪封山的“孤島”,沒有理發店、餐館等,鄉政府兩所商店里的物資也很快售罄。
為了緩解煙癮,我“開心地”喝完了3袋過期奶粉,1箱過期飲料,吃完了半箱過期方便面,在鄉政府周圍撿煙蓄電池無法存電,我們只能過沒電沒網、摸黑烤火的日子。

□ 2019年1月8日,新華社記者陳尚才(中)和楚魯松杰鄉干部在楚松村型欽牧場例行巡邏。(拉巴次仁/攝)
風雪連月、高山峽谷、斷電斷網、邊陲民族地區……人們生存之艱難不可想象,當然對記者“腳力”的考驗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這里,作為干部首先要克服生存面臨的困難:學會撿牛糞生火取暖、冰天雪地拖著水管抽水、手搖發電機洗衣服、爬樓頂清掃光伏板上屁股抽。惡劣的生存環境導致我經常偏頭痛、拉肚子、流鼻血,常常夜半醒來坐到天亮。強烈的紫外線曾三次曬傷了臉,整個臉發燒、灼痛、脫皮,4個多月不能洗澡,全身酸臭。無數次想要放棄,無數次又不斷告誡自己:我是新華社記者,是西藏分社選派的干部,職業情操和新華社榮耀,決不允許自己當“逃兵”。
二、用腳“丈量”邊境線,深入踐行“四力”。掛職鍛煉以來,我始終以新聞記者踐行“腳力、眼力、腦力、筆力”要求自己,深入到基層一線和農牧區群眾身邊蹲點調研,對楚魯松杰鄉歷史、文化、經濟、生態、教育、衛生、黨建、脫貧攻堅等10余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針對“水電路訊網,科教文衛保(社會保障)”等十項民生工程,訪干群、住農家、話發展。
翻越雪山達坂巡邊、走進牧場帳篷采訪、夜宿農家沙發、在沙石山揮汗植樹、在河畔農田學犁地。我始終堅持跟著巡邊的百姓,騎馬前往放牧點去體驗巡邊路上的艱辛與歡樂;在暴雪中幫著群眾做完了牲畜分欄工作,圍著牛糞土灶煮甜茶……在這里,我不僅是一名新華社記者,更是一名鄉黨委副書記,干部群眾的眼睛在盯著我看,看我的作風、勇氣、干勁。這種“腳力”的考驗,不再僅僅是記者能否不畏山高路遠走到百姓跟前,而是將自己變成一名農牧民走進干部群眾的心間。
在楚魯松杰,所見所聞都是外界聞所未聞,也是最鮮活的新聞素材。我根據自己的真實見聞采寫了第一篇駐邊筆記《喜馬拉雅深處,大雪封山他們仍在放牧巡邊》,講述普通干部群眾在艱苦的環境里如何工作、生活、巡邊的故事。之后,從醫療、教育、社保、脫貧、守邊、道路、基層工作等方面去發掘故事。在跟鄉領導、耄耋老人、脫貧干部、村“兩委”班子的聊天中,一個個新聞線索隨之浮現眼前,我共羅列出《夜宿次白益西家》等30條新聞線索。
有了線索,采訪了干部群眾后,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就像蓋一幢樓房,地基已經打好,題目和結構才是骨架,題目怎么起?怎樣去架構?在深山里,我沒有“頭腦風暴”的團隊,一切只能是自己苦思冥想。為了寫好稿件,我曾三次推翻之前選定的題目,披著迷彩大衣,深夜在鄉政府的院子里,邊抽煙邊思考,曾一度有干部認為我精神不正常。最終我決定大膽拋棄傳統的新聞寫作模式,采用講故事、散文化的語言鋪陳敘述,用新視角突出稿件的鏡頭感和畫面感。每個深夜,我都伏案寫作,反復打磨每一句話,每一段文字,寫完稿件不滿意時,我甚至再次推倒重寫。
《新華每日電訊》在頭版為我開設“駐邊筆記”專欄,稿件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篇篇都能上頭版,雖然讓我欣喜,但也為之后的采訪寫作帶來了不小壓力。為此,我放棄了原來每周1-2篇的發稿計劃,對已擬定好的線索和題目進行了3次修定,對于不適合刊發頭版的題目果斷摒棄,最終調整為精心打磨20篇稿件。
三、堅守崗位,永葆新華社記者的初心和使命。在楚魯松杰蹲點,面臨的不僅是生活的艱苦,還有精神上的孤獨。近半年時間,進出楚魯松杰鄉的公路被大雪封住,還經常停電斷網。連鄉里的藏族廚師次仁扎西都感慨說:“無聊極了,真想光著屁股到山頂溜一圈。”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孤獨,一種與世隔絕的孤獨。
孤獨也是對年輕記者成長最好的磨練。經歷過就業和換崗的選擇后,重新踏入新聞之路的我,面對問題學會冷靜思考,面對困難會變通處理。作為掛職干部,始終牢記“對黨忠誠、勿忘人民、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新華精神,牢記自己肩負的職責使命。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我扎實采訪調研,累計行程2000余公里,走訪了全鄉70余戶人家,夜宿牧民家12次,采寫了涉及邊境風貌、脫貧攻堅、軍民團結、鄉村干部風采等近30篇稿件。
這次半年多的蹲點經歷,我收獲有三:一是切實體會到增強“四力”的重要性。在蹲點期間,我深刻體會到走進百姓門檻和群眾心坎的必要性,體會到善于觀察判斷的重要性,體會到學會用心、善于思考的意外之喜,體會到增強語言駕馭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的重要性。二是開闊了眼界,增長了才干。不同于以往的蹲點調研,我本身就是鄉黨委和政府的一名干部,要參與到鄉黨委、政府的決策和各項具體事務中來,要帶領干部群眾一起放牧巡邊。既是新華社記者,又是基層干部的“雙重身份”,使我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基層的情況,真正扎根基層,又跳出基層,更加深刻了解中國的國情和西藏的區情。三是收獲了一份溫暖與力量。這份溫暖和力量來自于干部群眾對我的認可和西藏分社對我傾注的關愛。永遠難忘出發時分社領導和同事的殷殷囑托和千里遠送,雪山解封時在深山見到分社同事時的熱淚盈眶,掛職結束時干部群眾依依不舍的那一雙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