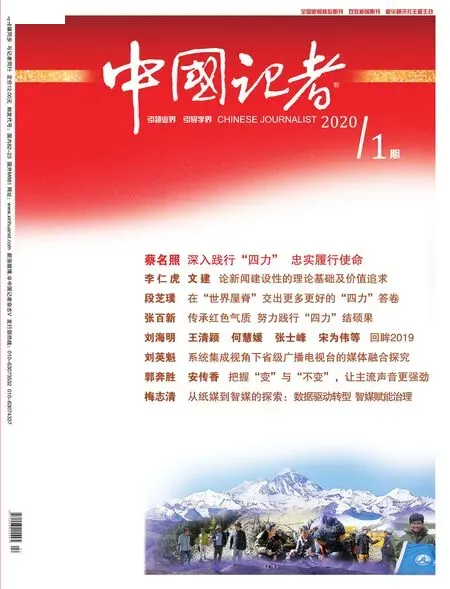用心、用情記錄“小人物”們的2019年
——“工廠小人物”系列攝影專題回顧與展望
□ 宋為偉
這些年,工廠是我常去的地方。每每翻看在那里拍攝的照片,畫面里有父母對孩子深沉的愛,也有孩子對父母的依戀,一張張面孔的背后是再苦再難也要在一起的人間真情。與平日里車間內埋頭忙碌、面無表情的場景不同,當你真正走近這些為生活負重前行的人們,你會發現另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他們”。在歷史的長河里,這些“小人物”們認真用力地生活著,正如你我。在即將告別2019年、邁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之際,用鏡頭記錄他們,正如記錄這個時代下的每一個人,希望每個認真生活的人,都不被生活所負,用影像在歷史的長河里留下一絲漣漪。
外來務工人員是新聞紀實攝影熱衷聚焦的題材。福建民營制造業發達,吸引了大量來自西部農村的勞動力。作為新華社記者,我一直關注外來務工人員題材,用鏡頭反映人口流動和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生態。
從2018年開始,我持續對福建多地的工人家庭進行跟蹤拍攝,其中以在閩南石獅一家服裝廠拍攝的影像最多,形成了“工廠小人物”系列攝影報道,如《爸爸,不要走!》《工廠“小候鳥”守在你身旁》……這些攝影報道在新華社通稿、微信公號和客戶端等渠道播發,不僅新媒體端閱讀量迅速突破10萬、100萬大關,還被《新華每日電訊》《China Daily》等眾多媒體刊登,引發社會關注。
一、以時間為軸線厘清影像故事的情感主線
這些報道鎖定了同一家工廠這一空間要素,在不停向前延伸的時間軸線上,故事主人公與社會產生交集,經歷眾多外來務工人員在融入城市過程中所經歷的酸甜苦辣,以具體事件引發共鳴,找到貫穿每組報道的情感主線,打動自己,打動讀者。
我仍無法忘記第一次走進這家服裝廠的情形——那是2018年1月的一個中午,金利萊斯服裝廠里不少工人已經下樓打飯,而在五樓的縫紉車間里,一對年輕的工人夫婦還在工位上忙碌,他們的孩子“聰聰”伏在一旁吮著手指,直勾勾望著忙碌的母親,眼神里流露出的情緒難以形容。這一刻,時間已凝固,只剩下車間里縫紉機“噠噠噠”的聲音,但我的心卻無法平靜——在城市中,有多少像個他們這樣的家庭,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來到城市,用雙手創造幸福。這不正是“中國夢”的一種微觀寫照嗎?
每次來到工廠,我都會花上幾天時間和工人近距離接觸,接受他們的邀請住進工人宿舍、一同吃飯,靜下心來交流和相處,獲得他們的信任和親近,走進他們的生活,最終捕捉到帶著體溫的影像。
作為長期影像項目,拍攝記錄是第一要務。部分報道,在拍攝前就已確立方向和主題,如《爸爸,不要走!》。拍攝時正值春節前夕,工廠已經放假停工,多年未回四川老家的黃海龍決定獨自回去看望留守家鄉的父母和長子,妻子黃愛華則帶著從小跟父母在工廠生活的“聰聰”回福建娘家過年。這是“聰聰”出生以來第一次經歷離別,回哪里、去還是留,這也是許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輕夫婦每逢春節必做的選擇,我預感到可能“有戲”。在與他們同吃同住記錄了近一周時間后,終于到了離別時刻。原以為三歲的孩子不知道離別的滋味,可當黃海龍坐上大巴車,聰聰就開始哭鬧,哭喊著“爸爸不要走!”在大巴發動的那一刻,隔著車窗玻璃的黃海龍看著哭鬧的聰聰,流下了眼淚。我在一旁默默記錄抓拍一家人在情緒上的起伏變化,這些情緒飽滿的照片將整組影像推向情感高潮。
部分報道在拍攝時僅是先行記錄,但在記錄過程中逐漸提煉梳理出了主線,如《3歲“縫紉機寶貝”的童年,讓人哭著哭著笑了!》是我用了半年時間,在記錄過程中逐漸梳理出聰聰走出朝夕不離的車間、適齡入托的故事主線,并通過積累的大量影像素材進行對比,烘托出先抑后揚的情感主線,讓讀者為“聰聰”的童年生活揪心之余,也看到了他融入幼兒園后的可喜變化。
值得關注的是,連續兩年暑假,我都以“車間里的假期”為主題,報道了利用假期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工廠與父母團圓的“小候鳥”的故事。不同的是,第一年的報道《車間里的暑假》淡化了個體故事,只是簡單用影像記錄現象,沒有系統深入地挖掘人物故事;而第二年假期報道《工廠“小候鳥”守在你身旁》則更側重挖掘人物故事,提煉人物情感,報道更具深度,也更注重光影對主題的烘托和表達。這兩次報道主題相似,但都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新華時評、澎湃等就“暑期誰來帶孩子”“城鎮化過程中雙職工子女假期陪伴”等民生關切發表多篇評論。

□ 2018年1月11日,在福建省石獅市金利萊斯服裝廠,聰聰望著在一旁忙碌的母親黃愛華。(宋為偉/攝)
同一個主題的兩次報道,均能產生較大反響,究其原因在于這一現象和話題的普遍性,易于與受眾產生共鳴。新媒體時代,手機是一個個移動的“窗口”,“窗口”背后有眾多曾經或正在城市打拼的“小人物”,他們能從這樣的“小人物”故事中找到些許相似的體驗、汲取溫情,或許能找到自己。
二、尋找影像報道的小切口
我的此類攝影報道均以孩子作為影像記錄的切入點。在目前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的背景下,人的流動是必然現象,而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亦被裹挾在其中。他們有自身的情感需求,有無奈、有身不由己。他們對幸福有自己的定義,而這一切,正是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社會特征。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孩子承載了家庭的期望,他們的成長備受社會關注,容易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關于孩子、“小候鳥”、打工子弟的新聞攝影作品也有許多,但比較零散,在時間和空間上缺乏縱深,不利于從發展的角度去衡量和觀察社會變化,難以發揮影像的史料價值。
我所拍攝的孩子分為兩類,一類是平時留守家鄉、假期來工廠與父母團聚的“小候鳥”,還有一類是與父母一起生活并在當地上學的打工子弟。我以家庭為單位對他們進行長線跟蹤記錄。1年、2年、10年,孩子的成長是顯性的、發展的,他們不斷與家庭成員和社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我認為,從拍攝孩子入手來記錄與其相關的人和事,能較好地反映整個家庭和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在長期影像項目上是很好的拍攝參照物。
以時間為軸線,將影像記錄堅持下去,記錄這些從農村到城市的“小人物”,記錄城鎮化進程和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這樣的影像實踐有不可替代的社會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