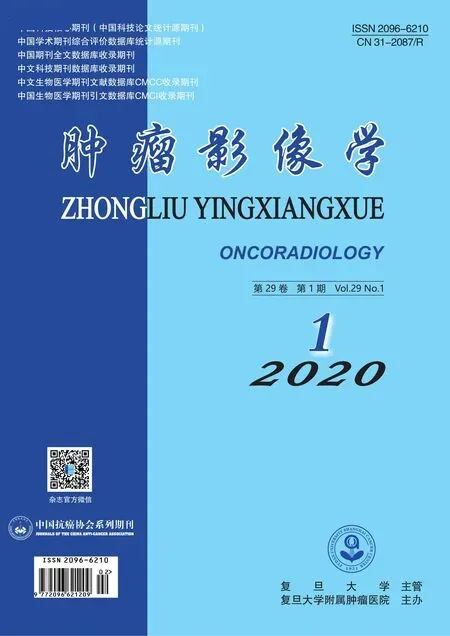超聲造影對乳腺影像報告和數據系統4a類腫塊的診斷價值
福建省腫瘤醫院,福建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超聲科,福建 福州 350014
乳腺癌是威脅女性健康的常見惡性腫瘤之一,早期診療可明顯改善其預后[1]。常規超聲在乳腺癌的篩查與診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良惡性病變的聲像圖存在較多重疊,尤其是對于理論惡性風險僅為3%~10%的乳腺影像報告和數據系統(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 4a類腫塊[2]。超聲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作為一種純血池顯像技術,有助于顯示病灶的微灌注[3-4]。有研究顯示,CEUS可提高乳腺良惡性腫塊診斷的準確率[5-8],具有較高的陰性預測值[9],可降低BI-RADS 4、5類病灶的假陽性率[10-12]。本研究對常規超聲診斷為BI-RADS 4a類的乳腺腫塊進行CEUS檢查,旨在準確判斷BI-RADS 4a類乳腺腫塊的性質,以減少不必要的穿刺活檢。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5年9月—2018年8月常規超聲檢查診斷為BI-RADS 4a類的乳腺腫塊患者156例,最終經過粗針穿刺或手術后病理學檢查納入148例,共149個腫塊。患者均為女性,年齡18~76歲(中位年齡44歲)。腫塊最大徑4.7~85.0 mm。排除標準:年齡小于18歲;孕期或哺乳期婦女;隆胸假體植入術后患者;正在接受化療或放療的患者;CEUS聲像圖質量差影響判讀者;不愿或不能簽署知情同意書者。本研究經福建省腫瘤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CEUS前及穿刺活檢前均獲得了所有患者的知情同意。
1.2 儀器與方法
儀器采用荷蘭Philips公司的iU Elite、iU 22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L12-5、L9-3頻率分別為5~12、3~9 MHz,造影前先用L12-5探頭檢查并記錄腫塊的大小、位置、方向、形態、邊緣、回聲、后方回聲變化、有無鈣化、周圍導管有無擴張、血流信號及腋窩淋巴結等情況,并選擇最佳切面,采用L9-3探頭進入造影模式,造影時注意病灶周圍留有足夠的正常乳腺組織與之作對比,當病灶較大時(L9-3探頭不能完整顯示的病灶),選擇低頻凸陣探頭(頻率3.5~5.0 MHz)或選擇病灶邊緣與正常組織交界部分行CEUS。調整聚焦點及增益,使造影圖像質量清晰可靠。采用意大利Bracco公司的聲諾維(SonoVue),造影前向SonoVue凍干粉末中注入5.0 mL的0.9% NaCl溶液,反復震蕩后制成六氟化硫微泡懸濁液。抽吸4.8 mL造影劑經肘靜脈快速團注,隨即快速推注0.9% NaCl溶液5.0 mL,存儲觀察病灶的動態灌注過程2 min,其中前1 min保持同一切面固定不動,之后動態掃查整個病灶,造影后選擇前1 min穩定視頻行定量分析。
1.3 圖像分析
乳腺腫塊的CEUS表現由2位有2年以上工作經驗的醫師共同完成,意見不一致時,二者協商后決定。觀察分析CEUS增強表現:增強時間(慢進、同進、快進),增強強度(低增強、等增強、高增強),增強順序(向心性、非向心性),增強后病灶范圍(難以分辨、縮小、不變、擴大),增強均勻性(均勻、不均勻),增強完整性(完整、不完整),增強后邊緣(難以分辨、清楚、不清楚),增強后形態(難以分辨 、規則、不規則),滋養血管(有、無),蟹足征(有、無)。造影后時間-強度曲線參數通過QLAB軟件勾勒病灶與周圍正常組織的感興趣區進行分析,參數包括峰值強度、曲線下面積、上升斜率及達峰時間。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2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各計量資料經正態性檢驗及方差齊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及方差齊性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非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用相對數表示,其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惡性腫塊在CEUS中的優勢比征象,并調整腫塊的BI-RADS分類,診斷性能的比較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149個BI-RADS 4a類乳腺腫塊中,良性病灶112個(75.17%),其中腺纖維瘤52個,導管內乳頭狀瘤15個,腺病30個,炎性反應14個,假血管瘤樣間質增生1個;惡性病灶37個(24.83%),其中浸潤性導管癌25個,浸潤性小葉癌1個,導管原位癌7個,實性乳頭狀癌1個,交界性葉狀腫瘤3個。病灶最大徑為4.7~85.0 mm(表1)。

表 1 149個BI-RADS 4a類乳腺病灶的基本信息
與良性病灶組相比,惡性病灶組患者在BMI、家族史、病灶的最大徑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在患者年齡、腋窩淋巴結陽性方面均高于良性病灶組患者(P<0.05)。
149個乳腺良惡性病灶CEUS結果顯示,惡性病灶表現為快進高增強,增強后形態不規則,邊界不清楚,病灶范圍擴大,或伴有滋養血管或有蟹足征,與良性病灶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149個乳腺良惡性病灶CEUS增強表現見表2。

表 2 149個乳腺良惡性病灶CEUS增強表現
以增強強度、增強時相、滋養血管、增強后病灶范圍、蟹足征、增強后邊界、增強后形態為自變量進行二分類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顯示,增強后病灶有無滋養血管、病灶形態是否規則與惡性病灶呈獨立相關性,其中增強后病灶有滋養血管較無滋養血管的惡性概率高15.79倍,而增強后形態不規則較形態規則的惡性概率高4.32倍。乳腺良惡性病灶CEUS表現二分類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表 3 乳腺良惡性病灶CEUS表現二分類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
以CEUS增強后形態不規則及有滋養血管為惡性指標對BI-RADS 4a類病灶進行重新分類,兩個指標均為陰性的病灶降為3類,其中一個指標為陽性的分類保持不變,兩個指標均為陽性則升到4b類。149個BI-RADS 4a類病灶經CEUS重新分類后:3類83個,4a類57個,4b類9個。3類病灶由原來的0個增加了83個(占55.70%),以CEUS BI-RADS 4a為活檢閾值,活檢率由造影前的100.00%降低至44.30%,癌癥檢出率由24.83%升高至51.52%,而允許隨訪患者的惡性風險僅2.01%,與BI-RADS分類標準規定3類允許隨訪的惡性風險2%相近,顯著減少了穿刺活檢的患者數(表4)。降類后的3個惡性病灶包括浸潤性癌2個,交界性葉狀腫瘤1個,其中交界性葉狀腫瘤(最大徑>5 cm)為良性表現,即快進高增強、增強后病灶大小不變、無滋養血管、無蟹足征、增強后形態規則、邊界清楚;2個浸潤性癌同樣為良性表現,即與周圍腺體同進等增強,形態及邊界難以分辨、無蟹足征、無滋養血管。2例浸潤性癌均伴有腋窩淋巴結異常。

表 4 造影前后活檢率、惡性風險及癌癥檢出率的變化
149個4a類乳腺病灶CEUS時間-強度曲線參數見表5。惡性病灶達峰強度、曲線下面積、上升斜率均顯著高于良性病灶,分別為(8.87±3.56vs6.79±3.12,P<0.05)、(260.38±122.38vs207.61±108.73,P<0.05)、(0.85±0.32vs0.68±0.36,P<0.0 5),達峰時間短于良性病灶,為(16.62±4.24vs18.29±6.67),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 5 149例4a類乳腺病灶CEUS時間-強度曲線參數
乳腺BI-RADS 4a類病灶ROC曲線的曲線下面積為0.500(95% CI:0.392~0.680)。經CEUS調整后BI-RADS分類ROC曲線的曲線下面積為0.835(95% CI:0.764~0.907),兩者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經CEUS調整后行BI-RADS分類診斷效能更高(圖1)。

圖 1 乳腺病灶CEUS后修正BI-RADS分類診斷效能的ROC曲線圖

圖 2 BI-RADS 4a類腫塊超聲表現(術后病理學檢查為浸潤性導管癌)
3 討 論
乳腺超聲BI-RADS分類在乳腺病灶良惡性評估方面具較高的應用價值,其中BI-RADS 4a類腫塊的惡性風險為3%~10%,推薦組織學活檢。本研究結果中,149個BI-RADS 4a病灶最終組織病理學檢查顯示惡性檢出率為24.83%(37/149),表明大部分良性病變經歷不必要的穿刺活檢或手術。
Nakopoulou等[13]研究發現,相較于良性腫塊,惡性病灶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表達增多,血管壁通透性增高,動靜脈瘺、腫瘤內部血管不規則的發生率高。亦有文獻[3]報道乳腺癌病灶外周血管分布更廣,分布不均勻,且血管彎曲、形態不規則。由于常規超聲對低速血流信號不敏感,難以顯示腫瘤微血管結構,限制了其在腫瘤新生血管評估中的作用;而CEUS可以清晰地顯示腫瘤微血管灌注模式,從影像學的角度體現良惡性病灶的血流動力學差異,可作為超聲BI-RADS分類的重要補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過度診療[14-16]。
本研究通過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惡性腫塊的優勢比是病灶的滋養血管陽性及增強后形態不規則。以該兩項指標對BI-RADS 4a類腫塊進行重新分類后,3類病灶由原來的0個增加為83個(占55.70%)。以4a類為活檢閾值,活檢率由100.00%降低至44.30%,癌癥檢出率由24.83%升高至51.52%,ROC曲線的曲線下面積由0.500增加到0.835,表明CEUS比常規超聲具有更高的診斷效能。重新分類后83個病灶可避免穿刺活檢,而允許隨訪患者的惡性風險約2.01%,與BI-RADS分類系統規定3類允許隨訪的惡性風險2%相近。因此對于BI-RADS 4a類病灶,可通過常規超聲聯合CEUS降低活檢率,避免醫療資源浪費。
CEUS降類后,出現3個假陰性病灶,包括浸潤性癌2個、交界性葉狀腫瘤1個。其中1個交界性葉狀腫瘤(最大徑>5 cm)為CEUS良性表現,即快進高增強、增強后病灶大小不變、無滋養血管、無蟹足征、增強后形態規則,分析其原因,可能與腫瘤巨大,采用低頻探頭探測而影響對CEUS特征的觀察有關。而另外2個浸潤性癌同樣為良性表現,即與周圍腺體同進等增強,形態及邊界難以分辨、無蟹足征、無滋養血管,這2個病灶較小,最大徑在1 cm左右,均是臨床發現腋窩異常淋巴結后懷疑乳腺病變就診。病變大小與腫瘤血管生成高度相關[17],部分較小的惡性病變新生血管不豐富,異質性不明顯,CEUS可表現良性的增強特征[18-19],因此對于1 cm左右的可疑惡性結節仍需要穿刺活檢,同時注意對腋窩淋巴結的探測,避免漏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的14個非哺乳期炎性病灶中,13個病灶CEUS表現為快進、高增強、增強后病灶范圍擴大,其中1個可見滋養血管、10個增強后形態不規則;由于炎性反應細胞可向周圍組織浸潤,血管擴張,血供豐富,可出現與惡性腫瘤相似的CEUS特征[8],因此需要根據患者的癥狀及相關化驗指標綜合分析,穿刺活檢有助于鑒別。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研究,患者數較少;參與本研究的醫師盡管具備行乳腺CEUS的經驗,但乳腺CEUS的檢查和判讀標準仍在探討之中,不同的醫師及不同的CEUS觀察切面對結果仍會有影響;本研究中部分患者僅有粗針穿刺的病理學檢查結果,可能存在低估問題。
綜上所述,對乳腺BI-RADS 4a類病灶行CEUS可以提供進一步的診斷信息,優化BIRADS分類,減少不必要的穿刺活檢或手術,對臨床決策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