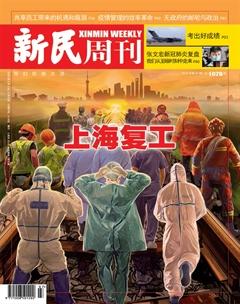粟特人的活躍:唐帝國興衰的真正奧秘
鄭渝川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日)森安孝夫著 譯者:石曉軍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1月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這本書有一大主角:粟特人。
在《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一書的序言中,長期致力于中央歐亞史研究的日本歷史學家、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安孝夫批駁了日本在內東亞國家歷史學界一些人的所謂“自虐史觀”。日本保守右翼人士將反省日本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中期的對外擴張、侵略的歷史學研究,貶低為“自虐史觀”;但在森安孝夫看來,真正的“自虐史觀”,其實是那種秉持了西方中心史觀,毫無憑據(jù)和理由的貶低東亞、亞洲古代歷史發(fā)展的成就,在探討歷史上的沖突、問題時不假思索地站在歐洲、西方的立場,將亞洲、東方視為敵對方的做法,而該做法在日本等東亞國家的歷史學界頗具代表性。
當然,擺脫西方中心史觀,不等于要陷入東亞、古代中國“唯一”、“獨特”的反向偏狹。從蒙古高原東麓一直到西麓,跨越天山山脈、中亞、烏拉爾山脈,直抵里海、高加索山脈、黑海,都可稱為所謂的中央歐亞地區(qū)。這一地區(qū)在巨大的山麓和山脈之間有許多遼闊的草原,沒有涌現(xiàn)所謂的古代文明古國,而是成為了一次次沖擊各大文明古國的游牧民族的策源地。《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書中指出,“從四大文明圈發(fā)展起來的農(nóng)耕民與從中央歐亞發(fā)展起來的騎馬游牧民之間的對立、抗爭、協(xié)調、共生、融合等關系之中”,才孕育了包括東亞文明在內的古代文明。
4世紀至9世紀之間,我們今天所稱的絲綢之路東段,粟特人是擔綱貿(mào)易、文化往來的重要甚至主要角色。粟特語也成為當時的國際語言。粟特人在人種學上屬于白色人種,粟特語是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中古伊朗語的東支。粟特人離開伊朗故地后,向東發(fā)展,其文字傳入突厥、回鶻,并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回鶻文字;13世紀,回鶻文字中產(chǎn)生了蒙古文字;17世紀,基于蒙古文字轉化出了滿文。
6世紀前后,粟特人中的精英開始在中國中原王朝(北方)中脫穎而出,涌現(xiàn)出不在少數(shù)的政治、外交、軍事精英。粟特人精英在參與中國中原王朝的政治時,有意像之前漢朝、三國時期的漢族世家那樣,對不同勢力各自“下注”,以確保贏得權勢對粟特人勢力把控西域商路的支持。唐高祖進入長安后,涼州的粟特人首領安興貴、安修仁兄弟發(fā)動政變,拘捕了當?shù)剀婇y李軌,將涼州獻給了唐朝;而安興貴之子安元壽則成為了李世民的輔佐者,曾在玄武門之變中發(fā)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即調動粟特人兵馬給予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方較大的打擊。
毫無疑問,隋唐兩朝的皇族,以及作為朝廷柱石的關隴集團,其實都帶有相當程度的鮮卑裔血統(tǒng)——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到唐代,匈奴、鮮卑、氐、柔然、高車、突厥、鐵勒、吐谷渾、葛邏祿、奚等族,都相當活躍,也逐步融合進入了之前狹義上的漢民族。而安史之亂爆發(fā)后,不僅宣告了盛唐時代的結束,而且也導致唐王朝從過去意義上的兼容、多元化帝國轉為了更趨單一保守的傳統(tǒng)王朝。安祿山和史思明在內的安史集團,多由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漢人組成,并獲得了粟特商業(yè)體系的資金支持。而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亂,得益于回鶻的支援。突厥裔的回鶻在唐王朝由盛轉衰過程中崛起,很快成為了與唐、吐蕃分庭抗禮,掌控西域和蒙古高原的新霸主。
書訊
《兩棲爬行動物的神話與傳說》
本書是一首關于蟾蜍和蛇、蠑螈和蜥蜴、鱷魚和烏龜?shù)捻灨琛T谶@本書里,爬蟲學家兼科普作家馬蒂·克倫普探索了世界各地從古至今的民間傳說。從創(chuàng)世神話到小道消息,從生育和重生到火災和雨水,從兩棲爬行動物在民間醫(yī)藥和魔法中的用途到它們在文學、視覺藝術、音樂和舞蹈中扮演的角色,克倫普揭示了我們?yōu)槭裁磿@些動物又愛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