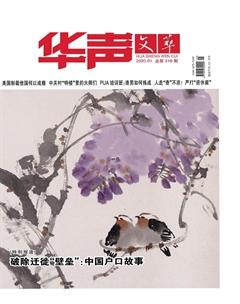被科學真理誘惑了70年
胡春艷

92歲這年,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我國著名煉油工程技術專家陳俊武稍稍放慢了速度——他把每周上班的時間減至3天。連續工作幾小時后,他可能需要睡上一大覺才能恢復體力。他工作了70年,跨越了兩個世紀,是中國最年長的“上班族”之一。“不搞創新就要落后于別人”的緊迫感自始至終催促著他一直“想方設法地創新”,90多歲了依舊覺得“還有一些精力,可以作些貢獻”。70年間,他為中國煉油工業的催化裂化技術作出一系列開創性貢獻,給我國高速前進的現代工業注入源源不斷的“能量”。
把自己的本事 用在國家需要的地方
陳俊武對化學著迷是從中學時代開始的。他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系,就是認準了要學好將來振興民族工業的實用知識。大二那年,陳俊武和同學一起到東北的撫順參觀,在日本人留下的頁巖煉油廠里,他第一次見到了一座日本人丟棄、尚未開起來的煤制油裝置,怦然心動。
“石油”成了他心中縈繞不去的牽掛,陳俊武把4年青春歲月揉進書頁和筆記之中。
他寫道:“科學真理把我誘惑得太苦了,生命的意義全寄托在沒有生命的分子、原子上了。”很快,他又給自己打氣,“外面的春天與我何干!最重要的是,讓內心充滿芬芳。”“我要使平凡的日子變得不平凡。”
畢業之際,陳俊武清楚,石油作為“工業的血液”將給整個國家的發展注入強大生命力。沈陽是東北最大的工業城市,工作生活條件優越,陳俊武的母親和家人都在那邊。陳俊武卻直奔撫順而去。他一頭扎進車間,干起了人造石油工廠的修復工程。顧敬心擔任當時項目總工程師,這位中國化工行業的元老撂下一句話:“這個項目搞不好,我就不刮胡子!”
盡管技術資料匱乏、生產條件簡陋,可因為“國家急需”,大家全都沒日沒夜地攻關,以最快的速度恢復生產。
陳俊武愛琢磨,他分析高速氣流原理后進行參數計算,又泡在車間與技術專家、老工人一起試驗,最終革新了蒸汽噴射器技術,一臺鼓風機1小時能省電25度。這次革新掀起了全廠創新的熱潮,也點燃了陳俊武心中的熱情。
當時原油產量劇增,可煉油廠加工能力不足,為了設計一種投資少、上馬快,對原油只需要中等程度加工的煉油裝置,陳俊武大膽提出蒸餾——催化聯合裝置的設計技術革新方案,并試運成功。1978年,陳俊武從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捧回了紅絨面燙金證書。那年,他出任洛陽煉油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由他指導設計的中國第一套快速床流化催化裂化裝置在烏魯木齊煉油廠試運成功,他指導設計的中國第一套120萬噸/年全提升管催化裂化裝置在浙江鎮海煉油廠開車成功。讓中國的煉油技術特別是催化裂化技術迎頭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時至今日,我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催化裂化世界第二大國。
一項技術把我國煉油技術 向前推進20年
1961年冬,當時的石油工業部決定開展5項煉油工藝新技術攻關,盡快改變我國煉油工業技術落后的面貌。這5個被稱為煉油工業“五朵金花”的項目,更像是橫亙在中國煉油工業前進道路上的“五座大山”。其中,流化催化裂化是煉油工業的關鍵技術,投資少、費用低、原料適應性強,是石油煉制中最重要的加工工藝之一。那個時代,這類裝置國外封鎖了最新技術。34歲的陳俊武受命擔任我國第一套催化裂化裝置的設計師。
難度有多大?陳俊武舉例說:好比一群從來沒見過大象的人,只摸到一只象耳朵、一條象尾巴,卻必須要畫出一頭完整的大象。
為了完成任務,陳俊武常常一天伏案十幾個小時,閉上眼睛眼前全是數據和方案。后來他作為技術骨干被派往國外學習,抱著“寶貝”回來后,陳俊武和技術人員干脆就住在干餾爐旁的簡易房里,睡大通鋪,爭分奪秒設計適合中國使用的一整套流化催化裂化裝置。4年后,這個由我國自主開發、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安裝的第一朵“金花”——催化裂化裝置一次投產成功,把我國煉油技術一舉往前推進了20年。
60多歲時,他將研究方向轉向國家石油替代戰略,與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合作,指導完成了甲醇制烯烴(DMTO)技術工業放大及其工業化推廣應用,為我國煤炭資源深度轉化利用開辟了全新技術路線,該技術榮獲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80歲以后,陳俊武又開始深入關注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化、碳減排等課題,為國家碳排放政策提供了關鍵決策意見。
他有一句名言,被很多人記下,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很多人的人生態度:“奉獻小于索取,人生就暗淡;奉獻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獻大于索取,人生就燦爛。”
陳俊武回顧自己追求創新的人生時說:“終歸是成功多于失敗,也取得了一些比較重大的成績。這樣回想起來,大抵是讓人心情比較愉悅的。”
科研道路上經歷的那些失敗,在他看來無非是證明了這條路走不通,“你探路了,別人可以吸取經驗教訓”,只要認真地走,“走不通也是一種前進”。
他覺得自己確實是“運氣很好”,抓住了人生和整個國家的發展機遇,也找到了可以展示才華的舞臺。
最近他剛剛統計了中國院士的平均壽命,想看看哪個學科的學者最長壽。“我已經活過了平均壽命。”他笑著說,還要再接再厲。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