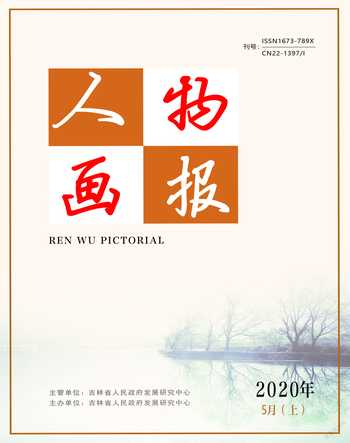文化淵源中的經典
摘 要:《詩經》和《圣經》兩部經典作品作為中西文化的淵源之一,具有較強的可比性,本文從創作模式相似性進行了可比性研究探討。
關鍵詞:《詩經》;《圣經》;創作模式
一、《詩經》和《圣經》具有可比性
《詩經》和《圣經》是中西方文化的淵源之一,要想弄清楚中西方文化的真諦,人們都喜歡從這兩部經典中去尋找答案。郭錦玲在她的博士論文《意蘊不同的經典——從<詩經>和<圣經>看中西方文化精神與藝術思維的原始差異》中早有研究。關于《詩經》和《圣經》是否可以列入文學著作,并且從主題的角度進行比較,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詩經》被尊稱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肯定可以列入文學范疇的。通常人們都會把《圣經》歸入宗教典籍中,然而,隨著人們越來越多的從《圣經》中解讀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和語言藝術審美,《圣經》的文學性也逐漸被人們認可。王新球就曾經出版過一本《<圣經>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性》,書中對《圣經》的文學性予以肯定。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審視兩者所存在的可比性。首先,世界萬物皆有可比性。異域作家、兩部作品之間,往往存在著多方面的邏輯聯系,即是說可以找到“第三者”將它們聯系起來,那就是今天我們可以從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架設在兩部經典之間的橋梁。其次,高爾基曾經說過“文學即人學”,文學是人對萬事萬物的感受和理解而進行的創作,從一定意義上講,人心即文心。有許多人類共同的東西都是文學所描寫的對象,于是文學也成為解讀人類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規律和本質的一種途徑。《詩經》和《圣經》作為中西方文化文化淵源的代表作,自然也是早期先民對社會和自然的理解,他們面對著同一個客觀世界,有著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欲求,共同的磨難,共同的困惑,共同的感受,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者,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人類審美活動的物化形態之一。有自己的一套生產和發展的規律,有自己的特性,這些規律和特性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民族之間,既會表現出它們的差異性,也會表現出它們的共同性。《詩經》和《圣經》中就都具有詩歌體裁,祭祀、戰爭和情愛主題,體現了道德和欲望,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神、人和王之間的矛盾和融合。最后,現今比較文學領域中,也涌現出不少拿兩部經典來比較的案例。
二、創作模式相似
遠古時期,由于生產力低下,社會活動單純,語言貧乏,古人在對大自然奧秘的探尋中,對人類自身矛盾和問題的思考的背景下創作這兩部經典。皆呈現出屬于民間和文人混雜創作,由后人編纂,歷史跨越時間較長,出現真偽之說等相似的創作模式特點。
根據《圣經是怎樣寫成的》一書的介紹,《舊約》陸續成書于公元前5世紀——前2世紀,1世紀定型為39卷,《新約》共27卷,成書于公元4世紀。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考證舊約是由誰來創作的,但有個共同的觀點,舊約是屬于民間口頭創作。其中《詩篇》最早,產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紀王國形成時期:《哀歌》是巴比倫之囚(約公元前586年發生)以后即公元前6世紀左右形成;《雅歌》的成型時期多有爭議,而根據《雅歌》中已有地租的記載,當是在封建制度形成以后,即大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之間;《約伯記》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前3世紀希臘化時期;《傳道書》形成于公元前2世紀;《篇言》成書于公元前3世紀。在文字和紙張尚未出現公元前時代,人們對神的崇拜和對歷史的記載往往是口耳相傳的,從《圣經》舊約產生的年代就可以看出,大多數內容口是民間口頭傳作的。而且在傳播的途中,由于是經過不同的人傳唱,其中不乏有許多內容是重復,而且還相會矛盾。
如果從語言的口耳相傳的角度看,其實也口耳相傳時出現誤傳的一中表現,這時候是人們因為沒有文本參照,靠自己的背誦來記憶的話,所以期間會有疏漏的地方。這也能證明《圣經》舊約主要是民間口頭創作的。
新舊約的劃分是以耶穌出生為界限的,新約由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使徒書信和啟示錄組成。使徒書信分保羅書信和一般書信;保羅書信又分教會書信、個人書信、監獄書信和希伯來書。《新約全書》的數量比較一致,都有27卷。《新約圣經》正典書目,于公元397年舉行的迦太基會議正式確定。其原本已失傳,現所發現的最早抄本殘片約為公元2世紀時所抄。在公元4世紀新約文本大致固定后,有埃及、亞歷山大、敘利亞等抄本流行。目前保存的最早希臘文《圣經》抄本為4~5世紀的抄本,最著名的有西奈抄本、梵蒂岡抄本和亞歷山大抄本。在這些抄本中都明確提出作者是說,并以作者的名字來命名。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關于《詩經》的編集,漢代有兩種說法:第一是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經》305 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也能證明《詩經》是采自民間口頭的文學作品。第二是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從《詩經》的內容來看,尤其是國風中,大多記載的民間各種活動時人們傳唱的內容。且《詩經》是民間口頭創作和部分有文人創作的理論已經被大多數人認可。
《詩經》大約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 8 歲 。 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 。 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后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流傳下來,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而今,由于《詩經》經歷秦毀漢建的歷程,學界也還在辨別齊、魯、韓、毛詩之真偽。
參考文獻:
郭錦玲 意蘊不同的經典——從《詩經》和《圣經》看中西方文化精神與藝術思維的原始差異[J]? 暨南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肖紅艷(1979-)女,漢,籍貫:湖南武岡市,職稱:講師,碩士學位,研究方向:文學、新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