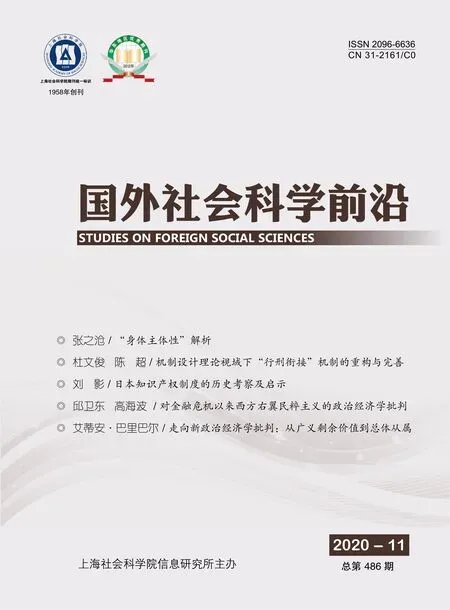新聞的算法推薦與公民的政治社會化 *
萬旋傲
內容提要|算法推薦介入新聞業,個性化新聞流替代傳統媒體新聞流,這會對公民政治社會化過程有什么影響,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研究發現,雖然人們的偏好和需求在塑造個人的政治信息環境越來越重要,但是算法推薦并沒有整體提升公民的政治新聞供給數量和質量。相反,新聞消費者的偏好正在推動媒體犧牲硬新聞,提供更多軟新聞,這一趨勢并不利于公民的政治學習和政治知識積累。主動尋找政治新聞的人與不主動尋找政治新聞的人、高教育水平的人與低教育水平的人,在個性化新聞環境中的政治知識差距一再增大。盡管算法推薦也給許多人提供了偶然接觸和學習政治的機會,但是缺乏深度的認知加工也導致偶然學習的效果并不理想。同時,算法推薦進一步強化了選擇性曝光效應,促使圍繞政治問題、公共事件的輿論態度出現兩極分化與相互對立的格局。算法推薦甚至還成為了政治操縱的工具,影響公民的線上和線下政治行為。厘清算法推薦對公民政治社會化帶來的可能性風險,對于國家、平臺、算法機構和公民參與算法治理十分重要。
政治社會化通常指塑造個人在政治體系中的角色的過程,①Justin Martin, News Us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mong Young Jordania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73, 2011, pp. 706-731.或從公民的角度定義為人們習得政治知識、規范、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模式的過程。②Anastasia Kononova, Saleem Alhabash and Fritz Cropp,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3, 2011, pp. 302-321.政治社會化有助于政府與其公民之間的互動,是政府進行有效統治和社會管理的基礎。家庭、學校、同伴和大眾媒體被認為是政治社會化的主要來源,其中,大眾媒體逐漸成為公民的主要政治信息源,其政治社會化的作用日益凸顯,有時甚至超過了家庭和學校。③Steven Chaffee and Stacey Frank Kanihan,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from the Mass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4,1997, pp. 421-430.然而,伴隨著媒介技術的迭代發展,人工智能和算法深度介入新聞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智能媒體時代已全面開啟:《紐約時報》、BuzzFeed 和Mashable 等都借用各種算法來決定哪些新聞內容、在什么時間將通過其社交媒體賬戶對外分發;Facebook 上有多達6000 萬機器人用戶被算法操縱,通過自動發布和傳播政治信息(其中包含大量的假新聞)影響2016 年美國大選;越來越多的新聞媒體直接使用機器作為新聞代理,進行新聞編寫、來源驗證、內容核查和分發;我國的新浪微博、今日頭條、一點資訊、騰訊新聞等重要新聞源,都紛紛創立或轉型成為個性化的算法推薦新聞平臺,通過用戶的社交關系、搜索記錄、瀏覽歷史、互聯網使用軌跡等指標來計算用戶的新聞偏好,實現精準化推薦。在算法推薦時代,千人千面的個性化新聞資訊成為現實,人們的所聞所見所想都受到了算法的全面規制和影響,其無形之中產生的一系列政治效應和政治后果引人關注:算法推薦塑造的政治信息環境是否促進人們接觸了更多的政治和時事新聞,是否增加了人們的政治知識積累,減小亦或擴大了公民的政治知識差距?是否影響了人們的政治態度,加劇政治分化和政治分歧?對人們的在線政治參與行為和離線政治參與行為有什么影響?概括而言,算法推薦在公民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這是一個令人期待同時又飽含爭議的新興議題,亟需更多實證研究對不同政治語境的現象進行多維論證。目前,圍繞該議題出現的理論假說、預測已反映了一定的問題,值得我們審視和討論。
一、算法推薦的興起
算法推薦被定義為根據用戶的偏好從超集中選擇一組對象的系統。①Alejandro Montes-García, Jose María álvarez-Rodríguez,Jose Emilio Labra-Gayo and Marcos Martínez-Merino, Towards AJournalist-based News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e Wesomender Approach,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vol. 40,2013, pp. 6735-6741.其最早發源于美國,1992 年開始,GroupLens 對美國論壇Usenet 中的消息進行排序,向用戶推薦他們可能感興趣但尚未自行發現的話題,其后來成立的Net Perceptions 一度成為領先的算法推薦公司。②Joseph Konstan and John Riedl, Deconstructing Recommender Systems, https://spectrum.ieee.org/computing/software/deconstructing-recommender-systems.此后,幾種可用于不同領域的推薦系統陸續被開發出來,并被證明可有效地進行個性化的信息過濾,學者馬爾科· 巴 拉巴諾威客(Marko Balabanovi?)和約阿夫· 肖漢姆(Yoav Shoham)將其分類為:基于內容的推薦——提取用戶喜歡的項目屬性;協同過濾推薦——推薦具有相似興趣和品味的用戶的使用項目;混合推薦——混合內容推薦和協同過濾推薦。③Marko Balabanovi? and Yoav Shoham, Content-based,Collaborative Recommendat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40, 1997, pp. 66-72.在物質表象上,算法推薦系統是一串代碼,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部署時才有技術輸出的意義。然而,算法推薦作為一種以自動化決策為導向的技術,它在馴服海量信息浪潮的同時,也取代了新聞守門人、議程設置者、信息中介的角色,決定著社會的信息分布、排列組合,深刻建構著人們的輿論、認知、政治和社會文化生活。學者麥克· 阿納尼(Mike Ananny)敏銳地把握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算法被看作是與社會、技術相關的一種話語和知識文化,這涉及在算法結構中,信息如何生產出來、如何浮現在我們面前,以及我們如何來理解這些信息,這些信息是如何被看作是合法的,又是如何被賦予公共意義的。”④Mike Ananny, Toward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Observation, Probability, and Timeliness,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vol. 41, 2016, pp. 93-117.與之相應地,算法推薦的風險與責任也成為不可逃避的話題。算法操縱、歧視、回聲室效應、過濾氣泡、威脅數據隱私、限制交流與表達、影響人類大腦和認知能力、社會異化等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擔憂。①Michael Latzer, et al., Algorithmische Selektion im Internet: ?konomie und Politik Automatisierter Relevanzzuweisung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Abteilungfu?r Medienwandel &Innovation, Universit?tZürich, IPMZ, Forschungsbericht, 2014.但由于算法推薦系統有賴于復雜的機器學習能力,算法的推薦過程具有天然的不透明性,并缺少可解讀的數學技術,因此,算法經常被描述為“黑箱”②Tarleton Gillespie,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 in Tarleton Gillespie, Pablo Boczkowski and Kirsten Foot (eds.),Media Technolo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pp. 167-194.,致使算法推薦出現錯誤決策、偏見決策甚至破壞性決策時,既難以被察覺,也缺乏較好的治理手段。正如伊萊· 帕里澤(Eli Pariser)所說,算法“通過控制我們看到的和看不到的東西,無形地改變我們所經歷的世界”。③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盡管如此,算法推薦和個性化信息仍然不可阻擋地正在變成新聞消費的主流形式,算法技術也在理性主義的批判中、科技限度的反思中、人文主義的審視中,不斷地發展和擴張著。此時,如何確保理論走在科技前面,尤為重要。
二、理解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理論在20 世紀50 年代逐漸發展起來,其概念和內涵闡釋十分豐富。1959年,第一部以《政治社會化》命名的著作問世,作者赫伯特· 海曼(Herbert Hyman)從政治心理的角度闡釋政治社會化為“通過各種社會機構調節的社會模式的學習過程”。④Herbert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1960 年,美國政治學家大衛· 伊斯頓(David Easton)和羅伯特· 海斯(Robert Hess)基于對美國兒童政治取向的調查研究,將政治社會化解釋為“人們習得政治取向的過程”,這種政治取向由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和評估標準組成。⑤Robert Hess and David Easton, The Child’s Changing Image of the Presiden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4,1960, pp. 632-644.⑥David Easton and Robert Hess, The Child’s Political World,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1962, pp. 229-246.加里布埃爾· 亞伯拉罕· 阿爾蒙德(GabrielAbrahamAlmond)和賓厄姆·鮑威爾(BinghamPowell)也曾論述,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每個政治體系都有某些執行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結構,它們影響政治態度,灌輸政治價值觀念,把政治行動技能傳授給公民。⑦[美]加里布埃爾·亞伯拉罕·阿爾蒙德、小G. 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培林、鄭世平、公婷、陳峰譯,東方出版社,2007 年,第83 頁。當代一大批學者也分別從各個視角對政治社會化內涵作出了系統解釋和論證,基本明確了以下三個要點:一是政治社會化對于促進政府公民的良性互動、維護國家政治穩定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政治社會化的內容主要為政治文化的傳遞;三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和結果涉及了學習政治知識、內化政治態度、形成參與行為模式三個方面。
政治知識很好理解,主要表現為“存儲在人們長期記憶中的事實政治信息的范圍”,⑧Michael Delli Carpin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通常通過測試個人對特定政治事件和政治事實的記憶獲得。關于政治態度,許多人更傾向于使用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認同、政治觀念、黨派態度、政治價值觀或政治評價等概念,但大體上都反映人們對政治制度、政黨、政治權威、政策或重要政治人物的評價。⑨Marc Hetherington and Jason Husser, How Trust Matters:The Changing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6, 2012, pp. 312-325.政治參與指“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行為的活動,這種活動可以是影響政治的意向,也可以是產生了影響政治的結果”。①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Henry Brady and Norman Nie, American Citizen Participation Study, Ann Arbor,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1995.政治參與可分為在線政治參與和離線政治參與兩種模式,在線參與政治包含:政治信息(閱讀和搜索政治信息)、政治互動(評論和討論公共事務,分享政治新聞和片段)、公共制作(發表政治文章或制作政治視頻等)、集體行動(發起或參與集體行動)。②Mats Ekstr?m and Adam Shehata, Social Media, Porous Bounda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olitical Engagement among Young Citizen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0, 2018,pp.740-759.離線政治參與在西方國家的主要表現為參加政治集會、投票和向政治候選人捐款等行為,在我國表現為簽署請愿書、參加集會、給官員或政府部門寫信、參與政治訪談等行為。③Michael Chan, Hsuan-Ting Chen and Francis Lee,Examining the Roles of Mobile and Social Media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ree Asian Societies Using a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Approach, New Media &Society, vol. 19, 2017, pp. 2003-2021.實踐過程中,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三者密切相關,大量經驗研究證實,更廣泛的政治知識有助于更穩定和一致的政治態度,增加對政治制度的信任,促進人們的政治參與。④William Galston,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217-234.⑤Nakwon Jung, Yonghwan Kim and Homero Gil de Zú?iga,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Efficacy i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14, 2011, pp. 407-430.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大眾媒體對政治社會化的持續影響就引起了廣泛關注,但相關實證研究卻得出了較為復雜的結論。有學者認為大眾媒體新聞促進了民眾的政治學習,強化了民眾的政治意識,這種政治意識又反過來促進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學習和政治參與,形成良性循環。⑥Pippa Norris,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一些媒體的信息質量較低不利于政治知識積累和政治興趣培養,甚至加劇了負面政治態度和情緒。⑦Claes De Vreese and Hajo Boomgaarden, News,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News Media Exposure o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Acta Politica, vol. 41, 2006, pp. 317-341.還有學者提出了差異效應假設,認為報紙對政治社會化具有正面影響,但電視乃至互聯網的影響是無效的,甚至是負面的。⑧William Eveland,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of Learning from the News: Evidence from Nonelection, Off-year Elec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ntex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8, 2001, pp. 571-601.⑨Michael Beam, Myiah Hutchens and Jay Hmielowski,Facebook News and (De)Polarization: Reinforcing Spirals in the 2016 US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1,2018, pp. 940-958.時至今日,算法和智能媒體的快速發展正在從根本上重塑公眾的政治信息環境,迫使我們再度重新思考政治社會化的發生路徑。
三、算法推薦與公民政治知識
媒體的政治學習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同的媒體環境為個人提供了不同的政治學習的機會。⑩Markus Prior, Post-Broadcast Democracy: How Media Choice Increases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Polarizes Elec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邁克爾· 德利卡皮尼(Michael Delli Carpini)和斯科特· 基特(Scott Keeter)提出對政治知識學習產生重大影響的三個核心要素是:機會、動機和能力。機會指政治信息的有用性,包括很多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媒體環境;動機決定了人們是否對消費政治信息感興趣;能力解釋人們是否有足夠的技能來理解信息。①Michael Delli Carpin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在此,考察算法介入新聞業是否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學習和政治知識積累,也離不開對這三個核心要素的討論。我們具體嘗試回答三個問題:
(一)算法推薦的新聞環境是否給公民提供了更多政治信息?
評估媒體、政治和公民之間關系變化的一個關鍵概念就是政治信息環境,這個概念有時被稱為信息環境或媒體環境,通常指新聞或政治信息的總供給。②Peter Van Aelst, et 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1, 2017, pp.3-27.關于政治信息環境,有一個潛在共識,即政治信息供給越多,人們接觸政治信息并進行政治學習的可能性就越高。一些研究表明,政治信息環境對人們的媒體使用以及政治知識產生了重大影響,③Peter Van Aelst, et 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1, 2017, pp.3-27.與信息貧乏的國家相比,在信息豐富環境中的美國公民能夠更多地了解政治問題,④Jennifer Jerit, Jason Barabas and Toby Bolsen, Citizens,Knowledge,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2006, pp. 266-282.甚至各國政治知識的差異也可部分歸因于政治信息環境的變化。⑤Susan Banducci, Heiko Giebler and Sylvia Kritzinger,Knowing More from Less: How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creases Knowledge of Party Posi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從政治新聞的絕對數量上講,毫無疑問,在過去幾十年間持續增加。盡管如此,仍然有學者提出了當前“政治新聞供給正在減少”的說法。這一說法看似難以理解,但也指出了幾個鮮明的問題:首先,政治新聞的絕對數量增加,不等同于在整體的媒體信息供給中,政治新聞的相對數量也在增加,因為體育新聞、娛樂新聞的增量更大;其次,政治新聞的絕對數量更多,也不意味著人們日常使用的媒體資源中政治新聞也在增加;第三,人們對政治新聞的需求和使用可能正在下降;第四,高質量的政治新聞數量可能正在下降;第五,政治新聞的多樣性在減少。⑥Peter Van Aelst, et 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1, 2017, pp.3-27.伊萊· 帕里澤提出的“過濾氣泡”理論也論及了類似的問題,他認為,個性化的信息世界最終將我們置于氣泡之中,我們只能獲得與之前的消費行為相匹配的信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熟人分享的信息,或與我們觀點相一致的信息,最終我們所看到的內容一再縮小。⑦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同時,算法推薦依賴于用戶喜好,而用戶喜好往往會避開硬新聞,選擇軟新聞(即偏娛樂化的新聞),但硬新聞才是對政治民主和政治知識有效的新聞類型,⑧Eli Pariser, Did Facebook’s Big Study Kill My Filter Bubble Thesis? https://www.wired.com/2015/05/did-facebooksbig-study-kill-my-filter- bubble-thesis/.因此也沒有理由相信算法推薦新聞對人們的政治信息環境和政治知識學習產生積極影響。⑨Michael Cacciatore, Sara Yeo, Dietram Scheufele, Michael Xenos, Dominique Brossard and Elizabeth Corley, Is Facebook Making Us Dumber? Exploring Social Media Use as a Predictor of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95, 2018, pp. 404-424.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人們對政治新聞的需求。在算法時代,人們的偏好對于塑造政治信息環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還沒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人們對政治新聞的需求和使用在明顯減少,但對軟新聞需求上升的趨勢引起了不少擔憂。帕布羅·哈維爾·博奇科夫斯基(Pablo Javier Boczkowski)和尤金伲亞· 米切爾斯坦(Eugenia Mitchelstein)針對7 個國家的20 個新聞網站近4 萬篇新聞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發現,媒體的新聞偏好與公眾的新聞偏好總是存在差異,但新聞消費者的偏好正在推動媒體犧牲硬新聞,提供更多軟新聞。①Pablo Javier Boczkowski and Eugenia Mitchelstein, The News Gap: When the Information Preferences of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Diver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3.媒體為了爭取更多觀眾注意力的競爭行為,只會不斷強化媒體滿足觀眾需求的趨勢,提供“點擊誘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②Jonas Nygaard Blom and Kenneth Reinecke Hansen,Click Bait: Forward-Reference as Lure in Online News Headlines,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76, 2015, pp. 87-100.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軟新聞的受眾在增長,但并沒有必然地導致硬新聞受眾的減少,同時,軟新聞還給那些原本缺乏政治興趣的人提供了更多接觸政治信息的機會。③Matthew Baum, Soft New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Evidence Of Absence Or Absence Of Eviden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0, 2003, pp. 173-190.例如,社交媒體上,人們肯定會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娛樂或個人身份建構、社交關系建構,但也沒有理由認為有政治興趣的人不會在社交媒體上消費硬新聞和公共事務消息。④Homero Gil De Zú?iga, Nakwon Jung and Sebastián Valenzuela,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7, 2012, pp. 319-336.針對我國新聞消費者的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以今日頭條和微博為代表的算法推薦新聞媒體促進了公民的軟新聞知識水平增長,但同時,其對提高公民的公共事務知曉度也有顯著作用。⑤崔迪、吳舫:《算法推送新聞的知識效果——以今日頭條為例》,《新聞記者》2019 年第2 期。不過,還缺乏縱向研究考察軟新聞知識與硬新聞知識的變化趨勢。不同國家的政治信息環境有較大差異,軟新聞的數量差異也較大。⑥Carsten Reinemann, James Stanyer and Sebastian Scherr,Hard and Soft News, in Claes de Vreese, Frank Esser and David Nicolas Hopmann (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6, pp. 131-149.即便是不同媒體,也會因受眾、定位和算法規則不同而呈現迥異的政治信息環境和新聞質量。但整體上,更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軟新聞已呈現了明顯擴張的趨勢,它是否切實擠壓了硬新聞的空間還需要進一步論證,但我們應傾向于重視該風險,關注不同媒體的新聞質量差異,關注人們對高質量硬新聞的需求,以及不同新聞消費群體的政治知識差距。
(二)算法推薦的新聞環境是否增加了公民的政治學習機會?
這個問題的一個核心辯論點是,算法推薦是否為人們提供了偶然和被動接觸政治信息的機會,以及偶然接觸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公民的政治學習。美國皮尤民意調查顯示,目前,62% 的Facebook 新聞用戶大多是偶然得到新聞,而不是因為他們積極嘗試關注最近的社會動態。⑦Jeffrey Gottfried and Elisa Shearer,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https://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積極或有目的的學習并不是人們學習的唯一方式,個人也可以通過偶然的曝光被動地了解政治。⑧Matthijs Elenbaas, Claes de Vreese, Andreas Schuck and HajoBoomgaarden, Reconciling Passive and Motivated Learning:The Saturation-Conditional Impact of Media Coverage and Motivation On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 41, 2014, pp. 481-504.算法推薦讓“新聞找到我”,人們在無意之中接觸了許多熱點政治新聞和朋友關注的新聞并獲取政治知識,①Homero Gil De Zú?iga, Brian Weeks and Alberto Ardèvol-Abreu, Effects of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Use Implications for News See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22, 2017, pp. 105-123.赫伯特· 克魯格曼(Herbert Krugman)稱之為“沒有參與的學習”,尤金·哈特利(Eugene Hartley)稱之為“非錨定學習”。②Herbert Krugman,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Learning Without Involve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9,1965, pp. 349-356.因此,不少學者猜測,當前媒體環境可能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更多樣化的學習機會,也提供了一個克服知識差距的機制,因為被動學習比主動學習產生更多樣化的學習收益,用戶更容易接受他們所接觸的信息,增加了平時不太注意的政治知識。③Leticia Bode, Political News in the News Feed: Learning Politics from Social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9, 2016, pp. 24-48.但反對觀點認為,一方面,缺乏政治興趣的人,即使偶然接觸到算法推薦的政治新聞,也常常不會點擊新聞鏈接進行深入閱讀,也沒有進一步的認知加工,無法助益其政治學習;④Solomon Messing and Sean Westwood, Selective Exposure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Trump Partisan Source Affiliation When Selecting News Onl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41, 2014, pp. 1042-1063.另一方面,偶然接觸新聞和感知“新聞找到我”使人們主觀上產生了“膨脹的知識感”⑤方師師:《搜索引擎中的新聞呈現:從新聞等級到千人千搜》,《新聞記者》2018 年第12 期。,從而主動尋找新聞的動機下降,通過傳統新聞媒體尋找新聞的行為減少,最終將不利于其政治知識學習。⑥Homero Gil De Zú?iga, Brian Weeks and Alberto Ardèvol-Abreu, Effects of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Use Implications for News See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22, 2017, pp. 105-123.相比而言,那些積極主動尋找政治新聞的群體,他們從新聞供給更豐富、內容選擇更多的高選擇媒體環境中獲取政治學習的機會更頻繁、更深入,學習效果也通常更明顯、更受認可。⑦Homero Gil De Zú?iga, Brian Weeks and Alberto Ardèvol-Abreu, Effects of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Use Implications for News See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22, 2017, pp. 105-123.鑒于政治學習需要深入的認知處理,高選擇的算法新聞環境下的偶然學習效果仍值得懷疑。
(三)算法推薦的新聞環境是否擴大了公民的政治知識差距?
關于算法推薦的新聞環境是否會增加不同群體學習機會的不平等,擴大公民的政治知識差距,這與政治信息環境、政治學習動機和個人認知能力都密切相關,三者的影響通常相互交織。邁克爾· 比姆(Michael Beam)和杰拉爾德· 科斯基(Gerald Kosicki)指出,個性化的新聞門戶平臺為那些積極主動尋找新聞的人提供了一個更便利的新聞獲取工具,因此使用這些個性化新聞平臺可能會增加不平等。⑧Michael Beam and Gerald Kosicki, Personalized News Portals: Filtering Systems and Increased News Exposure,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91, 2014, pp.59-77.有學者總結,隨著社會的信息越豐富、獲取便利性越高,高教育水平者與低教育水平者、對政治和新聞感興趣和不感興趣者的政治知識差距都會增加。⑨Peter Van Aelst, et 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1, 2017, pp.3-27.例如,一項針對社交媒體的實證研究表明,盡管Facebook 被廣泛用于信息交換,但是高教育水平者和低教育水平者交換的信息內容和信息質量都不同,高教育水平用戶會交換公共事務信息并且能夠記住它,但是低教育用戶通常不分享那些有益于增加政治知識的信息。①Sung Yoo and Homero de Zú?iga, Connecting Blog,Twitter and Facebook Use with Gaps in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7, 2014, pp. 33- 48.即使軟新聞使用、偶然學習可能為那些沒有政治學習動機、教育水平較低的群體或多或少提供一些政治學習的機會,但考慮到算法推薦使不同群體的新聞環境區別更加鮮明,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存在政治知識差距擴大的趨勢。
四、算法推薦與公民政治態度
關于智能媒體與公民政治態度的關系,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話題就是:作用日益增加的個性化和算法是否最終過濾掉了與我們政治態度/ 立場不同的觀點?②ZeynepTufekci, Facebook Said Its Algorithms Do Help Form Echo Chambers, and the Tech Press Missed It,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32, 2015, pp. 9-12.選擇性曝光理論長期以來一直關注這個問題,人們是否更多暴露于與自己態度一致的新聞,從而強化了自己的態度,出現態度極化傾向?③Wolfgang Donsbach and Cornelia Mothes, The Dissonant Self: Contributions from Dissonance Theory to a New Agenda For Study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arles Salmon (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36,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2,pp. 3-44.這種現象如果被證實,那么值得擔憂的問題是:算法推薦是否會助推輿論在公共事件上的相互對立,或助長我國民粹主義等社會思潮的負面效應,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造成影響和挑戰。
我們首先試圖尋找算法推薦可能造成政治極化的證據。一些理論家稱,過濾我們新聞環境的算法,有效地將我們置于自己信仰的回聲室中,這是兩極分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④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選擇性曝光理論認為,個人傾向于消費與他們的觀點和信仰一致的媒體信息,避免與自己態度不同甚至挑戰自己態度的內容。⑤Natalie Stroud,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ur, vol. 30, 2008, pp. 341-366.尤其是當前的新聞環境中,過濾信息的能力更加強大,用戶可以非常輕松地根據自己的偏好來分類信息,并且借助算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選擇性曝光結果。⑥Dominic Spohr, Fake News an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Filter Bubbles and Selective Exposure on Social Media, 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 vol. 34, 2017, pp. 150-160.例如,米歇爾· 德· 維卡里奧(Michela Del Vicario)等人對2016 年1 月至7 月期間與英國脫歐相關新聞進行交互的100 多萬用戶進行了挖掘分析,發現用戶都傾向于關注一個立場的敘事而忽略另一個,并很快形成兩個態度完全對立的立場,該分析證明了兩個相互隔離的回音室確實存在。他們進一步通過自動主題提取和情感分析技術,比較了兩個回音室的呈現方式和情緒反應,發現兩個回聲室效應和極化效應都非常明顯。而有趣的是,這種極化效應是用戶自發形成的,因為新聞在測試之前并沒有明顯的態度分類,態度分化可能是算法為個人偏好匹配不同內容過程中形成的,這也是算法推薦導致了選擇性曝光和過濾氣泡現象的有力證據。⑦Michela Del Vicario, Fabiana Zollo, Guido Caldarelli,Antonio Scala and Walter Quattrociocchi, Mapping Social Dynamics on Facebook: The Brexit Debate, Social Networks, vol.50, 2017, pp. 6-16.
不過,一位在Facebook 工作的研究人員在《科學》(Science)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在Facebook 上接觸意識形態多樣化的新聞和觀點》的文章反駁了該觀點。該研究對1010 萬Facebook 用戶所接觸信息的意識形態同質性進行了檢驗,結果指出,Facebook 的算法推薦系統會小幅度降低不同態度新聞的比例,個人的選擇則在限制不同態度的內容交叉曝光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①Eytan Bakshy, Solomon Messing and Lada Adamic,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 vol. 348, 2015, pp. 1130-1132.媒體紛紛對此進行了報道,標題如“Facebook 說回聲室不是Facebook 的 錯”(Wired)、“Facebook 表 示其算法不對您的在線回聲室負責”(Verge)、“Facebook 的研究表明,你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不是算法”(Mashable)。盡管Facebook宣稱其一直在努力創造一種獨立的、不嵌入任何其他價值的新聞推薦算法,但科學家們不以為然,眾多的科學研究仍在不斷地證明Facebook 過濾了相反態度的新聞并抑制了內容的多樣性,并呼吁媒體認真對待和改進其技術。②Zeynep Tufekci, Facebook Said Its Algorithms Do Help Form Echo Chambers, and the Tech Press Missed It,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32, 2015, pp. 9-12.
除了政治極化之外, 強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RSM)還提出了算法推薦的去極化結果和體內平衡結果。去極化結果更有可能發生于政治態度較弱、政治觀點尚不完全明確的人身上,他們在算法環境中會暴露于更廣泛的政治觀點之下,促進其政治態度轉變;而體內平衡立場認為算法推薦更多是強化和維持了原有態度,它在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上的作用有限,因為態度常常是較為穩定的。③Michael Slater,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ntent Expos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ttitudes,Media Psychology, vol. 18, 2015, pp. 370-395.④Michael Beam, Myiah Hutchens and Jay Hmielowski,Facebook News and (De)Polarization: Reinforcing Spirals in the 2016 Us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1,2018, pp. 940-958.
在我國,關于算法推薦的政治極化效應和意識形態影響的實證研究比較匱乏,但國內學者也開始陸續關注算法通過非制度性權力來構建“社會共識”的作用,⑤喻國明、楊瑩瑩、閆巧妹:《算法即權力:算法范式在新聞傳播中的權力革命》,《編輯之友》2018 年第5 期。以及算法推薦因擠壓主流媒體空間、加劇社群區隔與價值觀分化、占據新聞把關權,從而對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帶來負面影響等問題。⑥張志安、湯敏:《論算法推薦對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18 年第10 期。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民粹主義在近年持續盛行,并且顯現出與其他社會思潮較強的合流之勢,時常圍繞社會公共事件將公共輿論和情緒推向極端,甚至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鮮明對立。例如,將2017 年北京開展“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解讀為“北京驅逐低端人口”,輿論集體將國家和政府的形象推向負面的現象,致民粹主義思潮泛濫,⑦陳琳、單寧:《當前國內社會思潮趨勢走向》,http://www.rmlt.com.cn/2018/0709/522791.shtml。值得警惕的同時,也應該反思算法推薦在輿論態度極化的問題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五、算法推薦與公民政治參與
算法推薦與公民的政治參與可以從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兩個視角來解釋。我們首先討論間接影響。正如大多數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論證,媒體使用常常通過影響人們的政治討論、政治態度、政治興趣或政治效能,進而對人們的政治參與行為產生影響。⑧Jack Mcleod, DietramScheufele and Patricia Moy,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6, 1999, pp. 315-336.⑨Hernando Rojas, I. PérezandHomero Gil de Zú?iga,Comunicacio?n y Comunidad, Universidad Externado de Colombia Press: Bogotá Colombia, 2010.這些中介影響因素可以分類為認知因素和傳播因素。其中,認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認為多媒體元素和新聞超鏈接引起人們的認知加工再影響政治參與;①William Eveland,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of Learning from The News: Evidence from Nonelection, Off-Year Elec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ntex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8, 2001, pp. 571-601.傳播中介模型(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②Jack Mcleod, Dietram Scheufele and Patricia Moy,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6, 1999, pp. 315-336.以及同類型的市民傳播中介模型(Citizen Communication Mediation)③Dhavan Shah, Jaeho Cho, William Eveland and Nojin Kwak,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2, 2005, pp. 531.、 競選中介模 型(Campaign Mediation Model)④Dhavan Shah, et al., Campaign Ads, Online Messaging,and Participation: Extending the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7, 2007, pp. 676-703.和O-S-R-O-R 模型(Orientations-Stimulus-Reasoning-Orientations-Response)⑤Jaeho Cho, et al., Campaigns, Reflection, and Deliberation:Advancing An O-S-R-O-R Model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9, 2009, pp. 66-88.則驗證了新聞消費通過促進公民政治討論等傳播行為,影響公民的政治參與。邁克爾·陳(Michael Chan)等人近期的一項實證研究,綜合了認知和傳播中介模型,以O-S-R-O-R 為模型框架驗證了移動和社交媒體新聞在線上和線下政治參與中的作用,三個概率抽樣樣本都證實了移動/ 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影響政治討論和政治效能,間接影響線上和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⑥Michael Chan, Hsuan-Ting Chen and Francis Lee,Examining The Roles of Mobile and Social Media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ree Asian Societies Using a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Approach, New Media &Society, vol. 19, 2017, pp. 2003-2021.鑒于社交媒體新聞與移動媒體新聞都是算法推薦新聞的典型代表,我們討論的算法推薦新聞與政治參與的間接關系,可以從大量的相關研究中尋找到有效的間接證明,但是缺憾在于,這些研究中還缺乏針對算法推薦新聞和個性化新聞與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的間接關系的討論和解釋,這也是未來研究可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
而有關算法推薦與公民政治參與的直接關系,我們不得不提到近年在西方國家倍受關注的議題——假新聞,具體表現為通過算法操縱社交媒體上的假新聞傳播并影響人們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問題。假新聞是“有意的且可驗證的、錯誤的,并可能誤導讀者的新聞文章”。⑦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 2017, pp. 211-236.2016 年美國大選之后,“假新聞”成為了一個廣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相關觀點認為,假新聞傳播在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其中社交媒體作為假新聞的主要傳播載體,為唐納德· 特朗普的當選起到了不可小覷的潛在作用。⑧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 2017, pp. 211-236.社交媒體中的機器人(通過算法制造模仿人類的自動賬戶)通過點贊、分享和搜索信息,可以將虛假新聞的傳播力放大幾個數量級,主導社交媒體中有關競選的大部分政治內容,影響美國公民的投票行為。⑨David Lazer, et al.,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vol. 359, 2018, pp. 1094-1096.同時,它們還通過操縱社交媒體中的算法推薦,促使社交媒體向更多用戶推送其內容。⑩Facebook, 2017. Stats. Facebook.皮尤調查報告顯示,社交媒體上的大量政治新聞要么不準確,要么完全是假的。更嚴重的問題是,大約2/3 的美國成年人(64%)表示假新聞引起了大量關于事實政治信息的混淆,22% 的人表示這會導致一些混亂。①Pew Research Center,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7, http://www.journalism.org/2017/09/07/news-useacross-social- media-platforms-2017/.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國,社交媒體中的算法推薦同樣能夠輕易成為別有用心者操縱政治的工具,散布謠言,煽動情緒,對公民的輿論風向、政治態度甚至線下政治參與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無論這種影響在我國是否普及,在技術上算法已完全具備操縱的能力,而我們針對其治理,無論從法律法規、平臺自律、技術治理上,都還缺乏有效手段,其中潛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六、結 語
對于政府而言,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政治制度的有效存在都取決于公民的認同,并在行為上遵守法律、執行規則。公民政治社會化的可能性風險,是政府管理工作中不可忽視的問題。算法介入新聞業,個性化新聞流替代傳統媒體新聞流,對公民的政治社會化有什么影響?我們從政治社會化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入手展開討論并得出結論:隨著人們的偏好和需求在塑造個人的政治信息環境越來越重要,算法推薦并沒有整體上提升公民的政治新聞供給數量和質量,相反,新聞消費者的偏好正在推動媒體犧牲硬新聞,提供更多軟新聞,這一趨勢并不利于公民的政治學習和政治知識積累。主動尋找政治新聞的人與不主動尋找政治新聞的人、高教育水平的人與低教育水平的人,在個性化新聞環境中的政治知識差距一再增大。盡管算法通過熱點推薦和社交關系推薦也給許多人提供了偶然接觸和學習政治的機會,但是缺乏深度的認知加工也導致偶然政治學習的效果不甚理想。同時,算法推薦進一步強化了選擇性曝光效應,人們傾向于消費與他們的觀點和信仰一致的媒體信息,避免與自己態度不同甚至挑戰自己態度的內容,②Natalie Stroud,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ur, vol. 30, 2008, pp. 341-366.導致圍繞政治問題、公共事件的輿論態度出現兩極分化、相互對立的格局。算法推薦甚至還常常成為直接政治操縱的工具,通過操縱人們看到的內容,影響公民的線上和線下政治行為。
如何防范和治理算法推薦可能導致的政治風險,給國家、平臺和公民自身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目前,全球針對算法出臺的比較典型的國家干預措施包含:提供公共服務、指揮和控制監管、通過補貼和稅費激勵、建立共同監管機制、通過軟法和信息服務提高人們對風險的認識和了解,并促進其行為調整。③Florian Saurwein, Natascha Justand Michael Latzer,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Options and Limitations, Info, vol. 17,2015, pp. 35-49.學者們還建議,增加算法的透明度和政府的控制權,④Wolfgang Schulz, Thorsten Held and Arne Laudien, Search Engines as Gatekeeper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Internet Search Engines Including Media Law and Anti-trust Law, German Law Journal,vol. 6, 2005, pp. 1418-1433.建立中立搜索原則,⑤Marina Lao,“ Neutral” Search as a Basis for Antitrust A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6, 2013, pp.1-12.并建立倫理監管委員會參與監管。⑥Felicitas Kraemer, Kees Overveld and Martin Peterson, Is There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 13, 2011, pp. 251-260.平臺進行政策響應或行業自律的措施通常包括:建立公司的算法原則和標準、建立算法風險的評估機制、建立處理公眾投訴的監察機制等。①Florian Saurwein, Natascha Just and Michael Latzer,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Options and Limitations, Info, vol. 17, 2015, pp. 35-49.還有一種看法是選擇保守治理,依靠新聞消費者、新聞平臺和算法服務供應商的市場行為“自然”變化降低風險。例如,給新聞消費者提供技術工具實現自助匿名化或去個性化服務,ConteIt、Reflect 和OpinionSpace 等工具就是專門通過搜集意外發現的信息來避免過濾氣泡和偏見;②Paul Resnick, Kelly Garrett, Travis Kriplean, Sean Munson and Natalie Jomini Stroud, Bursting Your (Filter) Bubbl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Diverse Exposure,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ompanion, San Antonio,Texas, 2013, pp. 95-100.算法供應者會通過提高技術保護來對抗被操縱,或減少推薦偏差;新聞平臺也會通過內容優化策略來避免風險。如果這種機制運行樂觀,那政府只需針對必要的問題進行輔助性干預即可。
因此,厘清算法推薦對公民政治社會化的可能風險,對于國家、平臺、算法機構和公民都十分重要。但是,本文在梳理過程中也發現了一系列缺憾和問題:第一,各個國家政體不同、文化不同、政府公民互動關系不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和結果都呈現明顯差異,亟需各國針對該問題進行多角度的實證驗證,同時關注跨國比較,確認各國技術與政治的共性關系與特殊性,跳出單一國家研究的限制;第二,要測量算法推薦引起的公民政治社會化的變化,十分需要面板數據的縱向驗證,橫向數據因其本身的缺憾很難確認因果關系,未來應重點補充縱向調查和驗證;第三,公民政治社會化涉及諸多概念,應該提高相關研究對概念操作化的一致性,以利于后期的比較研究;第四,許多研究偏向于以當前流行的媒體為對象開展政治社會化研究,例如國外集中對Facebook 的研究、國內對今日頭條的研究,盡管算法作為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常被討論,但也導致學者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平臺,直接針對算法推薦與政治社會化的關系討論不夠深入,這個問題值得被專門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