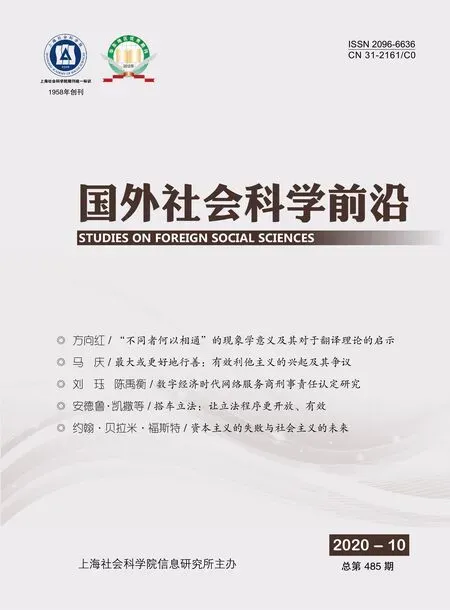“不同者何以相通”的現(xiàn)象學(xué)意義及其對于翻譯理論的啟示
——從張世英“兩種目標(biāo)”說談起
方向紅
內(nèi)容提要| “不同者何以相通”是當(dāng)代最緊迫、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對這個(gè)問題給出的幾種解決方案并不能令人滿意。在《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一書中,張世英提出“兩種目標(biāo)”說,即相同性追求和相通性追求。這一學(xué)說,對于解決這個(gè)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本文首先介紹“兩種目標(biāo)”說,并在現(xiàn)象學(xué)的意義上將其等同于海德格爾的“存在者整體”學(xué)說;然后以胡塞爾、海德格爾、德里達(dá)、梅洛-龐蒂等人的語言觀為例證,揭示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所實(shí)現(xiàn)的突破及其遭遇的困難;最后探討張世英經(jīng)過現(xiàn)象學(xué)轉(zhuǎn)換的“兩種目標(biāo)”說對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的啟示,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關(guān)于“最大相通點(diǎn)”的翻譯理論設(shè)想。
不同者何以能夠相通?根據(jù)張世英在新近出版的《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以下簡稱《對話》)一書自序中的說法,這是縈繞在他心頭近40年的問題。這個(gè)問題在今天看來應(yīng)該是當(dāng)代最緊迫、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之所以最緊迫,是因?yàn)闊o論是大國之爭、文明沖突還是種族糾紛、宗教戰(zhàn)爭,在當(dāng)今世界都呈愈演愈烈之勢,其背后大都遵循著不同者不可通的思維邏輯,這樣的邏輯將會(huì)帶來沖突和戰(zhàn)爭不可避免這樣的危險(xiǎn)結(jié)論。之所以最根本和最重要,乃是由于無論是現(xiàn)實(shí)問題還是理論問題,無論是政治問題還是經(jīng)濟(jì)問題,只要我們試圖徹底地追根溯源,最后我們撞上的還是這個(gè)問題。我們不妨以幾個(gè)理論問題為例來說明。
在跨文化研究領(lǐng)域,特別是在對東西方文化作比較研究的時(shí)候,我們常常陷入究竟是“以中釋西”還是“以西釋中”、究竟是格義還是“反向格義”的兩難中,因?yàn)橹形鳛椴煌撸岩环讲⑷氲搅硪环降囊曈蛑校粌H會(huì)帶來巨大的誤解,還有可能導(dǎo)致其中的一方喪失自身的獨(dú)特性。
在政治哲學(xué)領(lǐng)域,比如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從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發(fā)展而來的承認(rèn)理論那里,主人和奴隸、自我和他人雖然已達(dá)到相互承認(rèn)對方的高度,但這種承認(rèn)其實(shí)十分脆弱,它會(huì)因無法避免的“社會(huì)閉合”或“論證閉合”所帶來的蔑視體驗(yàn)而取消,因?yàn)樗麄冸p方仍是不相通的不同者。
自我和他人問題在心靈哲學(xué)和現(xiàn)象學(xué)的主體理論這里更加尖銳了。通過身體的作用,一個(gè)心靈如何把另一個(gè)不同的心靈視為心靈而不是看作物體?自我如何意識到他人?是自我把他人看作他人,還是他人(包括他人的目光或面容)喚醒了自我,讓自我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每一種回答都會(huì)走向理論上的死胡同。從自我出發(fā)走向的是唯我論,而從他人出發(fā)將會(huì)迫使哲學(xué)走向獨(dú)斷,即我們必須斷言他人的先在性。如果我們認(rèn)可這種獨(dú)斷,可能會(huì)引發(fā)更嚴(yán)重的問題。眾所周知,當(dāng)列維納斯把自我當(dāng)成他者①當(dāng)然,這里的他者與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他人還不是一回事,但他者正是通過他人的面容顯示自身的。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首先表現(xiàn)為自我與他人面容的關(guān)系,從而進(jìn)一步表現(xiàn)為自我與他人以及自我與鄰人的關(guān)系。的人質(zhì)時(shí),德里達(dá)發(fā)現(xiàn)了其中隱含的暴力因素并提出了“第三方”概念,以便在自我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植入正義。
在翻譯理論中,我們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同者之相通的重要性以及確定和允諾相通程度的困難性。兩門不同的語言通過翻譯可以互通,可以讓處于不同語言系統(tǒng)中的人們相互交流和理解,可是,這種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相通的實(shí)現(xiàn)中包含了多少扭曲和誤解?這些扭曲和誤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允許的?譯中的不可譯,信中的不可信,達(dá)中的不可達(dá),是各種翻譯理論無法回避的難題。
這里所舉的幾個(gè)例子旨在說明這個(gè)問題所具有的寬廣的理論跨度。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對這樣一個(gè)基礎(chǔ)性問題也做過深入的探討并給出了幾種解決方案,但是,遺憾的是,這些方案本身會(huì)帶來更大的問題。
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解決方案歷來為后人所詬病。按照黑格爾的理論,一對不同者,比如主人和奴隸,他們之間的不同和斗爭會(huì)導(dǎo)致互相揚(yáng)棄對方并由此進(jìn)入更高的發(fā)展階段。可是,在進(jìn)入更高階段之前的時(shí)間里,在彼此揚(yáng)棄對方之前的時(shí)間里,不同者之間何以相通這個(gè)問題似乎被略過了。
理性主義的解決方案看似簡單,只要訴諸人類的共同理性,自我和他人之間就有了相通的基礎(chǔ),可是這個(gè)方案也最獨(dú)斷,因?yàn)樗牙硇灶A(yù)設(shè)為人之本性,這個(gè)預(yù)設(shè)遭到了包括福柯在內(nèi)的一大批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批判。
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決方案,一般而言,其實(shí)是一種不解決方案。后現(xiàn)代主義者安于不同者之間的不同,甚至認(rèn)同并強(qiáng)化這種不同。他們反對普遍性,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的獨(dú)特性,拒斥普遍真理,訴諸地方性知識。這個(gè)方案最終滑向的是經(jīng)驗(yàn)主義、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
解釋學(xué)對這個(gè)問題著力最大,它專門討論不同者是何以溝通的。伽達(dá)默爾的“視域融合”說就是一個(gè)針對性的方案。但是,當(dāng)伽達(dá)默爾在無奈之下端出“視域融合”底下的“善良意志”的時(shí)候,德里達(dá)的逼問——善良意志不正是權(quán)力意志嗎?——似乎是無法反駁的。顯然,在“善良意志”的眼里,詮釋和對話完美透明地展開,不同者最終走向“視域融合”。可在權(quán)力意志看來,在溫情脈脈的溝通和融合的下面進(jìn)行的是不同者中的一方對另一方殘酷的統(tǒng)一化和同一化過程。
如果我們既不能從普遍性出發(fā),也不能從個(gè)體性出發(fā),既不能訴諸獨(dú)斷,也不能走向經(jīng)驗(yàn),那么,不同者究竟何以相通?難道還有第三條道路嗎?
本文擬從張世英的“兩種目標(biāo)”說出發(fā),并在現(xiàn)象學(xué)的意義上將其等同于海德格爾的“存在者整體”學(xué)說;然后以胡塞爾、海德格爾、德里達(dá)、梅洛-龐蒂等人的語言觀為例證,揭示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所實(shí)現(xiàn)的突破及其遭遇的困難;最后探討張世英的經(jīng)過現(xiàn)象學(xué)轉(zhuǎn)換的“兩種目標(biāo)”說對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的啟示,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關(guān)于“最大相通點(diǎn)”的翻譯理論設(shè)想。
一、張世英的“兩種目標(biāo)”說
張世英在《對話》中指出,①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48頁。哲學(xué)有兩種目標(biāo):西方古典哲學(xué)的目標(biāo)是追求認(rèn)識論上的相同性,而自黑格爾之后的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與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目標(biāo)則是追求本體論或存在論上的相通性。何謂相通?張世英的看法是:“彼此不同的東西而又能互相溝通,這就是我所說的相通。”②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48頁。張世英舉例說,你的痛感雖不直接表現(xiàn)為我的痛感,但它可以牽動(dòng)我的不忍之心,似乎我也在痛一樣,這就是你與我的相通;在莊子與惠施關(guān)于魚之樂的辯論中,就不同而言,惠施說得對,但就相通而論,莊子說出了不同者亦能相通的道理;儒家關(guān)于“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的說法更是不同而相通的典范例證。③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49頁、第51頁。張世英這樣的解釋,想必不會(huì)有人反對,但真正具有哲學(xué)意義的問題是:“不同的東西何以能夠相通?相通的含義是什么?”④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50頁。顯然,相通的定義及其運(yùn)行機(jī)制才是哲學(xué)需要面對的困難。
張世英從辯證法的萬物普遍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尼采關(guān)于事物是相互作用的總和的思想、萊布尼茨關(guān)于每一單子都是反映整個(gè)宇宙的一面鏡子的說法以及華嚴(yán)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主張出發(fā),通過對萊布尼茨和華嚴(yán)宗理論基礎(chǔ)的揚(yáng)棄,給出了關(guān)于相通的嚴(yán)格的定義:相通是不同者之間的無廣延的但卻是真實(shí)存在的交叉點(diǎn),這個(gè)交叉點(diǎn)本身是全宇宙內(nèi)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jié)晶。⑤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52~53頁。從這個(gè)定義出發(fā),“不同”與“相通”都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解釋:“說‘不同’,是指普遍的相互作用、相互聯(lián)系的方式不同;說‘相通’,是指它們都反映唯一的全宇宙,或者說它們本是一體。”⑥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53頁。強(qiáng)調(diào)形式為引者所加。
“反映”這個(gè)詞道出了不同者如何相通的運(yùn)行機(jī)制。張世英以一個(gè)個(gè)體的人為例,生動(dòng)地闡明了相通的運(yùn)行機(jī)制:“這里所謂的反映和鏡子只有比喻意味,不能理解為照相那樣,把宇宙整體的模樣機(jī)械地、具體而微地縮小到每一交叉點(diǎn)或每一物、每一人這樣的小小照片中。‘反映’是指聯(lián)系、作用、影響之類的含義。例如某一特殊的人之所以為他,乃是無限聯(lián)系、作用、影響的結(jié)果,這些聯(lián)系、作用和影響包括父母的以至祖祖輩輩的,朋友的以至不相識者的,近處的以至遙遠(yuǎn)的,現(xiàn)有的以至過去的,物質(zhì)的以至精神的,有形的以至無形的,重要的以至不重要的,如此等等,以致無窮。總之,每一交叉點(diǎn)或每一物、每一人都向全宇宙開放而囊括一切,一切又向它集中,交織于它。就是在這種意義下,我說它‘反映’全宇宙。”⑦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54頁。
如果我們進(jìn)一步追問,全宇宙內(nèi)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其載體或承擔(dān)者是什么?其根據(jù)為何?那么,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張世英對此也作過思考并給出了正面的回答。在說明時(shí)間上的不同者也具有相通性這個(gè)論斷時(shí),張世英指出:“其根據(jù)就在于古與今雖不同而又相通,二者原本‘一體’‘一氣流通’。”⑧張世英:《中西哲學(xué)對話:不同而相通》,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57頁。顯然,在張世英看來,全宇宙內(nèi)部不同時(shí)間和空間中的事物之所以能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其根據(jù)就在于它們有一個(gè)共同的體,或者更準(zhǔn)確地說,它們本來就是一體,這個(gè)體,具體到承擔(dān)者方面,就是流通不息的氣。
二、張世英“兩種目標(biāo)”說的現(xiàn)象學(xué)意義
接下來我們要對張世英的“兩種目標(biāo)”說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的轉(zhuǎn)換,這樣做是基于以下兩點(diǎn)考慮。
首先與我們的主題有關(guān)。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已經(jīng)完成了對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突破,但自身仍面臨很多根本的困難,本文希望張世英的思考能給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帶來新的啟示。然而,張世英的思想來源十分復(fù)雜多樣,既有來自辯證法的,也有來自唯理論的;既有來自當(dāng)代的,也有來自古典的;既有來自哲學(xué)的,也有來自美學(xué)和宗教的。這些豐富的思想資源,特別是其中的概念和術(shù)語,例如“反映”“鏡子”等等,無法直接與現(xiàn)象學(xué)對接對應(yīng),因此也很難直接服務(wù)于對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的反思。——這是我們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轉(zhuǎn)換的理由或者動(dòng)力學(xué)上的考慮。
其次與張世英自身的現(xiàn)象學(xué)思考有關(guān)。在張世英的理論庫中,現(xiàn)象學(xué)本身也是一個(gè)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對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德里達(dá)的嫻熟應(yīng)用就證明了這一點(diǎn)。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張世英的很多思考,例如對“反映”和“鏡子”等概念的審慎使用以及所附加的種種限制和說明等等,本身就體現(xiàn)了現(xiàn)象學(xué)的“面向?qū)嵤卤旧怼钡木窈蛷氐椎默F(xiàn)象學(xué)還原的意識,只不過他在這樣做的時(shí)候沒有使用現(xiàn)象學(xué)的名稱而已。——這是我們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轉(zhuǎn)換的合法性考慮。
基于以上考慮,現(xiàn)在我們可以對“兩種目標(biāo)”說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轉(zhuǎn)換了。我以為,海德格爾的“存在者整體”(das Seiende im Ganzen)①“存在者整體”即“神學(xué)”,它是“元存在論”的主題。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可參見方向紅:《試論海德格爾元存在論概念的出現(xiàn)及其意義》,《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1期,第11~18頁。學(xué)說可以完美地對應(yīng)張世英關(guān)于相通的思考。從上面的梳理中,我們知道,張世英的相通概念具有三個(gè)要素:全宇宙或全宇宙的唯一性,不同者原本的“一體”即“一氣流通”,無廣延的但卻是真實(shí)存在的交叉點(diǎn)。而海德格爾的存在者整體也具有三個(gè)要素:囊括一切時(shí)間(過去、現(xiàn)在、未來)、空間(在場、不在場)和模態(tài)(現(xiàn)實(shí)、必然、可能)中的存在者之大全,貫穿于大全中的那個(gè)特定存在者即此在,此在之“此”(da)作為此在與他人以及此在與世界的交匯點(diǎn)。很明顯,張世英的全宇宙或全宇宙的唯一性就相當(dāng)于海德格爾的存在者之大全,海德格爾的那個(gè)貫穿于整體中的存在者說的正是張世英關(guān)于全宇宙內(nèi)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載體,即作為“一體”在不斷流通的“一氣”,同時(shí),作為交匯點(diǎn)的“此”恰恰不具有廣延的性質(zhì)但卻真實(shí)存在。
當(dāng)然,嚴(yán)格地講,海德格爾與張世英兩人的學(xué)說之間還是有差異的。一方面,張世英最終把貫穿宇宙的“一體”理解為流通不息的“一氣”,而海德格爾的那個(gè)位于總體之中的存在者(das Seiende)則更具廣泛性,它不僅可以囊括“氣”,更可以指此在、單子、神、意識、權(quán)力意志等等;另一方面,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shí)間》中把相通視為作為人的此在之間的領(lǐng)會(huì),而張世英的相通則指包括人在內(nèi)的萬物之間的相通。不過,需要補(bǔ)充說明的是,海德格爾自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已在一般存在者的意義上理解此在,并把這個(gè)意義上的此在寫為“此-在”(Da-sein)。
經(jīng)過現(xiàn)象學(xué)的轉(zhuǎn)換,我們現(xiàn)在便可以對張世英的相通說給出這樣的表述:萬物相通而不相同,相通乃在于萬物交匯于“此”(Da),這個(gè)“此”既非對象,亦非實(shí)在的空間,而是事物的聚匯與敞開之所。這個(gè)“此”在物那里表現(xiàn)為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在人那里顯現(xiàn)為語言、領(lǐng)會(huì)和情緒。這個(gè)“此”乃存在本身和那個(gè)貫穿于存在者整體中的存在者共作而成。
帶著這樣的理解,讓我們具體地考察一下在翻譯過程中不同語言的相通性問題。
三、現(xiàn)象學(xué)理論的翻譯如何做到不同而相通?
翻譯是一種擺渡,在德文中徑直就是一個(gè)詞:übersetzen(擺渡,翻譯)。
讓我們設(shè)想:一條大河分隔兩岸,兩岸是說著不同語言的思想。
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岸之思想如何擺渡至另一岸?這個(gè)問題可以細(xì)分為兩個(gè)問題:第一,是誰推動(dòng)了思想的擺渡?第二,思想可以不走樣地?cái)[渡過河嗎?關(guān)于第一個(gè)問題,普遍的觀點(diǎn)是,正是譯者或者社會(huì)歷史的某種需要推動(dòng)了思想的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例如,某個(gè)譯者的眼光和行動(dòng)推動(dòng)了一部譯作的問世,某個(gè)歷史事件、某種社會(huì)風(fēng)尚促成了一批譯作的問世。可是,如果我們依倪梁康把翻譯大致作“技術(shù)類”“文學(xué)類”和“思想類”的區(qū)分,①倪梁康:《譯者的尷尬》,《讀書》2004年第11期,第90頁。那么,也許我們會(huì)同意德里達(dá)以及德里達(dá)式的本雅明的說法:原文,尤其是思想類翻譯,其動(dòng)力來自于思想自身的吁請,因?yàn)椤拔摇辈辉摫贿z忘,因?yàn)椤拔摇北仨毨^續(xù)生存,“我”必須死后重生。②[法]雅克·德里達(dá):《巴別塔》,《論瓦爾特·本雅明:現(xiàn)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郭軍、曹雷雨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頁;J.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385.被思想召喚著甚或“脅迫”著去翻譯,這是我們常常見到的譯者們的表述。
至于第二個(gè)問題,現(xiàn)在幾乎不會(huì)有人天真地作出肯定回答了,但大家對于走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的觀點(diǎn)卻大相徑庭,例如,有人堅(jiān)持字面直譯,有人提倡詮釋式翻譯,有人聲稱翻譯即背叛。與所有這些回答相對,德里達(dá)一方面認(rèn)為,翻譯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不走樣是不可能的,走樣的程度會(huì)超出我們的想象,達(dá)到容忍的極限:“這里我們觸及到翻譯的極限……純粹不可譯的與純粹可譯的在此相互交匯。”③[法]雅克·德里達(dá):《巴別塔》,《論瓦爾特·本雅明:現(xiàn)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郭軍、曹雷雨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9頁。在德里達(dá)看來,每一個(gè)思想、每一個(gè)文本都是獨(dú)一無二的,每一次翻譯不僅會(huì)面臨另一種語言中符號帶來的新的意義鏈的生產(chǎn)和流動(dòng),更嚴(yán)重的是,還會(huì)面臨這種語言系統(tǒng)在總體上的規(guī)制,在意義的無法追蹤的、無限的延異中,思想隨時(shí)都有失去自身的風(fēng)險(xiǎn)。在這個(gè)意義上,翻譯成了一件既無必要也不可能的事情。
如此一來,翻譯成了不可能的可能、沒有必要的必要,思想的擺渡究竟要如何進(jìn)行?若要回答這個(gè)難題,我們需要回到一個(gè)更基本的問題:思想是如何發(fā)生和傳播的?它和語言的關(guān)系如何?讓我們從現(xiàn)象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對這兩個(gè)問題做一點(diǎn)思考。我們從第二個(gè)問題開始。眾所周知,自古希臘哲學(xué)開始,思想和語言(當(dāng)然還有存在)的同一性就已確立并得到了絕大部分思想家的堅(jiān)持和貫徹。在現(xiàn)象學(xué)這里,初看起來,各個(gè)哲學(xué)家的觀點(diǎn)似乎略有不同。胡塞爾把思想和語言的同一性關(guān)系轉(zhuǎn)換為意義和表達(dá)的交織性關(guān)系。他在早期就曾明確指出,表達(dá)不是某種類似于涂在物品上的油漆或像穿在它上面的一件衣服。①[德]胡塞爾:《純粹現(xiàn)象學(xué)通論》,李幼蒸譯,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第351頁。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言語聲音與意義是源初地交織在一起的。他的這個(gè)觀點(diǎn)一直到其晚年的“幾何學(xué)的起源”中都未改變。海德格爾則直接把思想與語言的同一性跟思與詩的同一性劃上了等號。在德里達(dá)的眼里,任何把思想與語言區(qū)分開,并將其中的一個(gè)置于另一個(gè)之先的做法都屬于某種形式的中心主義,都必須遭到解構(gòu)。在梅洛-龐蒂看來,語言不能單純被看作思維的外殼,思維與語言的同一性應(yīng)該定位在表達(dá)著的身體上。為什么同為現(xiàn)象學(xué)家,有的承認(rèn)思想與語言的同一性,有的僅僅認(rèn)可思想與語言的交織性呢?
這種表面上的差異其實(shí)源于思考語言的視角。當(dāng)胡塞爾從日常語言的角度考察意義和表達(dá)的關(guān)系時(shí),他看到的是思想與語言的交織性,可當(dāng)他探討純粹邏輯句法的可能性時(shí),他倚重的反而是作為意向性的我思維度。②分別參見[德]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譯,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第11章;《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研究和第5研究;《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章等等。在海德格爾那里,思想的發(fā)生來自存在的呼聲或拋擲,而語言又是存在的家園,因此,思想和語言在存在論上必然具有同一性,但在非本真的生存中,領(lǐng)會(huì)與解釋卻并不具有同一性。不過,它們的交織性是顯而易見的:沒有領(lǐng)會(huì),解釋無處“植根”;沒有解釋,領(lǐng)會(huì)無以“成形”。
③[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shí)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第32節(jié)。解構(gòu)主義視思想和語言的交織為理所當(dāng)然,但當(dāng)?shù)吕镞_(dá)晚期把解構(gòu)主義推進(jìn)到“過先驗(yàn)論”的層面時(shí),④關(guān)于“過先驗(yàn)論”,可參見方向紅:《過先驗(yàn)論:再論德里達(dá)政治哲學(xué)中的準(zhǔn)先驗(yàn)維度》,《吉林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5期,第106~111頁。他自認(rèn)為他的先驗(yàn)論比胡塞爾走得更遠(yuǎn)更徹底。在那里,思想和句法、理念和準(zhǔn)則尚未分裂為二。在梅洛-龐蒂的文本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失語癥患者由于失去思想與言語的交織性而帶來的各種癥狀,也可以看到在身體知覺中思想與語言的同一性發(fā)生,因?yàn)檎Z言與對語言的意識須臾不可分離。
⑤[法]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姜志輝譯,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第228~265頁。
也許,我們可以把與思想交織在一起的語言稱為普通語言,把與思想同一的語言稱為“純語言”(本雅明語)⑥梅洛-龐蒂把語言分為“能表達(dá)的言語”(parole parlante)和“被表達(dá)的言語”(parole parlée),有異曲同工之妙。參見[法]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姜志輝譯,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第255頁。。各民族的日常語言、科學(xué)語言、非本真的生存論語言等等都屬于普通語言,而純粹邏輯句法、本真的生存論語言、“過先驗(yàn)論”語言以及身體的表達(dá)性都屬于“純語言”。在對語言作了這樣的劃分之后,上述現(xiàn)象學(xué)家的種種分歧也就不復(fù)存在了。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回到第一個(gè)問題了。很明顯,作為“純語言”的語言涉及思想的發(fā)生,而作為普通語言的語言則與思想的傳播密切相關(guān)。我們這里嘗試從梅洛-龐蒂的身體現(xiàn)象學(xué)出發(fā),對思想的發(fā)生進(jìn)行描述。首先需要辯護(hù)一點(diǎn)的是,以身體為支點(diǎn)探討“純語言”和思想的關(guān)系是合適的,因?yàn)檫@里的身體不是經(jīng)驗(yàn)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眼里的身體,也不是自然科學(xué)意義上的身體,而是“現(xiàn)象的身體”,即經(jīng)過現(xiàn)象學(xué)還原的且“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論身體。這樣的身體在梅洛-龐蒂這里正是思想和純粹語言形成節(jié)點(diǎn)的場所:⑦[法]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姜志輝譯,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第300~301頁。思想在成形之前首先是某種無以名狀的體驗(yàn),而作為現(xiàn)象的身體以某種生存論的變化體驗(yàn)著這種體驗(yàn);語詞在對事件命名之前首先需要作用于我的現(xiàn)象身體并形成節(jié)點(diǎn)。例如,一方面是頸背部的某種僵硬感,另一方面是“硬”的語音動(dòng)作,這個(gè)動(dòng)作實(shí)現(xiàn)了頸背部對“僵硬”的體驗(yàn)結(jié)構(gòu)并引起了身體上的某種生存論的、朝向節(jié)點(diǎn)的運(yùn)動(dòng);再比如,我的身體突然產(chǎn)生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似乎有一條道路在身體中被開辟出來,一種震耳欲聾的感覺沿著這條道路侵入到身體之中,并在一種深紅色的光環(huán)中撲面而來,我的口腔不由自主地變成球形,做出“rot”(德文,“紅”的意思)的發(fā)音動(dòng)作,這時(shí)一個(gè)新的節(jié)點(diǎn)宣告完成。顯然,在思想的發(fā)生階段,體驗(yàn)的原始形態(tài)和思想的最初命名在現(xiàn)象的身體中是同一個(gè)節(jié)點(diǎn)的發(fā)生過程,就是說,思想與語言是同一的。
在思想的傳播階段,一個(gè)民族的思想與該民族特有的語音和文字系統(tǒng)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思想立于體驗(yàn)之上,每個(gè)體驗(yàn)總是連著其他體驗(yàn)。至于同樣的一些體驗(yàn),為什么對于某些民族來說,它們總是聚合在一起,而對于另一些民族來說,卻又互不相干,其答案可能隱藏在一個(gè)民族的生存論境況中。我們知道,每個(gè)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一個(gè)民族帶有共性的體驗(yàn)必定受制于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系統(tǒng)和社會(huì)歷史狀況,并因此而形成特定的體驗(yàn)簇。這些體驗(yàn)簇在口腔不由自主的發(fā)音動(dòng)作中發(fā)出該民族的語音之后,表現(xiàn)在普通語言上就是某些聲音或文字總是以聯(lián)想的方式成群結(jié)隊(duì)地出現(xiàn)。換言之,與體驗(yàn)簇相對的是語音簇和語詞簇。這就為思想的翻譯或擺渡帶來了挑戰(zhàn):如何在一個(gè)民族的語詞簇中為處于另外一個(gè)民族的語詞簇中的某個(gè)語詞找到合適的對應(yīng)者?
這看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每個(gè)民族都有自己獨(dú)特的風(fēng)土人情和社會(huì)歷史傳統(tǒng),一個(gè)語詞在一個(gè)民族中所引發(fā)的體驗(yàn)和聯(lián)想在另一個(gè)民族中如何可能完全對應(yīng)?就連本雅明也說,即使同樣是面包,德文的“Brot”(面包)與法文的“pain”(面包)在形狀、大小、口味方面給人帶來的體驗(yàn)和引發(fā)的聯(lián)想也是非常不同的。①W.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London:Routledge, 2000, pp. 15ff.日常詞匯的翻譯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描述細(xì)膩、表述嚴(yán)謹(jǐn)?shù)乃伎剂恕?墒牵诂F(xiàn)實(shí)中,翻譯的任務(wù)似乎已經(jīng)完成,不同民族長期以來成功的交流和溝通反復(fù)地證明了這一點(diǎn)。其中的理由也許可以從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得到說明。每個(gè)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這個(gè)世界是主觀的、獨(dú)特的,可盡管如此,不同的生活世界還是具有相同的結(jié)構(gòu)的。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解答本雅明的擔(dān)憂:雖然“Brot”和“pain”不是一回事,但是,由面粉發(fā)酵并經(jīng)烘焙的可充饑之物是它們的共同特征。在結(jié)構(gòu)性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允許用這兩個(gè)詞彼此作為對方的對等詞。
可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翻譯嗎?思想的擺渡可以無視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的差異而進(jìn)行嗎?僅僅從共同的特征、功能和結(jié)構(gòu)出發(fā),充其量只是一種“技術(shù)的翻譯”,而“思想的翻譯”,當(dāng)然也包括“文學(xué)的翻譯”,必須最大限度地把一門語言中的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帶進(jìn)另一門語言。如何做到這一點(diǎn)呢?把思想的發(fā)生和向另一門語言的擺渡這兩個(gè)過程聯(lián)系起來看,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新的思路。
在思想的發(fā)生過程中,思想與語言是同一的。在這里,體驗(yàn)和體驗(yàn)簇匯聚為梅洛-龐蒂意義上的節(jié)點(diǎn),節(jié)點(diǎn)表現(xiàn)為現(xiàn)象學(xué)意義上的“先驗(yàn)的聲音”或海德格爾所謂的“緘默的呼聲”②關(guān)于這種呼聲的進(jìn)一步探討,可參見方向紅:《“存在的要求”還是“天父的要求”——試論海德格爾與馬里翁的“呼聲”現(xiàn)象學(xué)》,《中國現(xiàn)象學(xué)與哲學(xué)評論》第13輯(現(xiàn)象學(xué)與神學(xué)),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157~169頁。。這樣的聲音或呼聲通過某一群人的身體表達(dá)出來,便形成這一民族的語言,這個(gè)語言包含著這一民族的詩—史—思,這個(gè)民族的某位天才的詩人—史學(xué)家—思想家用自己獨(dú)特的言語文字創(chuàng)造性地將其再現(xiàn)出來,一部偉大的作品便成形了。接下來的翻譯過程其實(shí)是上述思想發(fā)生進(jìn)程的逆過程。譯者首先面對的是作品的語言,他需要將作者獨(dú)具特色的語言含義和作品風(fēng)格擺渡至自己的話語系統(tǒng)中。譯者的言語文字依托的是另一個(gè)民族的語言系統(tǒng),而這個(gè)語言系統(tǒng)可以回溯至該民族的生存論境況,即該民族的體驗(yàn)和體驗(yàn)簇以及語詞和語詞簇。譯者的任務(wù)不僅是要保留原作的風(fēng)格、給出功能或結(jié)構(gòu)上的對應(yīng)詞,更重要的是,找出具有相同或類似體驗(yàn)或體驗(yàn)簇的語詞或語詞簇。
譯者最后的任務(wù)是困難的、看似無法完成的,因?yàn)槊總€(gè)民族的社會(huì)歷史處境和生存論狀況都不盡相同,他們的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有可能交叉,但絕不可能完全一致,如何能找到準(zhǔn)確的翻譯同時(shí)涵蓋兩個(gè)語言相異民族的相關(guān)的體驗(yàn)簇?可是,另一方面,這個(gè)任務(wù),用德里達(dá)的詞來說,又是絕對“必要的”,因?yàn)榉g正是要通過對那個(gè)最合適語詞的尋找,再造原作的體驗(yàn),以便生成我們自己的體驗(yàn),并以此為基礎(chǔ),擴(kuò)展、扭轉(zhuǎn)我們的體驗(yàn)或體驗(yàn)簇且最終固定在某個(gè)語詞或語詞簇上。
尋找最合適的表達(dá),或者說尋找“最確當(dāng)?shù)姆g”(德里達(dá)語),是譯者孜孜以求的理想。這個(gè)理想注定是無法完全實(shí)現(xiàn)的。德里達(dá)曾借用《威尼斯商人》中的情節(jié),把“最確當(dāng)?shù)姆g”比喻為安東尼奧和夏洛克之間的契約遵守難題①J.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365ff, esp. p. 377.:如何可以割下一磅肉而不流一滴血?與此類似,如何可以找到“最確當(dāng)?shù)摹闭Z詞或語詞簇而不擾動(dòng)相應(yīng)的體驗(yàn)或體驗(yàn)簇?德里達(dá)并沒有給我們提供答案,他最終讓我們求助于鮑西亞式的慈悲和寬容。
除了走向倫理要求,我們真的就無路可走了嗎?也許張世英的“兩種目標(biāo)”說可以給我們提供啟發(fā)。
四、關(guān)于“最大相通點(diǎn)”的設(shè)想
誠然,德里達(dá)關(guān)于翻譯的“不可能的可能”“沒有必要的必要”的說法以某種辯證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現(xiàn)象學(xué)翻譯理論遭遇的困境,并從中引出了翻譯理論的倫理學(xué)基礎(chǔ)問題。可是,辯證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不恰恰是對現(xiàn)象學(xué)的偏離嗎?我們能不能繼續(xù)沿著現(xiàn)象學(xué)的道路面對這里的困境呢?
考察德里達(dá)的“最確當(dāng)?shù)姆g”這個(gè)表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隱藏著張世英所批判的“相同性”思維。翻譯的最高理想是實(shí)現(xiàn)兩個(gè)不同民族的體驗(yàn)和體驗(yàn)簇、語詞和語詞簇的完全相同。換言之,不流一滴血的割肉才是最完美的割肉。當(dāng)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在所有可能的翻譯中找到一個(gè)最合適、最恰當(dāng)?shù)姆g也是值得追求的。正如割肉,既然不可避免地要流血,那么流血越少,證明割肉的手段越高明。顯然,德里達(dá)在這里把現(xiàn)成的后備術(shù)語或待選術(shù)語之間的比較當(dāng)成翻譯的最基本手段了。
難道翻譯通常不正是在既有的術(shù)語概念之間進(jìn)行揀選嗎?難道這意味著每次都要求我們創(chuàng)造新的概念?我承認(rèn),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我們并不是隨時(shí)創(chuàng)造新的概念。實(shí)際情況是,對于重要的語詞,我們常常有多個(gè)與之相對應(yīng)的翻譯,我們檢視這些譯詞,對比它們在語義和風(fēng)格上與原文的契合度,我們甚至還會(huì)更進(jìn)一步,對翻譯和被翻譯的語詞在各自文化的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中可能引起的效應(yīng)及其范圍進(jìn)行權(quán)衡。
然而,這樣的做法仍然是某種形式的相同性思維,或者說仍然保留了以相同性作為追求目標(biāo)的印跡。因?yàn)樗菑臉I(yè)已完成的語詞向與該語詞相關(guān)的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進(jìn)行“認(rèn)識論的”回溯,而不是相反,即從體驗(yàn)簇或語詞簇向業(yè)已完成的語詞進(jìn)行“生成性”回溯。前一種回溯方式把交叉點(diǎn)或匯通點(diǎn)當(dāng)成現(xiàn)成的對象,這會(huì)導(dǎo)致翻譯語詞的選擇被固化在一個(gè)或幾個(gè)語詞簇中,甚至被固定在詞典的釋義框架中;而后一種回溯方式則把交叉點(diǎn)甚至相同點(diǎn)當(dāng)成形成中的非對象,這可能導(dǎo)致某個(gè)處于完全不相干的語詞簇中的語詞作為選擇對象凸顯出來。
后一種回溯方式對核心術(shù)語的翻譯至關(guān)重要,我們不妨試著從張世英的“兩種目標(biāo)”說略作說明。對于一個(gè)核心術(shù)語或關(guān)鍵概念,譯者必須進(jìn)入原語言中去,找到相關(guān)的語詞簇,發(fā)掘一系列相聯(lián)的思想體驗(yàn)或體驗(yàn)簇,并以現(xiàn)象學(xué)的方式展示純語言向普通語言的諸種轉(zhuǎn)換過程,即梅洛-龐蒂意義上的諸多“節(jié)點(diǎn)”的形成過程;然后帶著這些語詞簇和體驗(yàn)簇返回到目標(biāo)語言中去,并將其置于純語言的基礎(chǔ)之上,考察它們在目標(biāo)語言中從純語言向普通語言的諸種轉(zhuǎn)換過程,即梅洛-龐蒂意義上的諸多“節(jié)點(diǎn)”的形成過程;最后對形成的諸多節(jié)點(diǎn)(當(dāng)然也可以說是“交叉點(diǎn)”)進(jìn)行甄別、比較和篩選,找出最能引發(fā)最主要思想體驗(yàn)或體驗(yàn)簇、最能涵蓋最主要語詞或語詞簇的節(jié)點(diǎn)或交叉點(diǎn)。這也就是我所謂的“最大相通點(diǎn)”。
依據(jù)這一回溯方式,在翻譯實(shí)踐上會(huì)帶來兩個(gè)后果。首先,也許某個(gè)古語、成語、俚語、俗語恰好符合要求成為“最大相通點(diǎn)”,這時(shí),這個(gè)語詞獨(dú)特的思想意義和體驗(yàn)價(jià)值便凸顯出來,為該語言中的人們重新認(rèn)識并為他們打開早已封閉的體驗(yàn)空間和意義關(guān)聯(lián);其次,也許根本找不到“最大相通點(diǎn)”。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提供一個(gè)勉強(qiáng)相通的術(shù)語,不如創(chuàng)造一個(gè)新詞。因?yàn)榍罢邥?huì)通過一個(gè)似是而非的節(jié)點(diǎn)把該語言的讀者導(dǎo)入到與原語言完全不同的另一個(gè)體驗(yàn)系統(tǒng)和語詞系統(tǒng)之中,而后者則會(huì)由于新詞帶來的間距化效應(yīng)而最大程度地聚攏并維持原來的體驗(yàn)系統(tǒng)和語詞系統(tǒng),并有可能在后來的應(yīng)用中為這個(gè)民族帶來新的體驗(yàn)簇和語詞簇,這對于擴(kuò)展該民族的體驗(yàn)范圍、豐富其語言表達(dá)、改造其體驗(yàn)和語言的關(guān)聯(lián)結(jié)構(gòu)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