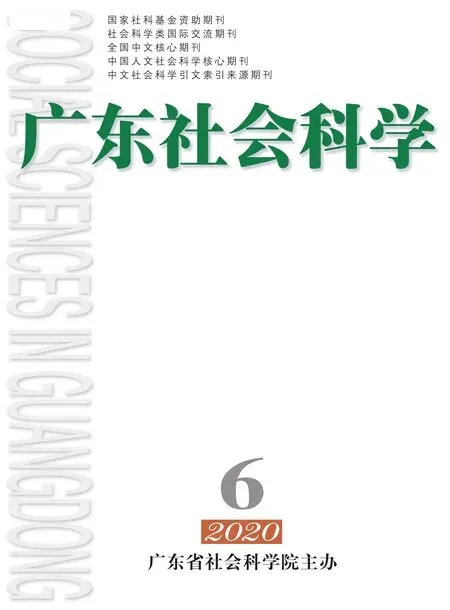觀念形而上學與直觀形而上學:心學思想中的二重向度與道德悖論
黃 琳
關于宋明理學的劃分,有理學、心學與氣學,陽明后學又有歸寂、現成與修正派的區分,但如果我們從建構哲學的基本形態出發,并以此為基準,將宋明理學諸儒諸派歸置其中,一一驗測,重新分派、歸類、驗證、實現,打破舊有的分派體系,目的是為了梳理宋明理學層面隱匿涵藏的普遍性的哲學問題,并針對其流弊,提出基于哲學形態理論缺陷的修正思路。陽明后學之所以議論紛紜,演變繁雜,究其原因,端始于陽明思想中潛存的雙重進路。因不重視概念的清晰、明辨、清理并建構,后學思想滋生困頓在所難免。明代心學思想流弊深遠,引起清代思想家的集體反思,抉本溯源,檢醒其中的理論缺漏,跳出自說自話而實則因缺乏哲學形態、理論系統的構建而造成似渾融而實混沌的理論困局。
一、觀念形而上學與直觀形而上學
康德在自然理性之域,認為“科學知識”要防止“空洞的概念”僭越至“事物自身”,防止概念自己提供一個直觀,認為由概念、觀念提供直觀是道德實踐域的事情。①與反對概念不包含現象而批判“純粹理性”不同,在道德論域,康德為了確保將道德奠基在理性的法則之上,并視之為先天義務,不僅將“內交”“要譽”“惡聲”的計較考量,亦隨即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德情感摒除在外。康德認為道德法則,(1)不能從經驗建立;(2)不能從“范例”引申;(3)不能從“人性底特殊屬性”、“脾性、性好,以及‘自然的性向’推演”;(4)甚至亦不能從“上帝底意志”來建立。若由之所立的道德法則決定我們的意志、行動,康德稱之為“道德之他律”(Heteronomy of the will)。②但是,康德亦由此無從說明道德究竟如何直接左右人的意志、行動,道德縱然純而又純,惟理性與之相關。但是,道德不僅失去內容,亦失去了動力,實踐理性、道德理性縱然純粹,卻無從知曉如何與實踐、踐履間產生任何真實的聯系。③
康德認為,真正的道德必源自主體的“善良意志”,道德應出自自由自律的道德法則,而非僅與外在形式化的理性規范若合符節。康德關注自由自律道德法則的建立,但對于普遍、形式的道德律,如何與真實的道德實踐相聯卻力不從心,最終惟倚附宣稱與之早已兩訖的宗教神訓,化解道德理性無從在經驗世界中開顯的道德困境。“善良意志的自我立法,相應地表現為超驗理性向自我頒布律令”,所謂“善良意志”,亦即理性化的意志,所以,在道德的實踐理性之域,康德以形式因為動力因,雖然解釋了道德秩序何以可能,但實則仍未能對現實域中的道德踐履、道德行為作出具體的說明。④
在休謨、盧梭等人看來,道德的動力因始終是一個問題,如果道義本身沒有力量,私意欲念之昏明開塞又如何能夠自行凈化本不純凈純粹的自身?形上之域的道德理性是一凝定靜止的超驗存有,若僅具邏輯推繹處的統攝,實則缺乏真實的動力精神并主宰,靜涵靜攝的道德理性無法真實地影響、決定現實的情感、意志與行動。休謨認為,“理性的作用在于發現真或偽”⑤,但是,即便理性能夠判斷是非善惡美丑,也不必然能夠導向行善抑或止惡。所以,休謨認為,理性不能成為動力因,因為“理性完全不活動,永不能成為像良心或道德感那樣,一個活動原則的源泉”⑥。休謨以非理性的情感為道德奠基,理性既然虛弱無力,那么,道德行為應以情感為動力,理性惟借助情感才能影響人的行為。⑦康德認為理性本身虛謙無力,只能如明鏡鑒照,知善知惡,與朱熹“理弱氣動”“理靜氣動”“活人騎馬”的理與氣、性與情的悖論若合符節。但是,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在道德奠基的問題上,都不可能像歐洲思想那樣在“情”與“理”的兩極間左右搖擺。
康德將道德法則準確無疑地奠基于理性,但隨之遭遇普遍、形式的道德理性無從過渡至具體的道德踐履、行為的困境。良知、心體、性體之道德理性是普遍、先天、先驗的道德本體,使得“心體”更多地指向超驗之域。“心統性情”,使得“心”與生命情意的感性生命有著更為契近的關系。情感、意念等非理性因素與道德理性之間,究竟是一者對另一者的統攝,抑或打開此種靜涵靜攝、空間概念化的形上哲學模態,將“情”與“理”復置于綿延流動、相互激勵、溝通交流并對治對決的關系之中?“心”統攝性情、思志,將隸屬于不同范疇的“情”與“理”統合、綜合、結合起來,絕非輕松之舉,并非一超驗橫攝、靜涵靜攝的“觀念形而上學”哲學模態可以涵攝,惟有揚棄道德理性、良知、心體、性體的抽象性與超驗性,讓“情”與“理”在對治對決的溝通交流中復歸綿延縱貫的一體一元模態。
柏格森并非要否定形而上學,而是反思理性邏輯帶給我們的,從概念到概念的觀念邏輯推繹的思維模式,認為惟沉潛至邏輯體系、理論架構的底層,復歸綿延、流動、真實的生命時間,再重新由現象升至本體的綿延縱貫之一體一元,是為區別于傳統西方觀念形而上學的直觀形而上學。⑧柏格森認為,傳統西方科學、哲學的形而上學還原是經典的凝定靜止、靜涵靜攝的二元論架構,而時間、生命、運動都是不可切分的。柏格森認為,“形而上學問題也許是被錯誤提出的”,傳統形而上學被引向去那時間之上,超越運動和變化的事物去尋找物自身與實在性,于是,形而上學成為只是或多或少的概念的人為安排,一種假設的建構。于是,形而上學宣稱超越了經驗,而實則只是取代了運動、完滿,日益深厚并富含啟示的經驗。這種經驗被一種固定、干涸、空洞的抽象取代,成為一種由若干普遍抽象觀念構成的體系。⑨由此意義而言,柏格森的“一切都已給出”,比胡塞爾的“回到事物本身”還要精辟直截、意涵深刻。
柏格森的思想是一種超越康德的努力,他認為“靜態的道德”(static morality)是關閉、凝定、靜止并業已終結的,“動態的道德”(dynamic morality)把靜止者打開,重新復歸、置身于“綿延”(Duration)流動之中。中西方的道德形上思想都面臨著根本的哲學問題,本文試圖通過來自西方的觀念形而上學與直觀形而上學與中國本土的宋明理學研究結合起來,發掘心學思想中潛隱涵藏的二重向度與道德悖論。
先秦孟子在人情發露處論性,并未說別有一未發本體,是在“志”與“氣”、“理”與“情”在一體一元縱貫的綿延流動中對治對決、感統激勵摩蕩,并最終開顯、呈露“志”對“氣”、“理”對“情”的主宰,抑或被其遮蔽。“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志可以主宰氣,氣亦可以主宰并支配志,這樣綿延縱貫一元論的直觀形而上學區別于凝定對峙、截然二元、靜涵靜攝的觀念形而上學。志對氣、性對情的主宰,并非“必然”,而只是“應然”,私意欲念的昏塞之“氣”隨時可能逆襲、反動、統攝并支配“志”或“心”,“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公孫丑上》)。⑩縱然不是絕對全體,但從周濂溪到程伊川、朱熹,更多展露的是一種超驗的觀念形而上學哲學進路,從程明道到陸象山、王陽明,則更多地展示出一種綿延俱進、一體一元縱貫的直觀形而上學哲學進路。無論是宋明理學中的濂溪、伊川、朱熹,還是陽明后學中的現成派與歸寂派,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觀念形而上學思辨建構的哲學形態,展現了二重向度的內在張力與道德悖論。
二、以“心”為名的“道德他律”
在朱熹宇宙論的架構中,理氣、道器作為生物之本與生物之具,已然內蘊一觀念形而上學的邏輯推繹關系。朱熹與王陽明對存在的考察都可化約為二重向度,朱熹以“理”為中心的超驗橫攝形上存有,與以“氣”為從屬的現實經驗的形下世界,共同構成一空間概念化的“觀念形而上學”理論體系。若從超越、形式、抽象的形上道德理性層面以觀,是為凝定靜止、空間概念化的理氣對決,若從綿延、流動的現實經驗層面以視,是為生命時間中的理氣縱貫,一體俱進,對治對決。諸如,朱熹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這天地”;“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朱子語類·理氣上》卷一)是就凝定靜止、靜涵靜攝的形上理論層面以言理,而“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未嘗離乎氣”,則是就綿延并進的現實流行層面而言理。
但是,無論朱熹如何強調理與氣的“不離不雜”,根本上仍偏于以形上之理涵攝形下之氣的理論架構,可謂“大橫攝下的小縱貫”。在朱熹的宇宙論系統下,理是一“無形跡”的“凈潔空闊的世界”,一旦運動即有形跡,便會進入感性的時空之中。但是,從太極到二氣、五行、萬物的觀念化邏輯推繹過程,只是提供了宇宙生成的模式,卻無從解決形上與形下之域的對峙,亦即理(太極)如何作為動力因,成為創化生生的生物之本的根本問題。具體至道德域,即是道德理性如何成為動力因,直接左右意志與行為的道德悖論。所以,無論如何強調一體一貫,一旦落入此種凝定靜止、空間概念化的“觀念形而上學”,理氣、性情必各執一端。朱熹在成就圓備宏闊理論體系的同時,也造成了此種哲學形態無從擺脫的悖論與痼疾,任何個體都無從逃匿形上觀念理性的規定與強迫。
沿循超驗的理論進路,邏輯推繹上的先后隨即割裂、凝定為理先氣后、理弱氣強,與經驗之域的理氣(性情)俱進、交融的二重向度并存,構成一幅繁復的思辨圖景。縱然不應外吾心以求理,但僅僅是“攝理入心”,并非可以簡單地解決此類問題,內在于主體的良知、心體、性體一樣可以成為超驗橫攝、靜涵靜攝的純粹的形式道德。
良知作為本體,首先表現為“先天之知”,而此種先天意義上的“知”,往往具有形上之學的邏輯設定、決定甚至強制義。空間概念化的形上邏輯推繹是人為的預設,與現實經驗世界的真實作用不同。王陽明有時也說,“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后。”雖然強調無先后、內外,但將道德本體、良知心體、性體作為一“寂然不動”的先驗之物,在哲學形態上已落入“本質先于存在”、凝定靜止的形上之學,故需倚賴“感觸神應”“自信得及”“保此一念”,以悟入、感通、徹悟,通過個人化的“直觀”以“觀照境界”,強調直觀、直感、感通,歸諸個體性的“經驗”神秘主義,藉此跨越道德理性與實踐、踐履間的裂隙。
良知作為內在的道德意識與理性原則,以天理為內容,王陽明稱之為“良知即理”,以彌合陸象山“心即理”所造成的理論粗疏。“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作為內在的道德理性,與康德自由自律的自覺意志頗類似但又不盡相同。“應物起念”處謂之“意”,現實的意志、意念源于“心統性情”之“情”與“理”的滾同而出。陽明一再區分良知與意念,“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良知、心體、性體,乃“至善”的道德本體,意乃“應物起念”,自然有善有惡,有是有非。
應物起念,是后天經驗活動的總稱,限定于具體境域之中的時空之域,良知作為判斷是非的理性準則,超越具體時空經驗的偶然性,由此可說“無善無惡”。陽明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良知先于經驗聞見,是先天、先驗的普遍之“知”,陽明通過良知與意念、聞見的區分,著力強調良知的先天性與先驗性,良知作為一般的理性原則,本身具有超越個體的一面。陽明以良知的先天先驗擔保其普遍有效性,與康德道德域中突出道德法則的普遍性相契近。王陽明常將良知作為凝定靜止、寂然不動、“未發之中”的本體,既有此本體論層面的設定,故已然蘊涵以“祛蔽”為中心的工夫進程。私欲意念、習俗成見都成了對良知的障蔽,“祛蔽”便成了“致知”過程中的應有之義,“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良知既是一“廓然大公”的“寂然不動”本體,潛隱著“致良知”即是一掃除蔽障、重新發現的“覓良知”過程。正基于此,陽明曰:“吾輩用功方只求日減,不求日增。”其邏輯推繹下,自然蘊含了現成派、歸寂派之為“寂然不動”本體掃除、廓清外在的雜擾與障蔽之功,惟以“覓”“悟”“守”,尋找、清理昏明開塞、私意欲念蔽障為工夫的工夫論。
無論康德,抑或朱熹,尤為重要的問題在于,先驗的道德理性與具體的道德踐履缺失真實聯系的問題。王陽明以良知的先天、先驗擔保其普遍與必然性,統攝、決定甚至強制現實中情、意、念、物(事)的實現,仍然存在割裂道德理性與實踐、踐履的潛在危險。但陽明終究未明白、透顯地講出,以“致知”與“格物”作為因果邏輯必然推繹之兩事,并非“致知”即能“格物”。“格物”,即正行為,良知并非一“只存有不活動”(牟宗三語),靜待人“覓”“悟”“守”的道德本體、靜存之理、本體之物。“格物”與“致良知”,亦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陽明并非懸空地“致知”,而是將“致知”落實在“格物”之上。
三、王陽明思想中的二重向度
良知作為先天本體,更多的是由邏輯在先的形而上普遍存在強制、決定形而下的情、意、欲、念、物(事)。但是,“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又表現了陽明心學的另一重向度,“知行合一”,絕非一超驗橫攝、凝定靜止的形而上學二元對立所能達至,而必然是“理”與“情”在綿延流動、一體縱貫中對治對決、相互激勵中開顯、呈露,抑或被遮蔽的過程,并由“心”先天統合、綜合成為現實的價值判斷與意向性,在此動態的“知行合一”過程中,打通先驗的道德理性與經驗的道德踐履、行動之間的隔斷。先驗的預設是思辨的虛構,旨在為理性本體的普遍必然性提供形上根據,陽明始終難以放棄對道德理性普遍必然性的先驗承諾,但與此同時,陽明又具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現實向度。
王陽明對現實域的關注,體現在他視“致知”與“格物”為一事,“知行合一”,根本是要致吾心良知于現實經驗世界的事事物物之上,亦即道德法則成為動力因,直接左右我們的意志、行動,而非概念化、觀念化地等同道德理性與道德實踐。楊國榮認為,“心體不是無人格的邏輯形式,它存在于主體在世的過程中”,良知“真正的境界總是將化為人的具體存在,并展開于人的實踐過程中。”與本體的現實性維度相應,理與心的融合意味著由形而上的超驗之域向個體性的現實存在的回歸。“依王陽明,人不能在自身的存在之外去追問超驗的對象,而只能聯系人的存在來澄明、開顯世界的本體性意義。”人應當在自身的存在與世界的關系中,而非脫離與世界的關系,在這之上或之外考察世界的意義。
但是,這樣的目標,若非哲學形態的轉變,單是簡單的“攝理歸心”并非必然能夠達成,更須在一“理”與“情”,良知、心體、性體與世情嗜欲在綿延俱進、對治對決的過程中解釋“致知”與“格物”。在心、意、知、物的關系上,究竟如何將存在的規定義與現實的經驗世界相聯系?將“情”與“理”復歸、投置于綿延流動、感通激勵摩蕩的對治對決、溝通交流過程中,其所形成、凝定的合力就是由“心”作出的現實、綜合的價值判斷。心統攝性情、思志,不僅僅是空間處的容納,“心”有綜合、結合“心體”之道德理性與情感、思志作出現實價值判斷的功能、職能。心在具體的時空境域中所形成、凝定的合力,亦即現實的意志、意念并指向行動的意向性。此種“動態的道德”,絕非建基于一業已扣合的觀念形而上學的宇宙模型或世界圖景的“靜態道德”。陽明曰:
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由“意”銜著心與物的兩端,而非知與物的兩端,心所發出的意向性直接導致意志、意念、行為。上述第一句王陽明所言極明,意志、意念的本體是良知,但“意”非由此良知“心體”作出,而是由“心”先天統合、綜合了在綿延俱進中對治對決、溝通交流中的“情”與“理”所凝定的合力,并做出的綜合的價值判斷。所以,“心體”不應僭越“心”的功能、職能做出現實、綜合的價值判斷。意向性的活動,是由意志、意念指向行動的方向,所謂“意向性”,是在具體境域的現實流行中,“情”與“理”、“志”與“氣”、性與欲、良知心體與昏塞之氣,在綿延俱進、對治對決的哲學形態中整合力量,最終凝定的合力所成就的“勢”之走向。
良知并非形而上學空間概念化邏輯推繹的先天預設,良知的作用與內容須在與情、意、欲、念的攜行俱進的過程中真實地開顯、呈露出來。邏輯的先天性只能展現為邏輯推繹層面的可能性,以空間概念化邏輯預設、推繹之必然,取代現實經驗世界之實然,其中隱藏著極大的誤解與危機。邏輯推繹上的預設與形而上學截然二分的觀念建構,區別于現實流行中的道德踐履,若強以之為“同一”,可謂以幻境代替實境。王陽明未曾放棄對形上本體的先驗設定,亦未完全超出思辨的哲學之域,但同時,陽明尚在綿延流動的一體縱貫中探討現象與實在。先天、超驗只是在邏輯上先于經驗活動,超離、超絕則離開現實經驗又返過來駕馭經驗,良知本體普遍、先天,但并非超絕、超離。楊國榮認為,作為思辨哲學家,王陽明對超驗性的拒斥并不徹底,對先驗與超越的區分亦非自覺明晰、前后一貫。形而上學邏輯上的先天假設就是離開現實的感應活動,落入此種哲學形態,本體的“先驗性”就升進至本體的“超驗性”之域。
綜括之,王陽明固然承認道德本體須在現實的綿延中開顯、呈露為道德踐履,但受制于以良知、心體、性體的先驗性為根據的哲學形態,王陽明似在兩者間搖擺不定。所以,陽明思想體系中存在雙層的理論架構,其一的邏輯前提仍存在以良知為一超驗本體的觀念性預設,與之相應,便有將工夫的作用限定抑或誤解為對先天本體的發現與把握的工夫論。“歸寂派”聶雙江言“歸寂”,以為能“致知”必能“格物”,由哲學形態邏輯推繹所致的工夫論,是以“致良知”為“覓良知”與“守良知”。“現成派”王龍溪言“現成”,以為“致良知”即“悟良知”“信良知”,能“悟”“信”良知,則必能應事。而事實上,王陽明“致知”與“格物”本不可分,“格物”即“正行為”,若格物處反倒無工夫,此種哲學形態、思想理路實則已然偏離孟子與陽明本意。但是,“歸寂派”以復歸虛明、虛靈的良知本體為工夫,“現成派”強調“徹悟”“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工夫樞紐雖然不同,卻并不妨礙兩派相近的哲學形態,也不可謂之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四、“心體”僭越“心”的道德悖論
王陽明認為,內圣之德實有諸己,如果僅僅依照外在的理性規范,而未能將一般的理性原則融合于內在的心體,行為則往往如同做戲,“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傳習錄上》)道德若非發自主體內在的道德理性、良知心體,只是亦步亦趨,遵照外在的道德規范,則易生出矯飾與偽詐。宋明理學當中,從哲學形態層面以言,最值得警惕的正是貌似“攝理歸心”,實則是偽裝成以“心性”為名的自由自律主體性的道德“他律”。其特點就是不僅具備道德律的普遍性,又實難揚棄其超絕、超離、純粹并強制的超驗性,并進而趨向絕對、橫攝、獨斷經驗世界中的情、意、物、事。事實上,不僅程朱要求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康德以實踐理性的超越性擔保道德律中純粹、普遍、形式化的道德理性,而陽明思想中亦潛存二重向度。
不可否認,王陽明思想中有“以知為行”“以念為行”“銷行入知”的傾向,因此,在論“知行合一”宗旨時,表現出“銷知入行”與“銷行入知”的雙重傾向。所謂“知行合一”,對于“合一”的抽象理解,建基于邏輯推繹“A=A”同一律,邏輯地導向二者界限的消融。正因如此,方會產生類似于禪宗的“以作用為性”,將先天、形式、至臻純粹的“道”降低為現實中的偶然作用,以外在機緣消解,甚至反噬內在的道德本體,此時良知失其主宰,故須下工夫,此即“致良知”。當自然流行中世情嗜欲的昏塞之“氣”,橫絕、逆襲、反動,統攝并支配“志”,則會陷入“依于理卻反失其理”的道德悖論而不自知。
高揚超驗、純粹良知、心體、性體之道德理性,以“心體”僭越“心”,使之純而又純、超離超絕、超驗橫攝、靜涵靜攝。使之束之高閣,惟理性與之相關,故惟具觀念形而上學的統攝與強制,喪失了心體與情意物事間的真實聯系,竟至得出以情感、思志、意念、物事,消解、逆襲、反動道德本體之道德理性的“依于理卻反失其理”的道德悖論。良知、心體、性體無從成為動力,左右人的意志、行動,正是基于此種空間概念化觀念形而上學之下,“情”與“理”所致的道德理性與道德踐履的二律背反。
王龍溪的一體俱無、一了百當,是落入此種哲學形態,觀念化、概念化地等同、同一道德理性與踐履的邏輯推繹結果。王龍溪特別反對“意見情識”的雜擾,并以此非難“修證派”諸儒,將良知心體的道德理性由經驗世界中分割、孤立出來,先驗而在,其結果是喪失二者聯系的任何可能。“心體”對“心”的僭越,斬斷道德理性與實踐、踐履的真實聯系,導致現成派及之后的泰州學派離開理以求心,化心為理,最終以心為理的邏輯進路。抽去普遍的道德本體,而與禪宗由“緣起說”及“自心是佛”的觀念出發,強調“以作用為性”頗為相似。
但是,不僅良知“心體”,情意生命更無從僭越“心”做出現實的價值判斷。依陽明之見,從源頭處說,心意知、心性情本是同體,故倡良知之說,因此,先天、超驗是指在邏輯上先于經驗的活動,“理”僅在邏輯上先于“情”,性非情的本體,情非性的發用,情感并非現實經驗世界中具體的現象。“情”與“理”是屬于不同范疇、功能、職能的異質者(heterogeneous),不能以一者涵攝另一者,惟有打開趨于僵化的靜涵靜攝的理論架構,建構一在綿延流動中對治對決、溝通交流、相互激勵、一體縱貫的動態(dynamic)、開放(open)、糾纏中開顯、呈露的“直觀形而上學”,與空間概念化、超驗橫攝的“觀念形而上學”,是全然不同的哲學形態。
縱然不是絕對的全體,但從周濂溪到程伊川、朱熹,更多展露的是一種超驗的觀念形而上學”的哲學進路,從程明道到陸象山、王陽明,則更多地展示出一種綿延俱進、一體一元、綿延縱貫的直觀形而上學哲學進路。若以良知本體為一超驗橫攝、普遍純粹的道德法則,抽離現象,先驗而在,強制、決定現實踐履的實現,實則截斷了道德理性與道德踐履間的真實聯系,建基于此的觀念形而上學哲學形態,縱然“攝理歸心”,但最亦終無從逃匿體與用、已發與未發、道德理性與行動踐履的二元對立。無論是宋明理學中的周濂溪、程伊川、朱熹,還是陽明及其后學之現成、歸寂派,都或多或少地帶有觀念形而上學思辨建構的形上形態,展現了心學的二重向度的內在張力。
試圖超越這種緊張,勢必以哲學視域的轉換為前提。一旦良知心體被設定為一“本質先于存在”的凝定靜止、空間概念化的形上理論架構,就自然引向一個跳脫現實的經驗之流,惟探尋形上超驗、靜涵靜攝本體的“覓”“悟”“守”的工夫過程,無從逃避道德理性與踐履間的隔斷。總之,“心”的范疇統攝性情、思志,廣義的“心”不僅包含普遍之理的道德理性、良知、心體、性體,還涵攝情感情緒、思志思慮、意志意念的情意生命。“心”具有綜合、結合“情”與“理”,并做出現實綜合判斷的職能、功能,“心體”不應僭越“心”做出現實的價值判斷。
結 語
王陽明思想兼具二重向度:一重偏重邏輯推繹的形上本體對形而下的情、意、物、事的規定,一重偏重在綿延流動的現實經驗世界中的生成與開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中,王陽明“心學”的哲學形態可謂之“大縱貫下的小橫攝”,把靜涵靜攝、超驗橫攝的“靜態道德”打開,將“情”與“理”復歸于綿延俱進、對治對決的“動態道德”之中。“從本體上說工夫”,接近以形上的邏輯推繹以言現實經驗世界的道德實踐;“從工夫上說本體”,接近在綿延俱進的一體縱貫理路中呈露、開顯本體,是在工夫中開顯本體的理論進路。相較之程朱“理學”,“心學”從某種意義上完成了哲學視域的轉換,但卻未必是形上形態、形上理路的根本轉變。陽明以普遍之理為“良知”心體、性體的內容,以內圣為理想之境,同樣具有超越既成存在的要求與性質。縱然“攝理歸心”,仍潛存以“心”為名的道德他律,與以超驗橫攝的道德“心體”僭越“心”所致的道德悖論。道德理性從經驗的世界中徹底地分割出來,孤立地如此徹底,希冀它純而又純,先驗而在,以致惟理性與之相關,又會把我們拖入一條與此相反,亦即失去與之聯系任何可能的險途之中。凝定靜止的超驗之理無從與真實的現象界發生聯系,這是在凝定靜止、空間概念化的“觀念形而上學”之下,體與用、理與情、已發與未發、本體與現象二元割裂所致的結果,這樣的哲學形態最終指向的是一純粹、普遍的形式道德與法則形式。
①葉秀山:《小文章,大問題——讀康德〈論哲學中一種新近升高的口吻〉》,杭州:《浙江學刊》,2011年第6期,第7頁。
②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5年,第110頁。
⑤⑥⑦休謨:《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94、494、503頁。
⑧⑨[法]柏格森:《思想與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9頁。
⑩黃琳:《道德自覺意志之顯現與存養——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讀》,天津:《道德與文明》,2017年第5期,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