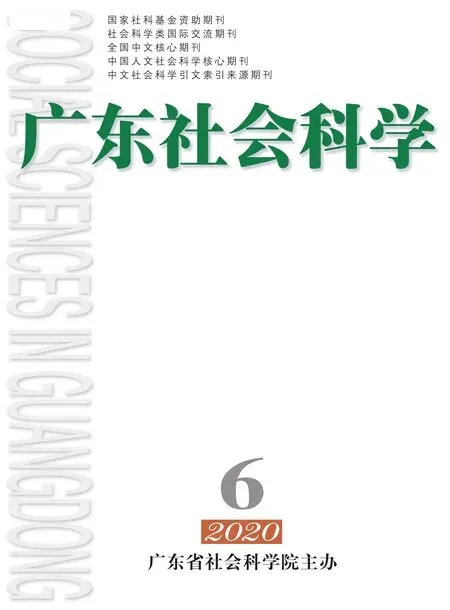從“消費異化”到消費者主體性:西方消費研究理論的變遷及其社會學反思*
張敦福
對消費的負面評判,在近來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是常見的。似乎與韋伯節制欲望的天職觀相對,丹尼爾·貝爾更多地把消費看作是享樂主義。在他看來,美國的清教思想已經淪落成為乖戾的小城鎮心理;世俗的霍布斯學說養育了現代主義的主要動機——追求無限體驗的貪欲。①在消費社會學理論新著中,瑞澤爾把沒有內涵,沒有特色,沒有個性,由某個中心建構和控制的、比較而言缺乏特定內容的消費的社會形式,小自麥當勞、沃爾瑪、可口可樂、信用卡,大至醫療、教育和娛樂等,稱為“虛無之物(nothing)”。②延展馬克思的“異化”理路,結合消費社會的實際,葉啟政尖銳地指出“在消費社會中,資本家及其同路人不斷利用傳播媒體創造虛無縹緲的符號消費和影像消費來刺激消費大眾無止境的消費欲望,挖起消費大眾身邊的錢財,從而完成‘階級’結構性的‘剝削’。這時被‘剝削’的對象,很明顯地已由無產階級的勞工本身,跨越特定的階級門檻,擴及廣大的消費大眾,這當然也包括其他資本家及其同路人自身”。③
消費和消費主義本身可能沒什么對錯之分,對消費的價值評判恰恰是值得謹慎對待的。當西
方消費者社會遭到批判時,似乎也應當看到正是歐美開啟了環境保護運動。因而,一個重要的、值得進一步回應的問題是,消費者是否是毫無反思、毫無反抗的被動接受者?這個問題背后的理論魅惑是,社會生活中的個人和群體是否只是社會化、制度化的木偶,還是有其主動性、能動性的行動者?進而值得探究的是,這類觀點的理論假設和范式是什么?有無別的可選擇的更恰切的理論范式?
一、“異化”概念的多變性
對社會科學家來說,“異化(alienation)”是個熟悉而神秘的概念。“異化”與勞動、商品、資本這些術語的緊密關系,加大了其復雜難解的程度。這個概念引起了很多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興趣,也增加了他們的困惑,這個概念在更廣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使得其深奧難解的程度變本加厲了。結果,即便是在基本的含義方面人們也難以達成一致,因而不可避免充滿混亂的看法。晚年的馬克思也覺得這個概念是“哲學上的廢話(philosophical nonsense)”,不再使用它了。④
關于青年馬克思的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ur)學說,已有太多論述,此不贅述。馬克思對于消費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斷。他看到,在異化勞動條件下,相對于生產勞動,工人的消費被邊緣化,工人的生活世界被擠壓,工人工作時間之外的自由活動蕩然無存。在馬克思看來,那時的國民經濟學對工人生活欲望和消費需求的克制十分賣力。“國民經濟學,盡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縱欲的外表……它的基本教條是:自我克制,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越少上劇院、舞會和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就越能積攢,你那既不會被蟲蛀也不會被賊盜的寶藏,即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現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財產就越多,你異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疏離生命也積累得越多。”⑤這些論述,很容易被理解為,馬克思不僅把異化看作資本主義勞動場所的重要特征,而且把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和消費領域也看作是與工人的生命疏離了,看作是異化的。“勞動異化”由此合乎邏輯、在后來也合乎事實地被理解、被轉化為“消費異化”。
在美國的工業自動化遭遇了異化現象后,異化這個詞已經流行開來,并從歐洲流傳到美國。對那時的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神學家、哲學家、詩人和公眾人士而言,“異化”成了一個方便的標簽,所有那些生產流水線工人和廣告制作者遭受的類似折磨——孤獨感、麻木感和認同缺乏——均被稱為“異化”,⑥只是這類學者名單中社會學家的 名字開始增多。到了1960年代,人們對社會上核心機構(如政府)的異化——袪魅感(the sense of disenchantment)、疏離感、孤獨感也有增無減。⑦然而,這個概念的含混、多變之處也令一些學者頭疼。同樣使用異化這個概念,弗洛姆指涉人在自己創造的社會力量面前的無力、瘋狂;P.Lasslett哀嘆家庭作為孤獨感防御大堤的潰決;在H.Swados的筆下,現代工廠工人如同被困的動物;R.Maclver發現現代工業社會人類的休閑被誤用了,人們并沒有獲得享受休閑的訓練和技能;Ernest van den Haag發現,人不能與自己快樂相處,不得不尋求別的偶像來模仿;在米爾斯(C.W.Mills)眼里,現代大眾社會缺乏個人表達,人們更多地接受觀點而非表達意見,且表達出來的觀點也較少伴隨有意義的行動。⑧“異化”的含義如此多變,以至于Denise指出:異化在本質上是個變色龍,它在不同的理論家手里被重新改造成不同的東西。⑨Johnson也不客氣地斷定,異化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仔細分析起來它沒有實質意義;這個概念試圖解釋一切,結果卻什么也解釋不了。⑩
1950~1970年代,圍繞異化的不同術語之間的關系成為現代爭論和辯論的主題。Williamson 和Cullingford看到,“異化”在語義上是混亂的,作為測量工具在信度和效度上是可疑的,作為概念工具是缺乏公信力的。Schacht警告說,人類經歷中沒有這種值得關注的“異化”現象,“設想它、探尋它是一種堂吉訶德似的幼稚”。1970年代,在進入社會學話語體系后,異化擴展到后來的教育學、社會心理學。由于“異化”對教師和教育理論家有用,因而在當代的教育和學校環境研究文獻中依然出現,而在其他應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則減少了。總之,1970年后,盡管在美國還有一些社會心理學家、教育研究者繼續使用和嘗試測量這個概念,學者們對此概念的興趣明顯下降。稍有轉機的是,實證社會學家的介入使得這個概念更加明朗了,同時限定、減少了這個理論工具的使用范圍和頻率。在美國,一些從事經驗和實證研究的社會學家把“異化”變得更明晰、更易于測量,他們嘗試尋找可靠而有效的工具測量構成“異化”的那些因素,把這個概念開發成一個在教育研究領域有用、有效的范式。例如,從馬克思、曼海姆、韋伯和涂爾干那里汲取營養,Seeman把異化闡釋為五個方面或變項(alternatives or variants):無力(powerlessness)、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無規范(normlessness)、孤獨(isolation)和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nt)。近來,瑞澤爾糅合了馬克思主義異化觀點和韋伯的理性化牢籠思想,引入其社會的麥當勞化理論,衡量其“麥當勞化”的“效率”、“可計算性”、“可預見性”、“技術控制”、“有限的人際交往”等。在經驗研究層面,Weakliem 和Borch (2006)運用哈里斯民意調查數據(比如,被調查者對“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等的看法),研究長期和短期的異化模式,發現黑人和低收入者在民主黨執政期間比共和黨執政期間更少異化感;長期而言,女性和未受高等教育者的異化感比較強。
異化概念由熱鬧歸于冷寂,部分源于“異化”概念運用和表述中明顯的道德評價意味。異化概念和理論需要面對另外的狀況和可能。就生產勞動而言,勞動異化的狀況固然存在,但假如出現了下列情境會是怎樣?比如工作很有報償,工作能增進情誼和愛,而業余的時間反而壓抑而可怕?就消費而言,異化勞動理論固然揭示了金錢和資本在維系權力差異格局中的重要意義,同時它也提出了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對那些被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工人來說,消費是否提供了動力和滿足?也就是說,消費是否有助于消解、破除勞動異化?當馬克思、恩格斯關切歐洲的工人工作和生活遭受壓抑,托克維爾則看到美國的工人階級由于工業化帶來的普遍富裕,不再把階級差別當作自然秩序。托克維爾擔心的是洶涌而來的消費品會毀壞工人把自身緊靠在共同體中的需求,毀壞他們的創造性。Rapoport & Rapoport恰當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的焦慮是冷漠從工作場所擴散到社區,托克維爾擔心的是冷漠將從家中擴散到工作場所。
二、消費領域的異化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開始的法蘭克福批判學派被稱為消費批判的三大傳統之一。Schor認為,這是當時人文學科中最富有影響力的一股力量。這個學者群體引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商品交換的理論,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分析當時的文化產業和消費文化,認為文化工業成功地對大眾實施了欺騙和操縱,最終使大眾成為“被動接受者”。他們的批判十分尖銳,被視為“無情的敵視”,他們表現出了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不同的是他們把馬克思集中關注的生產勞動領域轉向文化工業、精神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
本雅明所說的藝術作品大量復制的時代,也正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宣稱的文化工業的控制時代。藝術作品和其他大眾消費品“已經完全把自己和需要等同起來,它以欺騙為手段,徹底剝奪了人們擺脫效用原則的可能性。在文化商品中,所謂的使用價值已經為交換價值所取代。消費變成了快樂工業的意識形態,而后者的生產機制卻是它永遠擺脫不掉的”。
作為新派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與馬克思一樣把異化視為消極的、負面的現象。他宣稱馬克思在該領域留下了寶貴遺產,并把這一遺產更明確、更鮮明地引入消費領域,同時表明該遺產業已在消費領域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判斷。在他看來,“在獲取和消費的過程中,錢的異化功能已經由馬克思做出了十分精彩的描述”;“消費的過程與生產的過程一樣被異化了……金錢代表了一種抽象形式的勞動和努力……”。在生產和消費交織的過程中,馬克思筆下的“工人”成了弗洛姆的“消費人”。“消費人”是這樣一種人,他的目標主要不是擁有物,而是越來越多地消費,以此補償其內在的空虛、被動、孤獨和焦慮。在一個以大企業、大工業、政府和官僚為特征的社會,個人對勞動環境是無能為力的,感受到的是虛弱、孤獨、厭倦和焦慮。同時,龐大的消費工業對利潤的需要,通過廣告媒介,將他變成了一個貪婪的人、一臺要越來越多地消費的永動機。“消費人”處于幸福的幻覺之中,而他在潛意識中卻忍受著厭倦和被動。他把刺激和激動誤認為是快樂和幸福,把物質上的舒適當作活力;滿足貪婪成了新的宗教。消費自由成了自由的核心。
不同于弗洛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方面表達了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疑問。人們在他們的商品中識別出自身;在他們的汽車、高保真度音響設備、錯層式房屋、廚房設備中找到自己的靈魂。那種使個人依附于他的社會的根本機制已經變化了,社會控制錨定在它已產生的新需求上。在轉向文化和藝術品等更具有布迪厄所謂“區隔”意義的消費領域時,馬爾庫塞進而發明了一個與馬克思“勞動異化”可資對照的“藝術異化”(artistic alienation)概念。在他看來,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表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勞動的關系。與這一概念相對照,藝術的異化是一種“高水平”或中介了的異化。藝術異化中展現的藝術同時代秩序之間存在的主要裂痕,正在逐漸被發達的技術社會所彌合。隨著彌合的進展,馬爾庫塞所主張的、消弭異化的方略——認為人和萬物得以表現、歌唱和言談的方式,是拒絕、破壞并重建它們實際生存的方式——反倒被拒絕。在這種吊詭的情況下,“異化的作品 …… 成了廣告節目,它們起著銷售、安慰或激勵的作用”。
在這里,一些問題出現了:在勞動異化情景下產生的反抗意識為什么沒在工業社會的消費文化情境下出現?這些消費異化發揮作用的機制如何?微觀的、具體的經驗資料如何呈現出來?有無別樣的經驗事實和機制同時或隨后發生作用?正像早期以生產為核心的分析取向一樣,以消費作為主導、生產僅僅是附屬的論點也是一種錯誤的判斷。這個框架彰顯的精英主義思路,即對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貶斥,也是法蘭克福學派遭致批評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這個框架也沒能解釋為什么在消費市場上總是存在消費者抗爭和反抗的事實,沒能彌合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鴻溝,沒能有效地回答消費者是被動的木偶還是能動的主體或行動者。
三、新的研究范式:消費的主體性
“消費主體(consuming subject)”的論述主要來自消費文化領域對于自我與現代性的討論,即現代性的產生體現為自我的個體化。這里,沉重的、固化的現代性被輕靈的、流動的現代性所取代;消費的經驗和感受中,強迫轉變為上癮,購物可以驅魔,人們不樂意聽從說教而樂意看到展現和表演。事實上,早在二戰以后,把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結合起來、探索消費愉悅的細微之處,已經構成了一種知識工程。一批法國學者尤其突出,他們包括阿爾都塞和巴利巴(Balibar)、波德里亞、德波、利奧塔。如果馬克思試圖理解和揭示生產的政治經濟學,波德里亞則試圖理解和揭示商品作為消費符號和象征政治經濟學。19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文化研究學者對消費者和消費行為的研究,日益集中在有關“品位”、“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的討論上。
坎貝爾把現代消費主義與浪漫倫理視為一體的論斷,似乎與韋伯的禁欲倫理唱對臺戲。按照布迪厄的論述,社會區隔產生于生活方式,即人們的消費行為系統;通過這個系統人們區分并獲取那些更加值得向往的、值得認可的、有價值的消費品。Jackson清晰地展現了購物與身份認同的緊密聯系。在一個進行中的而非業已完成的全球化世界,消費文化呈現出的是多樣化的景觀:在印度呈現出公共文化的特征,在中國表現出消費民族主義,在俄羅斯則是消費的藝術化。在Comaroff看來,消費成為資本主義的最新意志,消費不僅象征著財富、健康和活力,也成為“建構自我與社會、文化與身份認同”的首要場域。Douglas、Miller則堅持認為,消費行為在生活方式的選擇和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具有想象空間,消費者具有反抗和被賦權的可能。消費者作為“能動者(agent)”而不是被動的木偶的一面,得到了突顯。另外,肇始于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接續迷戀者研究、品牌共同體及其他消費活動的研究,展示出多樣化的、積極活躍、有主體性的消費者。
另外,人類學學家和歷史學家對于商品的交流和合作研究表明,價值表現于被交換的商品中,人們著力關注被交換的物品,而不僅僅是交換的形式和功能:商品與人一樣,有著社會生命。物品負載著人際交往和交流的符碼,消費者借助于它與別人交流和交換。食品也罷,飲料也罷,服務也罷,只要與社會生活有關,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借助它們達成社會凝聚、獲取支持和幫助、尋求友善。因而,一種消費的理論必須是關于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理論。
當代學者在使用商品這個概念時,局限于那些人類生產的物品(和服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關或只有在資本主義滲透到的地方才能找到的東西。問題是,資本主義初期有商品化的過程,人類歷史上有著“去商品化”的過程,人這個物種在商品化、貨幣化的過程中同樣有著反向的行動和運動。在當下社會,具體而微的購物的性質存在是狂喜還是折磨的疑問,在更廣大的消費世界,消費政治(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也有著是“表達(expression)”還是“壓迫(oppression)”的問題。不管怎樣,一種新的轉向出現了,即關注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消費理論研究出現了。
四、欲望、主體與當代資本主義的愉悅經濟
資本主義在20世紀后半葉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豐裕的商品及其形式穿透到大眾媒介和大眾生活中,造成了一個景觀社會——德波的核心論題。“景觀是資本累積到這樣一個程度———它變成了圖像” ,“景觀不是圖像的一個集合,而是一個由圖像所規制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 。在這樣一個由極其豐富多彩的商品所構成的景觀社會,人們幻想自己具有主體性的欲望,而欲望的實現和滿足實際上是對真實欲望的消除。其結果是,這種景觀社會將人緊緊地組織進欲望生產—商品消費的“物體系”之中, “真正的消費者就這樣變成了幻想的消費者。 商品就是這種幻覺,這種幻覺是實在的,景觀是幻覺的最普遍形式。”由此,消費就絕不再是基于個體消費者“自主的”判斷,而是某種全盤規劃的社會機制。
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看來,這種全盤規劃的社會機制中,消費欲望、消費主體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愉悅經濟的發動機。德魯茲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一書呈現出了一個由“欲望機器”(desiring machine)編織而成的社會政治之網。他們所謂的“欲望”不是由匱乏所引發的心理渴求,也并非一種精神性的存在,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欲望是由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欲望是和尼采的意志相類似的一種創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顛覆性,應該充分地被施展出來;它是生產性的、創造性的、積極主動的,又是非中心性的、非整體化的。對于德勒茲來說, 主體是一個剩余,它不僅能產生剩余價值,而且能引發消費領域的重大變革。按照他們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異樣的主體,他沒有固定的身份, 游蕩在無器官身體之上,始終處于欲望機器的邊緣,由其用之于生產的部分所界定…… 毫無疑問,任何欲望生產已經緊接著是消費與耗盡, 因此是‘感官欲樂’”。如此,欲望的價值就在于,不經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轉譯和改造,直接投入社會生產與生活之中:“在確定條件下,社會生產純粹是而且只不過是欲望生產本身。我們認為,社會領域就是欲望直接投資的結果,它有史以來就是欲望框定的產品……”
Bohm 和 Batta對耐克商品的拉康式解讀表明,盡管耐克生產商是血汗工廠,人們對這類工廠有長期的抵抗,但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人很高興地花費不菲地購買這類昂貴的消費品。耐克品牌承諾,一旦買了最新款的訓練鞋,就會獲得神奇的愉悅的經歷。人們穿上這種鞋子后并沒有像喬丹跳得那樣高,不過,這似乎不影響人們相信和希望這是真的。正是這種幻想(fantasy)的力量在拉康的商品消費觀念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拉康在第十四期的講座中說道:“在幻想之外, 沒有任何值得渴望的東西, 沒有任何崇高現象:在幻象之外, 我們只發現了驅力, 只發現了驅力在征候的四周悸動”。受到快感原則調節的能指法則在型塑著主體的欲望的同時也在生產著主體的欲望, 它使得主體更為急切地奔向所欲望的那個“物”, 主體總想超越快感原則, 追求更新起點欲望滿足, 如拉康所說, “快感原則的功能就是使人一直去尋求他不得不再次發現、但卻不可能獲得的東西”。對拉康而言,資本主義終究是為了俘獲愉悅(jouissance),或任何可得的剩余愉悅(surplus jouissance),以便自身運轉下去。“在歷史上的某時點,當剩余愉悅變得可以被計量、被統計、被加總,這時就發生了有意義的變化。用大師的話語講,正是在這里所謂的資本積累開始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在消費社會背景下就轉化為“剩余愉悅”。“這種剩余價值是剩余愉悅的紀念碑,剩余愉悅從而等同于剩余價值。‘消費者社會’的意義源于構成其自身的‘要素’:人類就等同于我們的工業所產生的剩余愉悅”。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愉悅的體系(a system of enjoyment)。
人們之所以醉心于這些大品牌,是因為現代的主體為了構建自身就會不斷地消費更多的東西,這個進程的核心就是愉悅,而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愉悅的系統。耐克的案例表明,消費者可能主動地、愉快地醉心于這些大牌商品,這是他們社會生活的真實部分。晚期資本主義體現為,對于消費欲望和主體的張揚,對于愉悅經歷在社會生活中重要作用的開發和提升。
結語與討論:邁向更多經驗事實的消費主體性研究
從生產領域的勞動異化,到日常生活領域中的消費異化,馬克思本人及其跟隨者,對異化等概念工具曾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但他們的理解、使用、闡釋存在著差別和距離。正如以上所論及的,這些概念工具的意義并不總是那么明確清楚,有時存在含混之處,甚至被馬克思本人和后來的研究者所拋棄。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使得這些原本主要在哲學、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概念更具可測量、可觀察性,這種概念工具的操作化、明晰化的努力代表了消費研究的一種方向,盡管在這個方向上努力工作的學者遠遠沒有這些概念風行時的學者那么規模大、那么影響深遠。在諸多問題和挑戰面前,這些概念工具迄今仍然是人們從事現實批判與省察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在Kopytoff的筆下,馬克思的商品化是檢視高度金錢化、貨幣化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想類型。Renfrew看到,如同馬克思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這些概念適合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主義分析(formalist analysis)。在此意義上,這些概念工具是對現代社會達成科學分析的理論工具,在新的情景下可以得到延展和變換。在更可觀察的消費領域,Don Slater在消費文化研究中重新求助于基本問題和現代性概念,Miller重新嘗試把黑格爾的客體化理論(Hegelian theory of objectification)應用于他命名的“物質文化”,Lee重新把商品形式作為當代文化政治的關鍵。這些都是近期研究者從不同層面嘗試重新把馬克思主義融匯、綜合進消費者社會理論的努力。
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是粗線條的、邏輯的、示意圖式的。社會變遷業已并即將提出許多有待更深入研究的問題:從社會學史的角度看,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工作場所的異化狀況究竟怎樣?關于19世紀歐洲乃至世界工人生產和生活的狀況,有哪些民族志的、統計數據的、實地觀察的資料可以旁證或佐證馬克思的異化觀點?對消費的論述是否應更多強調社會的、文化的因素?20世紀及其后的相關資料如何?在那些后期工業化的國家,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異化現象?把市場交換與互惠和交誼截然割裂開來,如同把禮物交換看作是前工業社會共同體的浪漫想象一樣,是否同樣過于簡單?是否遺忘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按照文化設計運轉?“消費異化”開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大話題,這個話題直到消費主體性的范式出現之后,依然充滿爭論,需要更多經驗事實資料來檢視這些命題和觀點的恰切性與合理性。
① [美]丹尼爾· 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129頁。
② George Ritzer,TheGlobalizationofNothing, Thousand Oaks, CA:Pine Forge Press, 2004, p.3.
③葉啟政:《啟蒙人文精神的歷史命運:從生產到消費》,載應星等編《中國社會學》(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頁。
④ Iain Williamson and Cedric Cullingford,“The Use and Misuse of ‘Alie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BritishJournalofEducationalStudies, vol. 45, no. 3 (September 1997), p. 263.
⑤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頁。
⑥ B.Seligman, “On Work, Alienation and Leisure,”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 vol. 24,no. 4 (1965), p. 349.
⑦David Weakliem and Casey Borch, “Alie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form or Group-specific Change?”,SociologicalForum,vol. 21, no. 3 (2006), p. 415.
⑧ Eric Josephson and Mary Josephson, eds.,ManAlong,AlienationinModernSociety, New York: Dell, 1962.
⑨ T. C. Denise,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Some Critical Notices,” in F. Johnson, ed.,Alienation:Concept,Term&Meaning,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⑩ F. Johnson, ed.,Alienation:Concept,Term&Meaning,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