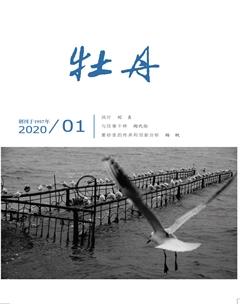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傳統繪畫中的人文精神
中國繪畫立足于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畫者在自然中感受自然,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中國繪畫具有濃厚的人文精神,有別于以理性科學為主導的西方繪畫。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之風的興盛促使中國畫的發展無論是技法還是理論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人文精神得到充足的體現。本文分別從繪畫理論、“寫意”的表現手法、筆墨的變化三個方面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傳統繪畫的人文精神,以期提高人們對中國傳統繪畫的認知程度,加深對人文精神的內涵理解,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中國有著傳統小農社會的歷史背景,人民崇尚中庸之道、滲透著人文精神,注重情感表達。中國傳統書畫講究天人合一,人在自然中感悟自然,表達思想、情感、意趣和志向。中國傳統繪畫作品中滲透了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的思想以及人文精神,對當今繪畫研究發展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發展的重要時期,士大夫們從傳統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高山流水、蘭亭集會、闊談老莊、蔑視禮法,形成了獨特的魏晉風尚,這一時期藝術發展尤其是美術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們的言行談吐、風格氣度、詩賦畫論等都是中國畫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后世的繪畫風格及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畫論中的人文精神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政局的動蕩和戰亂的影響,傳統的思想禁錮被打破,人們對個體的自由和人格尊嚴的追求,促使了魏晉玄學的誕生。在魏晉玄學的影響下,士大夫們崇尚自然、率真灑脫、超然物外、風流自賞的魏晉風度促使這個時期文藝美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各種書論、畫論等新的思想觀點的出現使得藝術領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中國古代美學“天”“人”“自然”“藝術”的范疇是共同發展、相輔相成的。中國繪畫無論表現對象是自然還是社會,終歸落足于人的生活,是生活美的反映,魏晉南北朝的畫論借助人物品藻的概念闡述美的本質。顧愷之借人物品藻提出“傳神寫照”“遷想妙得”的美學范疇,注重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內在深度,并在《洛神賦》中進行了繪畫實踐。王微在《敘畫》中也將此觀點延續到山水畫的創作實踐中去。謝赫《古畫品錄》中將“氣韻生動”置于首位,不僅發展了論顧愷之“傳神論”,更將此前散亂、模糊的思想系統化、明確化,這是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竹林名士嵇康“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將人物品藻引向神、骨、肉多層次的引導,以及對神情和氣質的把握,由此確定了中國畫“傳神”的定性位置,并成為整個中國畫的品評標準。后世理論即使經過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發展,也都圍繞著繪畫表現人物精神之美的范疇。
中國畫論透露出對人生命的重視、追求和美學上“人的覺醒”,人文精神的表現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連,與西方科學理性的精神相比,更加連綿不絕、富有生命力,不會輕易斷層與變異。
二、“以形寫神”的人文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傳統繪畫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從“形似”走向“神似”。東晉顧愷之率先提出了“傳神寫照”“遷想妙得”的繪畫理論,南齊謝赫的“六法”又將“氣韻生動”放在首位,宗炳的又提出“言外之象”等。要想達到“神似”的傳神效果就要靈活地進行“形似”的描繪。謝赫論衛協時曾說到:“雖不該備形妙,頗得壯氣。”蘇軾說“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體現出“神似”不僅是中國畫家的審美標準,更是最高的審美追求。
“神”就是“精神”“神態”,也可以理解為哲學當中的“神韻”,它并不是純粹抽象的概念,而是畫家對自然、社會、人情、時代等深刻的觀察體驗之后,加上自身的文化底蘊、氣質精神,上升到精神層面的韻味風采。元代畫家倪瓚曾說:“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近代學者陳師曾認為所謂的“逸氣”,就是一種超世界超社會的思想,脫離物質的束縛,發揮自由的情致。由此可見,“逸氣”可以看作是“神韻”的一個方面。如謝赫在評價陸探微時說:“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可見陸探微的繪畫不僅技藝精湛,還突破了對外形單純描摹的限制,同時準確把握了事物內在的精神氣質,說明了畫家對“神韻”獨到的理解,此處“以形寫神”的人文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綜上所述,“以形寫神”不單單是一種繪畫技法的要求,還是在對所描繪的客觀物體形象了然于心的基礎上充分的主觀情感抒發,融合自身文化修養氣質,展現出獨特的精神韻味,其既是一種表現手段,又是一種審美追求。
具體而言,“以形寫神”源于中國傳統儒家、道家的融合,畫家超然物外,使繪畫在風貌上具有一種玄遠幽深的哲學氣質。“以形寫神”在具體表現上,講究虛實變化,如陸探微“筆跡周密”的密體,又如張僧繇“筆才一二,象已生焉”的疏體,其線條變化婉轉安逸,與道家主張“虛靜”的思想如出一轍。顧愷之《女史箴圖》講述勸誡宮中婦女的道德規范,通過對貴族生活的描寫展現人物的風采,這體現儒家所倡導的“入世”思想,對人民“仁、義、禮、智、信”道德倫理觀的呈現,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描繪。“暢神悟道”的道家思想和“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融會其中,使得畫家擺脫了時間、空間的限制,超脫了對客觀物象表面的描繪,但又落足于社會現實,以獲得更大的藝術自由,加之畫家自身的文化底蘊、學識修養,個性表現等,畫家最大限度地發揮想象力,形成自己的創作意識,創造出富有精神價值的藝術作品。從這點可以看出,相較于西方的現實主義繪畫,中國的傳統繪畫更能體現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
三、筆墨變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國傳統繪畫由于工具的特殊性,不同于西方繪畫立體寫實的形態特征,所呈現出來的畫面更具有抒寫性和表現性。
對于中國畫所追求的“寫意”“神似”來說,筆墨無疑是最好的表現手段。不同的材料制作出來的筆有不同的特性,狼毫剛健、羊毫細軟、雞距有彈性,再加上不同的用筆方式,或鉤、或挑、或皴、或染,勾勒出輕重緩急、剛柔并濟、錯落有致、粗細不一的各種線條。畫家通過不同線條的性質,模擬不同物體的質感,山的俊挺、水的柔和、石的堅硬等,都可以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如此,墨法干、濕、重、淡、清的結合運用可以進一步加強對表現對象的生動刻畫。
筆墨除了單純的技法運用,更重要的是對畫家思想感情的表達。正如“骨法用筆”,說明線條不單單只是描摹對象的輪廓,它本身就具有一種抽象的形式美。畫家利用線條的力度、節奏、氣勢、韻律等,不僅可以表現出雄偉的氣勢、靈動的節奏感、無盡幽深的神韻,而且可以表達出作者自己的意趣志向、創作心境。閑適時運筆輕緩、鉤皴兼備;激昂時潑墨揮毫、氣吞山河;靈感突降時,寥寥數筆,躍然于紙;心中憂苦時,明月相伴,揮灑無盡愁思。此時筆墨就是畫家的心緒,相比于素描油畫而言,筆墨的運用更為方便快捷,頃刻間的便可揮灑而出,作品更具有感染力。
除此之外,中國畫也有著細致而層次分明的描繪。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用筆古樸細勁、深沉凝重,先用細線勾勒輪廓,在逐步渲染著色,既沒有皴法,也沒有點苔,其采用凹凸法,更加真實地展現出山石明暗的立體感。《洛神賦圖》的線描工細勻整,幾乎沒有粗細輕重緩急的變化,而是利用不同彎曲程度的線條表現物體的質感和動態,衣紋褶皺合乎人體形態,靈動又不失沉穩,現實性寓于造型手法中。時人評“筆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后世稱之為“高古游絲描”。由此可見,筆墨看似是繪畫技法,實際上是畫家思想觀念、生活閱歷、個性彰顯、文化底蘊的綜合體現。中國傳統的筆墨繪畫技法是人文精神表現的重要工具和載體。
(寶雞文理學院)
作者簡介:李媛琪(1996-),女,河南洛陽人,碩士,研究方向:學科教學(美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