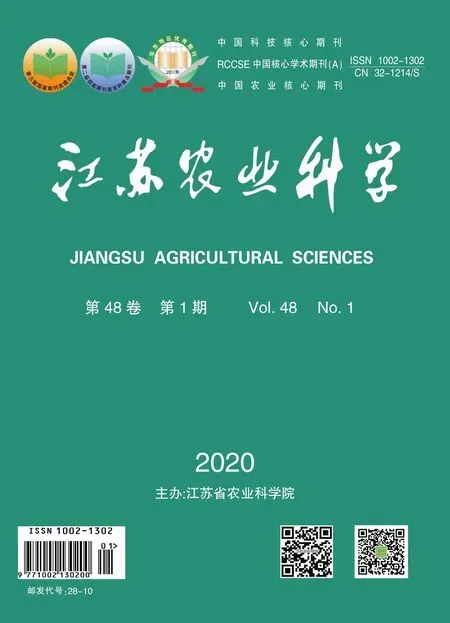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測度及路徑優化
楊 佳, 周麗君, 李秋雨
(白城師范學院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吉林白城 137000)
“十三五”期間,我國將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全國25個省(區、市)2.26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230萬貧困戶、747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目前,國內學者在鄉村旅游扶貧領域的研究,多集中在旅游扶貧的含義、旅游扶貧模式、旅游扶貧策略等方面,宏觀層面研究較多,中觀層面研究較為模糊,微觀層面研究不夠成熟,國外旅游扶貧研究重點已經逐漸延伸至對旅游益貧效應的探析[1]。在旅游扶貧效應方面,目前國內外學者認為,鄉村旅游扶貧效應包括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2個部分。積極效應主要表現在提升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帶動貧困村的經濟發展、促進區域人口素質提高和社會進步等,消極效應主要包括破壞村莊生存環境、對貧困村的過度文化入侵、主客矛盾逐漸激化等方面,對鄉村旅游扶貧效率的測度也應從單一的經濟效益轉向涵蓋經濟、生態、文化等多元化綜合效益體系。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吉林省是農業大省,生態環境良好,鄉村旅游資源富集,鄉愁文化厚重,適合發展鄉村旅游。2018年末,吉林省全省總人口為2 704.06萬人,農村人口為1 148.41萬人,占總人口的42.47%。在吉林省《關于印發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工程實施方案的通知》中,確定了將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吉林省48個縣(市、區)359個建檔立卡貧困村、2.8萬貧困戶、5.1萬貧困人口脫貧。近年來,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廳等各部門非常重視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工作,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積極推動鄉村旅游扶貧的發展,確保到2020年末,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面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1.2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以下簡稱延邊州)等9個市(州)作為決策單元,共涉及48個縣、5.1萬貧困人口。通過對吉林省2014—2018年近5年鄉村旅游扶貧效率進行測度,并探討其變化原因,旨在為吉林省及其他貧困地區鄉村旅游發展提供參考。
目前,對旅游扶貧效率的測度最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仍是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DEA模型是一種綜合指標的評價方法,使用該模型可用于多項投入與產出的效率評估,且權重不受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2]。然而,傳統的DEA模型只是對決策單元(DMU)的相對效率進行評估,而非絕對效率評估。由于旅游產業帶動作用強、關聯度廣,受環境因素和隨機變量影響很大[3]。因此,本研究選用三階段DEA模型,剔除環境因素與隨機因素的干擾,可以更準確地評估DMU的效率[4]。
目前,對地區鄉村旅游扶貧的效率測度主要集中在對地區旅游扶貧的現狀和發展態勢做出評估,全面測度地區旅游扶貧水平和潛力并可進行縱橫向分析比較的綜合性研究還相對缺乏[5]。因此,在數據選取方面,考慮到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測度數據選取的科學性及可行性,總結相關研究旅游扶貧效率論文的指標選取體系,在此基礎上,選取鄉村旅游人均收入和鄉村旅游人均接待量作為投入指標[6]。在產出指標上,考慮到鄉村旅游扶貧主要針對鄉村居民,因此,選取能夠反映農村居民經濟收入及生活狀態改善程度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產出指標。本研究DMU數量為9,投入產出指標數為3,符合DEA模型中對DMU數量與投入產出指標數量之比的要求。同時,選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環境變量[7]。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吉林省統計年鑒(2014—2018)》《吉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2018年)》,2014—2018年吉林省旅游產業發展報告、2014—2018年各市(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等。
1.3 研究方法
1.3.1 第1階段:傳統DEA模型分析初始效率 1978年由著名的運籌學家Charnes等首先提出了一個被稱為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模型)的方法,用于評價相同部門間的相對有效性[8]。本研究選用可變規模報酬模型(BCC模型),對于任一決策單元,投入導向下對偶形式的BCC模型可表示為
式中:θ(0<θ≤1)為綜合效率指數;λj(λj≥0) 為權重變量;ε為常量,表示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S+(S+≥0) 為松弛變量;S-(S-≥0) 為剩余變量;êT=(1,1,…,1)∈Em和eT=(1,1,…,1)∈Ek分別為m維和k維單位向量空間;j=1,2,…,n,表示決策單元;X、Y分別是投入、產出向量。DEA模型本質上是一個線性規劃問題。
若θ=1,S+=S-=0,則決策單元DEA有效;
若θ=1,S+≠0,或S-≠0,則決策單元弱DEA有效;
若θ<1,則決策單元非DEA有效。
1.3.2 第2階段:相似隨機前沿模型(SFA)模型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變量 Fried等認為,決策單元的績效受到管理無效率(managerial inefficiencies)、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effects)和統計噪聲(statistical noise)等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分離這3種影響[9]。構造SFA回歸函數(以投入導向為例)如下:
Sni=f(Zi;βn)+vni+μni;i=1,2,…,I;n=1,2,…,N。

SFA回歸的目的是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因素對效率測度的影響,以便將所有決策單元調整于相同的外部環境中[10]。調整公式如下:

1.3.3 第3階段:原始數據的調整和效率測度 運用調整后的投入產出變量再次測算各決策單元的效率,此時的效率已經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因素的影響,是相對真實準確的[11]。此時,再次運用BCC模型對吉林省旅游扶貧效率進行評價時,可以更加準確地反映各DMU的效率[12]。
2 結果與分析
2.1 第1階段實證分析
運用DEAP 2.1軟件對吉林省9個市(州)2014—2018年5年的鄉村旅游扶貧效率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見表1。
通過第1階段的DEA模型的初始效率分析,計算吉林省2014—2018年鄉村旅游扶貧的綜合效率值、純技術效率值和規模效率值。
2.1.1 旅游綜合效率測度結果分析 (1)從總體上看,2014—2018年,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綜合效率值從0.793上升到0.835,全省旅游扶貧綜合效率平均值為0.809,說明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的綜合效率處于較優水平,且大部分城市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2)從片區分布上看,吉林省中部片區旅游綜合扶貧效率最高,平均綜合效率值為0.874,遠高于全省旅游綜合效率平均值。吉林省中部地區經濟發達,與國家政策銜接緊密,高A級景區景點較多,旅游脫貧效果顯著。吉林省東部片區旅游資源豐富,旅游稟賦優良,旅游發展潛力巨大,但經濟基礎相對較薄弱,因此其綜合效率均值相對次之;吉林省西部片區旅游綜合扶貧效率較低,遠低于平均水平。(3)在2014—2018年間,吉林市鄉村旅游綜合扶貧效率值均為1,說明近5年來吉林市的旅游綜合效率處于相對有效狀態,綜合效率明顯優于其他市(州)。吉林市的小綏河村、韓屯村、馬鞍嶺村等,在吉林省各主要廳局的包保政策下,積極推進鄉村旅游脫貧工作,通過旅游收入帶動當地農民快速脫貧,在吉林省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1.2 旅游技術效率測度結果分析 技術效率是指通過科學技術手段的進步而獲得的生產效率的提升[13]。2014—2018年旅游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853,但平均值總體上呈下降趨勢。說明在鄉村旅游扶貧方面,對旅游資源的創新開發、有效利用及扶貧模式的創新發展等方面較為不足,大部分鄉村在進行旅游扶貧過程中扶貧模式千篇一律,依托現有的旅游資源或區域旅游資源進行粗放式開發,強調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忽略了村莊的文化底蘊和文脈,缺少精準式扶貧的措施和路徑[14]。
2.1.3 旅游規模效率測度結果分析 根據DEA模型,規模效率是指在既定的管理和技術條件下,尋求現有投入量與最優生產之間的關系,規模效率值等于1時,表示已經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15]。2014—2018年,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的規模效率均值為0.899,且從2015年后基本處于穩定上升階段,且大部分地區的規模報酬均處于遞增狀態,說明資源要素配置及規模投入的增加對于提升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是有效的[16]。
2.2 第2階段實證分析
由于第1階段的DEA模型會受到環境因素與隨機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第2階段采用SFA模型對投入變量進行調整,通過構建SFA模型,剔除外部環境和隨機誤差的影響,同時,重新調整第3階段的投入變量[17]。判斷環境因素對投入松弛變量影響的標準:如回歸系數大于0,即表明環境變量的增加會導致投入變量的浪費,如回歸系數小于0,即表明增加環境變量有利于減少投入松弛量[18]。通過測算分析,結果表明,環境變量對鄉村人均旅游接待量和鄉村人均旅游收入2個投入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說明人均GDP越大,鄉村人均旅游接待量和鄉村人均旅游收入投入冗余也越大,旅游效率越低(表2、表3)。

表1 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初始效率測度結果(調整前)
注:DMU為決策單元。Crste為綜合效率值,Vrste為純技術效率值,Scale為規模效率值。drs表示規模報酬遞減,irs表示規模報酬遞增,—表示規模報酬不變。表4同。

表2 鄉村人均旅游接待量第2階段SFA參數估計結果

表3 鄉村人均旅游收入第2階段SFA參數估計結果
注:表中*表示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因部分值較大,因此采取科學計數法。
2.3 第3階段實證分析
將第2階段SFA回歸分析調整后的投入變量重新帶入BCC模型進行分析得到調整后的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測度情況。由表4可以看出,剔除隨機干擾項后,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呈現了一定層面上的波動,外部環境變量的引入,使得吉林省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呈上升趨勢,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呈下降趨勢,反映了這一階段環境變量的引入對鄉村旅游扶貧的發展仍有較大的影響[19]。結合調整前后的效率空間分布(圖1、圖2)可知,鄉村旅游綜合效率均值由0.809上升至0.840,剔除環境變量后,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綜合效率上升,外部環境的改善對綜合效率的發展具有較大的提升作用;調整后的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純技術效率均值由0.853下降至0.847,變化不大,說明在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的發展過程中,對技術的利用水平、居民的參與體驗程度、鄉村扶貧的管理水平等方面總體提升不足,新技術與新方法應用不足,使鄉村旅游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鄉村旅游規模效率均值由0.899下降至0.846,說明對于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來說,由于交通通達性等制約條件,大型企業、投資集團等對貧困地區的設施、土地、配套等投入相對不足,未達到較高的規模效益;從空間分布上看,吉林省旅游鄉村旅游扶貧空間分布不均勻,中部地區明顯高于東部和西部地區。調整前旅游綜合效率值總體上呈中高西中東低的時空分布規律,長春市、吉林市等中部地區的旅游綜合效率較高,延邊州、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等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旅游綜合效率較低。調整后長春市、吉林市地區的旅游綜合效率較高,但四平市、通化市的綜合效率明顯下降,說明該地區受環境影響變量較大。
3 路徑優化對策
3.1 創新鄉村旅游扶貧模式,提高旅游扶貧技術水平
通過分析可知,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創新將成為提高鄉村旅游扶貧效率的主要路徑之一。在原有依托旅游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貧困村的文化內涵,通過“旅游+”模式,借用互聯網等科技元素,在網絡自媒體、公眾平臺、微信、微博等線上平臺進行宣傳,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地幫助貧困地區進行營銷與宣傳,突出優勢特色,提升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收入,進而帶動貧困村全面脫貧。
3.2 優化產業結構,形成區域發展優勢
通過分析可知,經濟較發達地區的鄉村旅游扶貧綜合效率相對較高,說明經濟因素對鄉村旅游扶貧綜合效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20]。對于貧困地區來說,首先要依托自身的優勢資源和特色,優化產業結構,提升旅游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要進一步促進鄉村產品向旅游產品的轉化,依托產業的技術化和深層次發展,提高鄉村旅游產品附加值的提高,促進旅游消費,提升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3.3 生態環境優先,促進可持續發展
貧困地區通常都擁有良好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在大規模的旅游開發中,極易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21]。因此,在進行旅游資源開發的過程中,首先要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第一要務,對貧困地區進行科學合理地規劃,實施分期開發策略,在旅游開發的過程中嚴禁破壞當地及區域的生態環境,同時充分考慮地區的特色,使貧困村與周邊區域協同發展。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環境保護監督機制,鼓勵企業、社會組織、當地居民等參與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監督工作,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維持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表4 吉林省鄉村旅游扶貧初始效率測度結果(調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