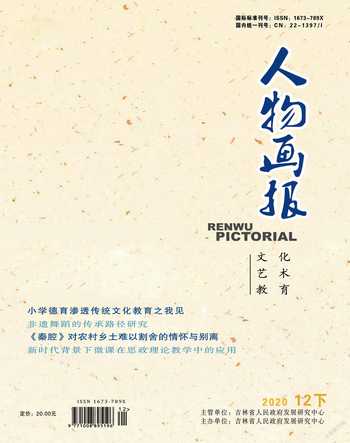《陶行知教育名篇》讀后感
翟燕飛
陶行知先生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誠誠懇懇的教育家。他堅持生活教育,堅持讓自己做“整個的校長”,堅持必須讓學生擁有科學、創造的精神……他的堅持成就了我們自己的教育。
他指出,中國的教育太重書本,和生活沒有聯系。教育不通過生活是沒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而教育。
時光悠悠,多少年過去了,我們的教育仿佛離生活更遠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已經漸漸變成了老一輩的談資,那些個有意思的生活場面也都變成了孩子們眼前一個個遙不可及的夢幻。孩子們“五谷不分”早已經是一種常態,我看,漸漸的,他們連牛羊馬也不認識了……
語文課例,不管是寓言故事,還是成語故事,很多都以小動物為喻,孩子們遇見動物,多也是動物園,動物園的動物也是動物嗎?這三十年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動物也是活生生、有特點的——公雞能振翅飛上十米高的大樹;白鵝也是欺軟怕硬的主兒;豬也喜歡橫沖直撞;山羊從房頂跳上跳下絲毫不成問題……動物園的動物,頂多是一副相應動物的模擬畫像,或者是3D打印成果展示而已。
小學一年級的課文《雪地里的小畫家》經久不衰,我們小的時候,親眼見過小雞的足跡,知道小鴨、小馬、小狗的腳印,甚至小豬、老鼠的腳印,所以讀這篇文章自己都會覺得十分有趣而笑出聲來……如今,城里的孩子,怎么了解小動物們的腳印?難道用吃的雞爪,或者是鴨掌、豬蹄?
幸虧這篇文章實在是膾炙人口,課堂還可以進行下去,不至于無聊,但是,這樣的教育是不是也因此變了味道?
生活教育,我覺得仍然是必須的。為生活而教育,我們的中國夢是不是也不遠了呢?
關于“整個的校長”,是在不能再認同。學而憂則仕,仿佛真的是我們的傳統。教而優則仕,難道我們的好老師都更適合當官嗎?為什么不留一些我們的專業性的人才?
陶行知先生說:“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的大些,他關系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的人去擔負嗎?……試問,世界上有幾個第一流的學校是命分式(陶先生認為跨黨的黨人,多妻的丈夫諸如此類“心掛兩頭”的人是命分式的人,不是整個的人。)的校長創造出來的?國家把整個的學校交給你,要你用整個的心去做個整個的校長。
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如果我們都能用一顆整個的心去做一件志向所在的事,那樣整個世界都將繽紛爛漫,春和景明,驚喜無限。
關于學生的精神,陶公說:“那么先生究竟應該怎樣子才好?我以為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教學生學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學聯絡起來:一方面要先生負指導的責任,一方面要學生負學習的責任。對于一個問題,不是要先生拿現成的學習方法來傳授學生,乃是要把這個解決方法如何找來的手續程序,安排停當,指導他,使他以最短的時間,經過想類的經驗,發生想類的理想,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經驗理想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得了這種經驗理想,然后學生才能探知識的本源,求知識的歸宿,對于世間一切真理,不難取之無盡,用之無窮了。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自得”,也就是現今教育家所說的“自動”……”
“我們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進步,就需膽量放大,將實驗精神,向那未發明的新理貫射過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礙,不怕失敗,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奧妙新理,一個個的發現出來。
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即是創造精神;大丈夫不能舍身實驗室,亦當埋骨邊疆塵,豈當隨便過去!”
老師能擁有科學、創造的精神,帶出來的學生還會差嗎?
陶公的教學法或許并不是“善之善者也”。“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才是陶公精神的本源。得益于李紅敏名師工作室,我由很久以前的慕名,終于轉而讀有所獲。
我只愿以陶公精神為食糧,做一位真真正正、誠誠懇懇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