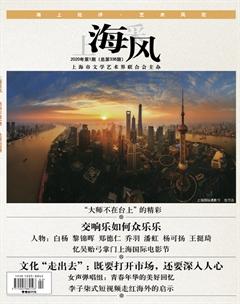憶吳貽弓掌門上海國際電影節
許朋樂


吳貽弓導演的離去給我們留下了難抑的悲痛和不盡的思念。在回溯他的人生之旅,追憶他的創作生涯時,常有人會為他當年的棄藝從政而惋惜,感嘆他沒能多留幾部類似《巴山夜雨》《城南舊事》這樣的傳世佳作。
是的,作為一個懷揣理想、才華橫溢又具有詩人品質的電影導演,在技藝臻萃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后,一定能沿襲自己的風格,創作出彰顯電影品質、極富藝術韻味的精品力作,吳貽弓,這位喊出“電影萬歲”的導演,有著做不完的電影夢。然而,命運改變了他,他不能盡興竭情地站在攝影機旁揮灑自己的才華和情思。不過作為上海電影界的領導,他不能在自己的藝術領地自由馳騁,但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他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才干,都毫無保留地衍化成組織和推動上海電影事業發展繁榮的歷史進程中一刻不停的追夢行動。對他來說,初心依舊,忍痛舍棄的只是個人的事業,重新擔起的是時代的需要、領導的囑托和同行的信任。他從一部影片的導演到上海電影事業的總導演,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成功之作。他大膽地將電影局和上影廠合并成立上海電影總公司,用企業化基地化的手段管理和運作上海電影,雖然走了一陣又折返原地,但他對電影產業化所進行的嘗試和探索為后來者提供了借鑒;他倡導和支持上海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創立了全國第一家國有性質的股份制電影企業——上海永樂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他探索廠校聯手辦學育才的途徑,分別在上海交大和上戲為上影定向培養制片和導演人才;他集聚上海電影界的有限財力,建造了全國第一家多廳豪華影城——上海影城和融合諸多電影元素的上海銀星假日酒店(現為五星級的銀星皇冠假日酒店);他開歷史之先河,領銜創辦了中國第一個A類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他的這些作品,或成為電影史上的重要篇章,或被稱為上海的文化地標和城市名片,其中最亮麗最有影響的當屬已經走過26個年頭的上海國際電影節。
壹
上海是中國電影之源,是新中國電影的重鎮,在上海舉辦國際電影節是張駿祥、張瑞芳、謝晉、于本正、張建亞等幾代電影人期待已久的夙愿,是吳貽弓將它變成了現實。而他所以能將夢想變成現實,完全得力于他是上海市電影局局長,是上海電影事業的掌門人、總導演。無法假設,如果當年不是吳貽弓當局長,上海國際電影節會這么如期而至嗎?會這么成功嗎?
平心說,現在回頭看,1993年創辦國際電影節不啻是一次帶有風險的嘗試。那時,電影行業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沒有徹底改變,壟斷的制片和封閉的市場,掣肘著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在低水平上掙扎,自身的實力和能力都不足以支撐一個完全開放的國際性的電影節。加上影視沒有合流,電影廠、電視臺各自為政,電影缺少媒介渠道和傳播手段,僅靠《上影畫報》《電影故事》兩本雜志又怎能擴大影響、形成熱點?更何況,國門還沒完全打開,許多人的思維、觀念還停留在“閉關鎖國”的地步,總認為在自己家里辦電影節,不能買了爆竹給別人放,言下之意必須確保中國影片得獎——對這些,吳貽弓不會不清楚,他明白電影的色彩,也熟稔“外事無小事”的警示。但是他沒有退卻。他清秀的外表里藏著堅強,他淡定的性格涌動著執著,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抑或從1984年憑借《城南舊事》奪得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鷹獎那一刻起,在上海舉辦國際電影節的念想就隱隱地根植于他心頭。
當了電影局局長和上影廠廠長后,他深知,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辦成一兩件正兒八經的大事情,有違于民心,有悖于責任。慶幸的是,那時擔任上海電影界領導的,幾乎清一色是在攝制組摸爬滾打過的電影人,這班人都有創辦電影節的情結,都愿意跟著吳貽弓在自己的任上完成這一使命。于是在上海電影工作的規劃中,舉辦上海國際電影節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先修渠再引水,先打基礎再壘屋,成了大家的共識。首先要做的是集中人力財力,從基礎設施建設起步。從1990年開工到1992年落成,毗鄰的兩處建筑,上海首家多廳影城——上海影城和擁有488間客房的豪華型的銀星皇冠假日酒店,相繼亮相于富有文化底蘊的新華路和法華鎮路之間。電影節的主會場落實了,賓客的住宿問題也解決了,渠道修成,接下來就得引水了。
貳
1992年的下半年,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籌備工作拉開了序幕,一群從電影局、電影廠抽調而來的工作人員聚集在影城幾間不大的辦公室,拉馬抬槍,開始與國際接軌了。我被老吳委以新聞委員會主任的重任。不過受命以后,我感激他的信任,卻沒有半點榮耀。我和絕大部分人一樣,剎那的興奮過后,更多的是忐忑和困惑。在這之前我們都沒有參加過國際電影節,找不到感覺,更沒有可參照的經驗,從未入過門,何處能下手?細想想,心里發怵。上千萬的辦節費誰給?超百部的參賽參展片怎么來?國際評委從哪里請?交易市場何處設?電影節究竟如何具體運作?新聞宣傳用哪些手段和形式?……這一系列問號都得老吳給我們答案。
吳貽弓一向以儒雅淡定的行事風格而為我們稱道。他不急不躁,即便內心風起云涌,可是表情卻波瀾不驚。不過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只要雙眉緊蹙,就說明這事棘手。記得,第一次開動員會,他沒有高談闊論,沒有細說重要性、緊迫性,更沒有說大話和狠話,但他的雙眉沒有舒展過。他何嘗不知道這是塊難啃的骨頭,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再難這箭也得發,而且得射中靶心。開完動員會,我們按部就班開始行動。老吳找每一個部門的領導交談,布置任務,交代規則,指明注意事項。他不是那種耳提面命的強勢領導,也不會事無巨細眉毛胡子一把抓、事必躬親大包大攬。他的最大特點,就是用人不疑,大膽放手,大家商定的事誰負責誰拍板。他對新聞委員會工作提出哪些是常規必做的,哪些是自選可做的,要求我們:頭緒多,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也不能抓了西瓜不要芝麻;事情多,不要怕事,不要多事,不要出事;記者多,要善待要厚待,盡力為他們提供方便。正是在他的指教點撥下,我們投入了籌備工作,邊學邊干,邊干邊學,老吳則坐鎮指揮,遇到疑難雜癥,他把脈開藥,藥到病除。
舉辦國際電影節,就得有國際范兒,就得按照國際制片人協會的章程和要求處理所有的枝枝節節。譬如,參賽片和參展片數量和出品日期都有嚴格規定,國際評委的組成、包括人數和國度也有具體要求,獎項的設置和評獎有完整嚴密的程序和方式,至于影片交易市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老吳的主要責任就是按照國際慣例掌控調節各部門的工作,并在這一過程中體現出他的價值和能量。
能否邀請到具有國際聲譽的電影藝術家擔任評委,是關系到電影節成敗毀譽的重要一環。那么我們靠什么能邀請到這些藝術家呢?平心說,我們能亮出的底牌和名片除了開放的上海以外,就是謝晉、吳貽弓這幾位在國際上有影響有人脈的中國電影的代表人物。靠著他們,美國的奧利佛斯通來了,日本的大島渚來了,俄羅斯的卡倫沙赫納福來了,中國香港的徐克來了——一個實力雄厚的國際評委會一下子將上海國際電影節提升到很高的檔次。盡管最初確定的九位評委,在電影會刊上公布于眾以后,最終只來了七位,給我們帶來些許尷尬,但絲毫沒造成一丁點負面影響。
同樣,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67部影片,形成了電影節的規模。近三十萬觀眾的熱情觀摩、二百多名記者的積極參與,也造就了電影節轟轟烈烈的聲勢。
更難能可貴的是,遵循國際制片人協會的規定,吳貽弓和組委會要求上海國際電影節必須設立影片交易市場。這應該是個難題,一是片源,雖然就在這一年國產影片的發行權已由中影公司移交各制片廠,但是各廠對市場基本是兩眼一抹黑,沒有交易渠道和交易對象,也缺少合格的發行中介,至于國產片能否走出國門那更是一無所知。二是場地,雖沒有很具體的設定,但形式上必須按照國際慣例設計。空間大了,沒有那么多客商,空間小了,太逼仄,又難形成市場的味道。權衡再三,決定在影城四樓設立了國際影片交易市場。雖然空間狹小,但螺螄殼里做道場,中規中矩、像模像樣,不僅包括港臺在內的中國十多家電影制片廠都設立了展臺,而且有許多海外電影機構也置身其中。進入市場須有特別的通行證,門口有武警戰士站崗,那架勢還是挺唬人的。因為是第一次,新鮮感和好奇心頗具吸引力,每天進進出出的人還不少,接洽談判,氣氛熱烈。雖然最終市場的交易總額只有2700萬元,但這是制片廠自己獨立做成的第一筆跨國交易,無疑揭開了中國電影史新的一頁。
與國際接軌,是電影節成功的必備條件,也是吳貽弓恪守的原則,宣傳上當然也不例外。盡管那時的制版和印刷技藝還不夠完美,但海報、會刊、指南、專題宣傳等等,這些電影節必須有的常規宣傳,上海電影節都做得非常精致,不亞于其他大型的國際電影節。就拿海報來說,我們采用專業和群眾結合、指派和海選并舉的征稿形式,從成百上千張樣稿中分階段淘汰,通過反復多輪的評比篩選,確定了一張在鏡頭中透視現代化上海的設計稿作為電影節主海報,這張構圖雅致、含義深邃又能讓人一目了然的海報,獲得了中外來賓的交口稱贊。時至今日,它的獨特性和藝術性依然會讓人眼睛一亮,思緒飛揚。
要說電影節宣傳最難最煩最頭疼的事,一是新聞發布會,二是“每日新聞”的編輯。發布會一場接一場,有時記者蜂擁而至、人滿為患,有時問津者寥寥無幾,出于對客人的尊重,我們還得組織工作人員到現場“濫竽充數”填場子。至于參加發布會的明星導演,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態度,有時冷不丁會“不著調”,弄得我們措手不及。曾經有位來自法國的導演,自稱對上海很有感情,對上海的紅色歷史也頗有研究,從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變到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說得頭頭是道,引來不少掌聲。誰料講到興頭上,他話鋒一轉,以“爭民主求自由”為幌子,為當今的“民運分子”鳴冤叫屈。作為主持的我,當然不能聽之任之,態度又不能簡單粗暴,當我的多次提醒和干涉被他忽視之后,我果斷終止了這場發布會。事后,我立即向吳貽弓匯報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對我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正是這種信任,鼓勵我們放手大膽、高度負責地去做好各項工作,及時處理一些突兀發生的意外。記得,我們在《每日新聞》上登載了一幅評委奧列佛斯通和韓國參賽片《悲歌一曲》女主演吳貞孩的合影,不料引來某個友好鄰邦的強烈不滿,他們找到我們表示抗議,說了一些很刺耳的話。我們明白,他們言辭激烈,并不是對這兩位電影人有多大意見,而是相悖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賦予他們的立場,令他們必須有個態度。我們一方面做一些必要的解釋,一方面積極安撫,用中國人的熱情化解他們的怒氣,及時平息了這場矛盾。
說到《每日新聞》,這也完全是與國際接軌的產物。大凡上了規模的國際電影節,每天都會出一份雜志,報道頭天電影節舉行的主要活動,預告當天的一些重要事項,還會介紹一些電影節重磅嘉賓和參賽影片,圖文并茂,內容豐富,是展示電影節的重要窗口。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籌辦期間,組委會就提出也要辦一份《每日新聞》,而且要中英文對照。盡管那時我們面臨的困難很大,無論是制版、印刷技術,還是采訪編輯力量,都難以勝任每天出一份雙語的16開本、32頁的雜志。但是,與國際接軌不容置疑,更不能推諉。習慣于“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我們,殫精竭慮、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餓了喝口贊助來的八寶粥,吃根不要錢的火腿腸;困了,就趴在桌上打個盹,每天通宵達旦,硬是克服各種困難,堅持電影節期間每天向賓客奉上一份《每日新聞》,盡管其容量難以和戛納等電影節相比,但它完全符合“國際慣例”。一開始,我曾經希望吳貽弓為這份雜志把把關,可是他笑著對我說,既然讓你當主編,就相信你有這方面的能力,你就大膽地干,真的有了什么,我來承擔。果然,我們曾經出過些差錯,但每次吳貽弓都只是提醒下次注意,從沒有疾言厲色地給予批評。
叁
當然,與國際接軌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當人們的思維和行為還沒有從約定俗成的習慣中解脫出來時,會產生不理解,甚至誤解。通常,中國人辦節過節,離不開吃。辦電影節,四方來客賓至如歸,自然要解決食宿,也少不了圓臺面的相聚。可國外辦電影節,無人過問這些,賓客都得自己解決。于是,老吳就與國際接軌了。關照接待要熱情,但不搞吃吃喝喝。這么一接軌,矛盾立馬出現。那些老資格有名望的電影藝術家,平時到哪都有人圍著捧著,一日三餐安排得妥妥帖帖。現在上海電影節連這些也不管了,這不是壞了規矩嗎?涵養好的,悶悶不樂,有點脾氣的少不了要嚷上幾句:上海人的小家子氣。但是國際制片人與會代表的反應卻大相徑庭。開始,他們擔心中國人辦節熱衷于推杯換盞,吃來吃去。那位親臨電影節的制片人協會的秘書長每天瞅著飯點就貓在影城三樓的“影城酒家”旁,考察“吃風”,一連幾天門庭冷落,讓他徹底打消了顧慮,也脫掉了有色眼鏡。再說電影觀摩,組委會明確規定除評委、記者等專場外,一律取消贈票,不管誰進電影院都得買票,誰送誰買。這種做法自然又有人不爽了。不爽也無奈,要與國際接軌肯定會傷及人情。或許最傷某些人情的還是評獎,雖然評委會主任是謝晉,但國際制片人慣用的程序不能違背,更不能更改,形式公平公正,程序嚴絲合縫,一人一票,各抒己見,三輪遴選,優勝劣汰,最終揭曉幾個大獎都沒有國產片的份。從感情上說,吳貽弓也好,謝晉也好,包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難免有些遺憾;但是沒有暗箱操作,沒有營私舞弊,這又讓我們問心無愧。正是這些與國際接軌的枝枝節節,體現了正宗,表達了真誠,為上海國際電影節贏得了聲譽,使它一亮相就獲得要求苛刻的國際制片人協會的認可,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A類國際電影節。
吳貽弓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他導演的這些“舊事”已融匯于上海這座城市,伴隨著他不朽的電影作品,為我們留下了永恒的精彩和永遠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