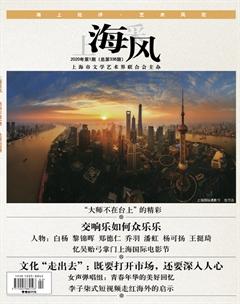熊佛西夜訪梅蘭芳
曹樹鈞

時值杰出的戲劇家熊佛西誕生120周年之際,寫一段他與梅蘭芳的故事。
1949年春,在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號角聲中,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濃重。在上海閘北區竇安樂路一所小樓里,幾位年輕人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仿佛同一位臨窗而坐的長須老人在談心。這是上海地下劇影協會的幾位同志正在召開秘密會議。上海地下劇影協會是中央和上海地下文委領導的外圍組織,主要任務是在戲劇界上層人士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并組織迎接解放的活動。今天出席會議的有許多負責同志,其中有黨員,也有非中共人士。居中坐著的那位長須老人叫熊佛西,戲劇界都親切地稱他為“佛老”,他是一位著名戲劇家,非中共人士。佛老年過半百,圓圓的臉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臉上總是笑嘻嘻的,雖然留著一把長須,仍露出孩子般的純樸。地下劇影協會半個月左右碰一次頭,地點不固定,每次閱讀一些黨的文件,討論形勢發展、商量地下活動并檢查其效果。今天的會議在佛老家舉行,由上級派來的一位姓吳的女同志傳達一項重要指示。
會議開始前,佛老在樓下親自開門,迎接每一個到會的人,進來的人手里總帶著一些東西,不是鹵菜,就是糕點。萬一有可疑的人闖入,就迅速裝成這是一次為佛老祝壽的聚會。
“佛老,人都到齊了嗎?”吳同志問。
“都到齊了,您說吧。”
吳同志用清晰而略低的聲音開始說道:“各位先生,你們知道,淮海戰役我們已經取得全勝,我軍正積極準備渡江。敵人已經樹倒猢猻散,蔣家王朝的喪鐘已經敲響。然而,狗急跳墻,還必然會垂死掙扎,他們還準備脅迫各界不少知名人士同他們一起逃往臺灣。為了打破他們這一陰謀,地下文委指示我們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深入的統戰工作。在戲劇電影界,尤其要注意做好梅蘭芳、周信芳兩位先生的工作。他們兩位名聲大、影響廣,傾向進步,有全國威望,反動派必然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敵人不僅脅迫,甚至武力綁架他們都很有可能。”說到這兒,吳同志向在座的幾位先生一個一個地看了過來,停頓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極為堅定地說:“文委要求地下劇影協會派人同這兩位先生正面接觸,坦率談心,給他們以具體的幫助和指引。”緊接著,吳同志又以商量的口吻說:“諸位看看,派那位先生去做這件工作合適?”
于是,到會者開始了緊張而又熱烈的討論。
“我看佛老去最合適。”地下劇影協會負責人之一的劉厚生同志直率地提名說:“佛老同這兩位大師都熟悉,他自己也是戲劇界的老前輩。”
接著幾個人發言,都一致認為這件事由佛老去最恰當不過。
在幾位年輕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熱烈討論過程中,熊佛西神態嚴肅。他認真聽取這些年輕同志的分析,一面自己估量著,這件事,我能完成嗎?
在場的人都談了看法,最后劉厚生同志征詢熊佛西的意見:“佛老,您看,這件事您去如何?”
“好,就我去吧!”熊佛西慨然接受了任務。
當夜,熊佛西一個人睡在臥室里,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晚上開會的情形,會后負責人同佛老個別交談的內容,又一一浮現在他眼前。他深深感到,黨將這樣一個重要的工作委托給他,這是對他的最大信任。他又想到這幾天謠言四起,什么“共產共妻”啦,什么“共產黨對文化人洗腦筋”啦,鬧得人心惶惶。
在這種情況下,梅蘭芳思想會不會有什么波動?但又一想,梅先生是一位正直、愛國的藝術家,他有鮮明的愛憎,明確的是非觀念,決不會在關鍵時刻走岔道。這時,熊佛西的腦海中又浮現出抗戰勝利不久,在大街上遇到梅蘭芳的情景。那天,梅蘭芳剃了胡子,穿著一身整潔的西裝,臉上露出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笑容,仿佛年輕了十歲。他巧遇佛老,分外興奮,緊緊握住熊佛西的手說:“佛老,想不到我們在這兒又見面了!日本鬼子終于垮臺了,我又能重新登臺了!”熊佛西也含著熱淚說:“畹華,你真不容易呀,寧可賣畫為生,拒不為鬼子演戲,可敬可佩!”想著他蓄須明志,熊佛西似乎覺得梅蘭芳又笑盈盈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忽然,耳邊又跳出吳同志臨別時反復叮囑的話語:“佛老,您可一定要抓緊時間,搶在敵人的前頭,無論如何不能讓梅、周兩位先生被敵人劫持走啊I”想到這兒,熊佛西“霍”地從床上爬起來,一看寫字臺上的小鐘正指著午夜二點。
他沉思了片刻,決定就在這兩天分別拜訪梅蘭芳、周信芳兩位先生,明天晚上,喔,現在已經過了午夜,應該說是今天晚上,就去拜訪梅先生。
第二天傍晚,熊佛西穿著一件長袍,拄著一根拐杖,步行前去拜訪梅先生。
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昏昏蒙蒙的馬路上,一會兒有國民黨的摩托車急馳而過,一會兒有一隊一隊全副武裝的軍警沿街巡邏。忽然,一輛“強盜車”(上海人對反動派捕人的警車的俗稱)發出恐怖的哨響嗚嗚地呼嘯而過,從車子背面門的窗口上還可以看見上了手銬的“囚犯”,他們一個個面黃肌瘦,眼睛里閃耀著憤怒的火焰。
到了梅宅,熊佛西將電鈴按了一下,沒有反應。再按一下,還是沒有人開門。“莫非梅先生不在家?”熊佛西暗暗思忖,又一想晚上他會上哪兒呢?他一般晚上是不出門的。于是,熊佛西將電鈴又按了一下。
邊門打開了,開門的是一位五十歲上下的阿姨。原來剛才她一直在門洞里張望,見來客一直按鈴,便向梅先生察報。經梅先生同意后,才將邊門打開。
就在邊門打開的時候,兩個黑影從大街的電線桿旁晃了一下,很快又消失了。熊佛西和出來開門的阿姨都沒有察覺到。
“先生,儂是——”阿姨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熊佛西一眼,操著上海方言問道。
“我叫熊佛西,狗熊的熊,上海實驗戲劇學校的校長,儂向梅先生講一講,伊就曉得格。”熊佛西也用帶著江西口音的上海話回答道。
正說著,在樓上窗口張望了一會的梅蘭芳先生下來了。
“啊,佛老,您來了,快請上樓。”梅蘭芳緊緊地握住佛老的手,熱情地引他進院。
剛入庭院,熊佛西就大聲說道:“哈哈,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敝校有一點小事,特來打擾足下。”
“噓。”梅先生忽然用食指朝嘴上指了一下,然后湊近熊佛西,低聲地說:“佛老,隔墻有耳,新近搬來的鄰居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
熊佛西連聲“哦哦”,點了點頭。抬頭一看,庭院臺階附近種上各種各樣的牽牛花,還養著不少鴿子,忙將話題一轉。
“梅先生,你這兒別有洞天,真是自成一格啊!”
梅蘭芳笑著說:? “我沒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歡種種花,養養鴿子,搞一點畫。佛老,您可別小看這些鴿子,我的近視眼就是它們幫我治好的。”
“喔,鴿子還能治病,頭一回聽見,你倒說說看。”熊佛西饒有興趣地問。
梅蘭芳一邊走,一邊說:“您知道,小時候我有輕度近視,眼珠子轉動不靈活。咱們唱戲的講究的就是手眼身法步,眼珠子呆板,目光無神,這還怎么唱戲呢?為這件事,我擔憂了好幾年。后來,我偶然養了幾對鴿子。鴿子飛得很高,我的眼睛總是不停地隨著鴿子動,愈望愈遠,仿佛望到天盡頭。天長日久,您猜怎么著?”梅蘭芬說到這兒,頓了頓,笑了笑說:“不知不覺,我那眼睛的毛病居然就治過來了。”
“畹華,你可真是個有心人哪!”熊佛西笑著說。
上了樓,梅蘭芳請熊佛西在一張單人沙發上就座,還沒等他沏茶,熊佛西就開門見山:“梅先生,上次承蒙你和周先生光臨敝校,舉行‘梅周義演。這次演出,不光在經濟上幫了我們的大忙,對那些妄圖扼殺劇校的家伙,也是一個很有力的打擊呢!”熊佛西用手有力地揮了一下。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梅先生謙遜地笑了笑。
“梅先生,下次有機會,還要請你和周先生再度合作,來敝校義演一次,如何?”熊佛西直率地問道。
“可以,只要你定個日子,我一定同周先生前來參加。”梅先生一口答應。阿姨將茶送了上來,梅先生接了一杯放在熊佛西旁邊。
“好!我先代表劇校全體師生,向你表示深切的謝意!”熊佛西從沙發上站了起來,真誠地向梅先生微微地鞠了一個躬。
“您坐,您坐,先喝口茶。這是一位朋友剛從福建帶來的烏龍茶葉,您嘗一嘗。”
這時,夜幕已經降臨,熊佛西見梅先生將窗簾布拉了起來,阿姨也已退出,便從單人沙發上起身,同梅先生并肩而坐。
“梅先生”,熊佛西忽然聲音壓低了一些,神色莊嚴地說:“今天我并非專為請你義演而來,主要是——”說到這兒。熊佛西警戒地向四周看了一看,接著說:“主要是受‘有關方面委托而來。”
梅先生一聽“有關方面”四個字,心中便明白了三分,忙說:“佛老但講無妨,畹華洗耳恭聽。”
于是,熊佛西將地下文委的指示用自己的語言轉述了一遍,又對梅先生分析了當前的形勢,談自己對中國前途的看法,并鼓勵梅先生不要怕受威脅。
“梅先生,”說著說著熊佛西激動起來,話也滔滔不絕起來,他鄭重地說:“作為一位有良心的藝術家,誰能坐視國家繼續這樣亂糟糟地下去,而至滅亡!如今黑暗王朝即將倒臺,光明即將到來,你我都會感到由衷高興的。先生是一位有志氣、有愛國心的藝術家,佛西深信先生不會被反動勢力所嚇倒。你我都知道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人,什么是獸。但是,古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請先生一定要準備‘應變。那些口里天天嚷著‘禮義廉恥,卻無時無刻不干著卑鄙齷齪勾當的家伙,他們什么壞事都做得出來……”
正講到一半,忽然一陣尖銳刺耳的警車聲由遠及近從窗外傳來,并且似乎停在了附近。熊佛西和梅蘭芳不約而同地走到了窗口,凝神屏氣地向窗外瞭望。借著馬路上微弱的路燈光,隱隱約約地只見對面馬路上,軍警們森嚴地站成兩行,果然有一輛“強盜車”,停在附近一條弄堂門口,不一會,兩個中年人被憲兵們推推搡搡押上了囚車。
又一陣警車的呼嘯聲劃過長空,接著便是死一般的沉寂,空氣都似乎凝滯住了。
熊佛西步履沉重地走到沙發邊,喝了一口茶,又用洪亮的聲音繼續剛才的話說:“梅先生,我再說一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一定要做好‘應變的準備,以免遭到那些野獸們的毒手。”他將“毒手”兩個字說得特別清晰,目光很自然地朝窗口瞟了一下。
“砰砰!砰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夾著一陣又一陣的門鈴聲傳進室內。
“梅先生,梅先生,不好了,有三四個粗壯大漢拼命敲門,說是進來查戶口,怎么辦?”阿姨三步兩步跑上樓來,氣喘吁吁地問梅蘭芳。
“不要慌,請他們進來,熊先生是我的朋友,怕什么?”梅蘭芳沉著地說。不一會,兩個全副武裝的憲兵和兩個腰里插著手槍的便衣闖了進來。
一個憲兵拿著一個大本本,對梅蘭芳說:“我們是警備司令部的,今夜奉命突擊查戶口,將你的戶口簿拿出來!”
阿姨顫抖地將戶口簿拿了過來,梅蘭芳將它遞給憲兵。
“你們家幾口人?”
“五口。”
“你兒子上哪兒去了?”
“他上鄰居家玩去了。”
“你老婆呢?”
“她上親戚家送東西去了。”
憲兵氣勢洶洶地盤問,梅蘭芳不慌不忙一一做了回答。
憲兵見他對答如流,人口情況同戶口本上記載的又一絲不差,便指著熊佛西問道:“他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朋友,叫熊佛西,他是——”
“好了,現在不用你說了,我們要問他。”一個滿臉絡腮胡子的便衣這時忽然打斷梅蘭芳的話,走到熊佛西面前,眼睛死死地盯著他。
“你是干什么的?”
“上海實驗戲劇學校的校長。”熊佛西慢吞吞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因為他知道自己有個毛病,話說急了容易口吃,為了不使敵人生疑,他竭力將回答的話說得慢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