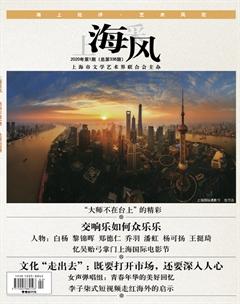女聲彈唱組:青春年華的美好回憶



2016年春天,在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慶祝建系60周年的前夕,一群古稀之年的老太太們為了一個共同的心愿聚集在上音校園里。她們是20世紀60年代上音民樂系和上音附中民樂科的畢業生,原民樂系女聲彈唱的參與者:元老級的成員張懷粵(二胡)、丁言儀(揚琴)、潘慧珠(琵琶),及70年代彈唱組演出活動的主將們:龐波兒(揚琴)、林元京(揚琴)、鄭玉華(琵琶)、金振瑤(古箏)和章循三(三弦)。
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對女聲彈唱當年藝術實踐點點滴滴的美好回憶,讓她們容光煥發,激動不已。回首往事,她們有這樣的共識:這個曾經讓她們付出青春年華的女聲彈唱,不僅是每個人藝術生涯中的重要一頁,更是現代民樂發展史上值得回顧和總結的一個篇章。女聲彈唱曾以煥然一新的形式和生動活潑、健康陽光的表演風格,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她們的彈唱及所演作品反映了時代的風貌,沉淀著那個時代文化的內涵,在繼承傳統和民間音樂的基礎上,豐富了自彈自唱的表達能力,把彈唱這個歷來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一切,讓女聲彈唱組的成員們感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把這段珍貴的歷史記錄下來,與未來民樂事業的后繼者們共同分享。
壹
女聲彈唱誕生于1963年,因1966年夏天“文革”的開始而停止演出。1971年春天重返舞臺的女聲彈唱一路順風地在1976年金秋登上了西歐四國的國際舞臺。1977年初春,女聲彈唱這個節目在觀眾的視線中悄然無聲地消失了。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給這個組合留下了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歷史。
女聲彈唱從1963年初創到1977年的銷聲匿跡,除了1966年到1970年期間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而停擺外,在長達十年之久的演出活動中,有24名民族器樂演奏者參與了這個藝術形式的實踐。其中2名是上音民樂系的進修生:她們是郭兆甄(三弦專業,來自廣州部隊文工團)和周靜梅(琵琶專業,原南京藝術學院琵琶老師)。其余22名女聲彈唱組成員均是上音民樂系和附中民族器樂專業的學生,當中20人都是彈撥樂專業,只有張懷粵和閔惠芬2人是主修二胡的拉弦樂專業。
l956年上音民樂系的建立和之前一年附中民樂科的誕生,顯示了當時中央文藝方針中大力提倡革命化、民族化和大眾化的決心。1958年上音附中為加大發展民族音樂的力度跨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從附中初中部的鋼琴專業中選拔了一批優秀的學生改學民族樂器。她們不僅為上音校園內民樂系科增添了一支生力軍,更可貴的是她們所具備的扎實的器樂演奏技巧和訓練有素的樂理知識,對民族器樂的作品和演奏技巧的突破革新具有深遠的影響。女聲彈唱的許多成員在自己的專業簡歷上都有這樣的轉折,如彈唱組初建時的組員張念冰(三弦)、忻愛蓮(揚琴)、高星貞(古琴)、項斯華(古箏),以及隨后參加過彈唱演出的張燕(古箏)、孫孟光(琵琶)、浦琦璋(揚琴)、龐波兒(揚琴)、林元京(揚琴)、章循三(三弦),都是從附中鋼琴科轉到民樂科的。這些女將們不僅增添了曾經以男生為主的民樂系科的色彩,更為以后女聲彈唱的建立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生源。
當時上音校園內轟轟烈烈的文藝革命化、民族化和大眾化的氣氛激發了民樂系師生在業務上力求創新的激情,女聲彈唱組的元老組員張懷粵和張念冰在彈唱組成立前就開始了自拉自唱、自彈自唱的大膽嘗試。張懷粵是1955年考入上音附中的首屆二胡專業的女生,1965年從上音民樂系畢業。當時年僅16歲的她,卻已經過5年部隊文工隊的磨練,唱歌、演戲、拉琴的自由結合已成她的工作常態,二胡獨奏與自拉自唱更是她日漸形成且廣受歡迎的節目。進附中第一年,她便在恩師陸修棠和陳恭則先生的關懷鼓勵下,登上文化廣場修繕一新的大舞臺演奏劉天華的二胡名曲,并受命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音樂周演出,擔任上海滬劇團丁是娥演唱《羅漢錢》選段和本院鞠秀芳、沈德皓演唱榆林小曲《姐妹打秋千》的伴奏樂隊首席。她本人也在附中民歌課上得到著名民間藝人丁喜才老師的榆林小曲傳授,因而在下鄉演出時表演的《五哥放羊》《掛紅燈》及其他獨唱與自拉自唱節目深受群眾喜愛。
張念冰是民樂系1965年三弦專業畢業生,她曾是上音附中初中部鋼琴專業的學生,升入高中時,轉入長笛專業一年,高二學三弦,1960年以優異成績直升上音民樂系。她回憶當時自己彈唱的體會:“我跟王秀卿先生學三弦時,她同時教過我一些自彈自唱的單弦牌子曲,我覺得由于自己的音樂基礎好,加上膽子也比較大,所以敢于一個人拿了把大三弦在上音大禮堂的舞臺上自彈自唱《翻身道情》和《洪湖水浪打浪》。”
對彈唱形式創新有興趣的師生還不止她們倆。張懷粵清楚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一天,她在獨自練習自拉自唱時,被正好路過的陳應時學長聽到,陳不僅大聲喝彩,而且當即鼓動她多找幾位不同樂器專業的女同學合作搞個女聲彈唱,“這種新的表演形式肯定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是這個建議促成了彈唱形式從個體到組合模式的轉換。在陳的有力推薦下,張首先找到剛從附中升入本科的潘慧珠。潘曾是附中高一聲樂科的學生,高二因變聲問題轉入民樂科學習琵琶,聲樂是她從未間斷的第二主課。她所接受的奏、唱兼備的訓練正是彈唱組合非常需要的對象。張的想法與潘的意愿一拍即合,她們很快又和也在嘗試三弦彈唱的張念冰達成一致的看法。自彈自唱的藝術形式在上音民樂史上突破性的探索,在這富有革新精神的學生中迅速醞釀發芽。
張懷粵認為建立一個由多種不同民樂器組合起來的彈唱是一個完全有可能即刻投入的革新項目。她的倡議不僅得到同班同學忻愛蓮、高星貞的積極呼應,更獲得當時以民樂系黨支書記和副系主任金村田老師為首的系領導的全力支持。很快,一個由張懷粵(二胡)、忻愛蓮(揚琴)、張念冰(三弦)、高星貞(柳琴、中阮)和潘慧珠(琵琶)組成的五人彈唱組在系領導的安排下正式成為與民樂系原有的小合奏、齊奏、重奏等藝術形式同等重要的選修課課目。與此同時,68屆的丁言儀(揚琴)欣然接受張懷粵的邀請也一起參加彈唱的排練和演出。自幼熱愛唱歌和跳舞的丁言儀雖然進入上音附中后學的是揚琴專業,但對每一個能讓她放開嗓子唱歌的工作都深感興趣。她不僅把唱歌的熱情帶進了彈唱組,又因為她的舞蹈功底了得,在為女聲彈唱設計表演動作時發揮了無人能及的作用。
尚在摸索階段的彈唱組得到了領導和老師們很多的關注和幫助,如有給她們上一對一聲樂課的許多聲樂系老師,有在她們排練中經常光臨現場指導的民樂作曲系的老師,如于會泳、胡登跳、連波、江明惇、夏飛云、張敦智等和同輩的顧冠仁、周仲康等。彈唱組最初訓練和演出的節目單上有不少于會泳的《不唱山歌心不爽》《人民公社實在好》《幸福花開遍地香》等作品。所以大家都記得于會泳曾多次與彈唱組成員們一起研究如何把這些獨唱歌曲改編成彈唱的曲目,以及不厭其煩地同她們示范唱好歌曲中每個細節的關鍵,他的作品和他的輔導讓女聲彈唱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貳
據原古箏齊奏組的范上娥(民樂系1966年古箏專業畢業生)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們為周總理表演古箏齊奏,在演出后的接見中,總理向我們講了音樂民族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性……好像還提到了《洪湖水浪打浪》。從那以后,我們就開始演出一些邊彈邊唱的曲目,如《采花調》《洪湖水浪打浪》等。”古箏齊奏組帶回的周總理指示得到院系二級領導的重視,也使已在為探索彈唱藝術而努力的成員們受到很大的鼓舞。借著這股東風,她們深信藝術走向通俗、面向大眾的革新精神一定會被這個時代接受和發揚光大。
女聲彈唱組這朵不起眼的小花幸運地誕生在一個能讓她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時代。在全國文藝界大力提倡“三化”的驅動下,以賀綠汀院長為首的院領導把全校師生下鄉下廠為廣大群眾演出作為文藝革命中的必修課程。在熱火朝天面向大眾的廣闊舞臺上,民樂系所有的女將們幾乎都練就了既唱又彈、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表演的本事。在僅有的幾張珍貴的照片中,除了女聲彈唱的基本組員外,還有項斯華(古箏)、周靜梅(琵琶)等的身影。作品和演唱能力尚處于稚嫩狀態的女聲彈唱在各種場合的演出中得到了意義非凡的歷練,廣大觀眾對她們那充滿生活氣息的藝術風格所反映出來的理解和歡迎使這個節目很快脫穎而出。作為一個嶄新的藝術形式,女聲彈唱以自己的作品《碼頭女司機》《學習老楊好榜樣》等曲目登上了1965年和1966年“上海之春”的舞臺。據大家的回憶,參加1965年“上海之春”演出的成員有第一代組合成員張懷粵、張念冰、忻愛蓮、高星貞、丁言儀和潘慧珠。后來張、張、忻、高四位于1965年畢業離校,又組成了第二代組合,成員潘慧珠、丁言儀、閔惠芬、郭兆甄和孫孟光參加了1966年的第七屆“上海之春”的演出。
1966年夏天,鋪天蓋地的“文革”浪潮席卷全國各地,剛結束“上海之春”演出的女聲彈唱和所有文藝界的同行們一樣,曾經繁忙的藝術活動戛然而止,這一中斷就是整整四個年頭。
1970年的秋天,“文革”開始后尚未分配的上音67、68、69和70屆畢業生按照中央有關“學生復課鬧革命”的指示全部返校等待分配。學校領導將全校各個系科的師生們合并成幾個規模較大的單位,如民樂系、聲樂系的師生和附小的教師們,就曾被安排在一起進行日常的政治學習。整頓還包括除節假日和周末外,學生們必須留校住宿。整個社會從散亂中逐漸回歸秩序,在風暴中疲乏了的人們渴望著正常平靜的生活。校方表示,在不影響政治學習的前提下,允許學生們練琴、練聲,重拾“文革”開始后被荒廢了幾年的基本功訓練。
當時,“八個樣板戲”幾乎占領了當時的文藝舞臺,隨之產生的京劇現代作品《鋼琴伴唱“紅燈記”》、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也在音樂界被視為音樂革命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典范和“破舊立新”的輝煌成果向社會推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清一色的京劇樣板戲和在屏幕上播放了好幾年的《地道戰》《地雷戰》等電影不再能滿足廣大觀眾對多元化藝術的需求。這種不可阻擋的變化讓上音那些擔心學了多年專業而不知前途究竟在何方的學子們看到了學有所用的希望。
據潘慧珠回憶,她們67、68屆畢業生在解放軍農場奉中央指示接受了兩年再教育后,從杭州喬司和安徽溧陽返回上音校園,看到的景象與兩年前離開上海時有了天差地別的變化。校園里到處響起久違的琴聲和歌聲。返校后的畢業生們清醒地認識到了抓緊時間恢復業務訓練對勝任未來工作的重要性。雖然究竟何去何從,何時下達分配方案,對翹首以待的畢業生們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但不少同學已不再把這段寶貴的時間視為單純的基本功恢復期,更試著在有限的時間內尋找能夠學以致用且切實可行的藝術實踐。
68屆的潘慧珠是這些待配畢業生中的一員。這個最早參加彈唱組的成員,憑著對彈唱藝術的熱愛和執著,從未停止過尋求這種藝術形式能重上舞臺并加以發展的契機。她看到了當時廣大觀眾對文藝作品和形式多樣化的期待,以及上音校園內領導和師生對業務學習的日益關注和重視,特別是非常時期所造成的民樂系幾屆畢業生集體滯留在校等待分配,這一史無前例的特殊情況在客觀上形成了極難得的人才高度集中和穩定的局面。民樂系待分配的女生們幾乎全是從上音附中一條龍升上來的學有所成的專業音樂工作者,她們是彈唱組最需要也是最完美的生源保證。對此,潘慧珠深信不疑,且已看到了彈唱復出的現實意義,她覺得必須牢牢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盡快充實人員,恢復訓練,讓這個曾經在“文革”前就已深受觀眾喜愛的女聲彈唱組重返舞臺。事實上,當初民樂系已有不少同學對女聲彈唱這個節目充滿興趣和信心。潘慧珠在這個當口不失時機地鼓動起大家心中原本就有的熱情,使重建女聲彈唱組的想法很快變成了現實。
原彈唱組的丁言儀、閔惠芬和孫孟光是重建后當然的骨干力量,張燕(古箏)、浦琦璋(揚琴)、龐波兒(揚琴)、王昌元(古箏)、王錚(古箏)、林元京(揚琴)、章循三(三弦)、趙宏(琵琶)等這群風華正茂的女將們的加入,更使原來就有良好基礎的女聲彈唱如虎添翼。組員們在聲樂系謝紹曾、溫可錚、胡靖舫、魏秀娥、高思聰、陳敏莊、鞠秀芳和鄭倜等多位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演唱水平有了可喜的長進。在彈唱組原有保留曲目的基礎上,在眾多詞、曲作者們的支持下,又增加了不少創作和改編的新曲目,他們有于會泳、朱踐耳、胡登跳、連波、張敦智、顧冠仁、周仲康、劉敦南、朱曉谷、徐景新、曹美韻、黃允箴、浦琦璋、周世昌、郭兆甄、趙開生和劉韻若等。中斷了4年演出活動的女聲彈唱組終于重新回到舞臺,迎來了新的挑戰。
加入了新鮮血液的女聲彈唱組除了活躍在音樂廳、上海各區縣劇場和下鄉、下廠、下基層的各種大小舞臺上,還接到了許多接待外賓的演出任務。在當時國門逐漸開放的形勢下,文藝招待會通常是接待外賓在華訪問期間必不可少的活動之一。女聲彈唱以其濃郁的民族音樂特色和生動活潑的表演形式被選為外事演出中的保留節目。據大家的回憶,僅在上海南京西路原中蘇友好大廈友誼廳的舞臺上,她們就曾經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埃塞俄比亞的塞拉西皇帝、阿爾及利亞的布邁丁總統、尼泊爾公主、菲律賓的馬科斯夫人、越南黨政代表團、美國的黑格將軍、朝鮮國會代表團和朝鮮血海歌舞團等國外賓演出過。她們不僅向外賓介紹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并常以彈唱的形式改編和表演這些國家的著名歌曲而得到外賓們的熱烈歡迎。女聲彈唱在面向各種不同觀眾的演出中日趨成熟,欣欣向上。
叁
在越來越多的演出中獲得的肯定和歡迎,讓組員們欣喜地看到了彈唱這個形式發展的前景,但她們清醒地認識到,要將彈唱這個藝術形式提升到一個應有的高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可貴的一步雖已邁出,但如何創作更多具有彈唱特色的作品,并練就高質量的演唱演奏水平,仍需這個群體持之以恒地努力。那個讓畢業生們期待已久的分配條例卻讓她們看到了“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那就是上音的畢業生屬全國統配,女聲彈唱十多個成員按此原則將被分配至全國各地的文藝單位,這意味著,這個在重建后剛站穩腳跟的組合在分配后完全有可能不復存在!
全體組員都不想看到這個已被證明深受觀眾喜愛的創新項目就此半途夭折,大家都覺得要再組建一個類似的、經過長期訓練而如此默契的彈唱組合太難了。1973年1月,彈唱組的潘慧珠、浦琦璋、龐波兒、王昌元、孫孟光、王錚、林元京和章循三等八人得到院方通知,她們被一起分配到了上海歌劇院的民樂隊!同年4月,在歌劇院只待了兩三個月的女聲彈唱組又因新的演出任務奉命調至上海合唱團。一起赴調的還有歌劇院民樂隊的楊家佩,她曾是原上海民族樂團資深的多種彈撥樂器的演奏員。上海合唱團這時正與上海交響樂團聯合排演交響樂《智取威虎山》,這是上海文藝界學習京劇樣板戲的重頭節目之一,即將赴京演出接受中央有關方面的審查。這場赴京演出是上海文藝界打造音樂界樣板團的前奏,音樂會由兩個部分組成:上半場是獨唱、獨奏、女聲彈唱等小型節目,獨唱者有男高音施鴻鄂、女高音林明珍和朱逢博,以及彈唱組成員中閔惠芬的二胡獨奏和王昌元的古箏獨奏;下半場是交響樂《智取威虎山》。在準備赴京演出的過程中,當時在交響樂團任琵琶演奏員的顧惠曼(1966屆上音附中琵琶畢業)和在上海合唱團任合唱團員的李康南(1969屆上音附中琵琶專業)也被調入彈唱組參加排練和演出。其時先后參與彈唱演出的成員已達16個人之多,清一色的女孩子,且年紀相仿,她們都到了考慮生育的人生階段。關于“何時懷孕生子”曾經是她們聚在一起交談的熱門話題,每個人都想挑選一個既不影響彈唱演出任務,又不讓自己錯過最佳生育年齡的時機來完成這件人生大事,想不到這些敬業的女孩子們左思右想后的決定,還是遇上了沒有預料到的、非一般的演出任務:女聲彈唱在調至上海合唱團后必須隨即離開上海,遠赴北京逾半年之久。這個無法預估的安排,讓懷孕已久的孫孟光和章循三無緣參加赴京演出。在京的幾個月中,彈琵琶的趙宏和彈古箏的王錚則因妊娠反應較大而無法堅持繁重的排練工作,也先后被迫返回上海。她們的位置由歌劇院民樂隊中的鄭玉華(1967屆上音附中琵琶專業)和金振瑤(1967屆上音附中古箏專業)趕來接棒。隨后,身懷六甲的潘慧珠又返回上海侍產。所幸懷孕高峰所造成人員的頻繁調動并沒有影響節目的質量,每個新加入的組員都能以其扎實的業務能力迅速跟上大家的步伐。
在京期間,中央電視臺錄制了女聲彈唱的保留曲目《碼頭女司機》《雷鋒頌》和《紡織女工》等,同時中國唱片廠把這些歌曲制成唱片,人們經常可以在電臺聽到這些歌曲的播放。1973年底,彈唱組隨同上海合唱團和上海交響樂團一起返回上海,被納入兩團合并而成的樣板團上海樂團的編制。在上海樂團中她們是一個獨立的群體,除了演出彈唱節目外,還在許多其他的節目中擔當伴奏的任務,例如民歌演唱家方芝芬就經常與彈唱組親密合作,一起演出。在上海樂團期間,聲樂老師鄭興麗的悉心輔導更令全體組員至今不能忘懷。她針對彈唱的發音、吐字等歌唱技巧設計了一套訓練法,使女聲彈唱在統一聲音和表現能力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女聲彈唱的成員們走過了學生時代,開始了職業演奏者的藝術生涯,她們成為上海文藝團體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組合,在忙忙碌碌的演出中繼續努力地錘煉自己。
肆
l976年,由上海樂團和上海舞蹈學校為主組成的上海藝術團奉命赴希臘、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四國訪問演出。這是“文革”后期上海市政府對外友協部門組織的最早的音樂舞蹈藝術代表團之一。由于出國人員編制的控制,女聲彈唱從11人的組合緊縮至9人。當時在上海電影樂團工作的元老級組員張懷粵曾受邀與彈唱組一起為出國演出集訓了好幾個月,但最終因只有一個二胡編制,她在彈唱中的位置由二胡獨奏的閔惠芬兼任了。張懷粵以及與閔惠芬長期合作的揚琴伙伴丁言儀都因編制原因未能成行,使大家深感遺憾。林元京接替了丁言儀的位置成為閔惠芬的揚琴伴奏。
女聲彈唱組這次出訪演出的曲目有《雷鋒頌》《我為祖國獻糧棉》《幸福花開遍地香》《碼頭女司機》《瑤山新歌》《草原女民兵》和《紡織女工》等。在這個被精簡了不少人員的團隊中,彈唱組除了自己的節目外,還必須發揮多面手的作用,來支持其他節目的需要。如在開場的鼓樂合奏中,大忙人林元京成了演奏十面鑼和云鑼的主角;為了加強樂隊的低聲部,潘慧珠拉起了革胡;為了填補弦樂聲部的空缺,楊家佩拉起了二胡;她們是器樂獨奏二胡、板胡、笛子、笙、嗩吶和民歌獨唱等節目中伴奏的主力軍,還是舞蹈《洗衣舞》的伴唱者等。此外,每到一個國家,女聲彈唱的演出曲目中總會有一首經彈唱組的改編能手浦琦璋巧妙潤色過的該國民歌。雖然姑娘們不會講外文,歌聲里帶著濃重的華語口音,可這些當地歌曲依舊讓聽眾們倍感親切,滿心歡喜。她們代表中國人民向出訪國人民表達的友善之情,通過演唱這些曲目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共鳴和互動。
1976年年底,完成了歷時兩個多月出訪任務的上海藝術團啟程回國。與此同時,歷時十年的“文革”正式結束。不久,由于政治形勢巨變所造成的沖擊波的影響,正在走向事業巔峰的女聲彈唱在觀眾的視線之中迅速地、永久地消失了,這個藝術形式原本可以走得更遠更好的,此結果實在出人意料。
女聲彈唱解體后,部分成員繼續留在上海樂團的伴奏樂隊工作。期間,有好幾個人先后調至上海民族樂團,她們是丁言儀、閔惠芬、王昌元、龐波兒、金振瑤、鄭玉華和楊家佩。林元京留在上海樂團的交響樂隊打擊樂組,潘慧珠留在上海樂團任彈唱演員,李康南回到上海樂團的合唱隊,浦琦璋去輕音樂團任電子琴手,王錚去深圳工作,孫孟光和章循三仍在上海歌劇院。雖然那個她們曾為此付出青春年華的女聲彈唱組的結束令人扼腕嘆息,但在女聲彈唱多年藝術的實踐中所獲得的經驗,對這些成員日后的專業活動產生了很有價值的影響。正如丁言儀在她的文章《唱歌這樂子》一文中所寫:“這種邊彈邊唱的形式,我認為可以培養學生多聲部概念,是訓練音準節奏的好辦法之一,增進相互的配合和協調,有利于音樂的表現,我從中得益匪淺,為日后與二胡伴奏及合奏、重奏打下了基礎。我把彈唱形式運用到教學中,寫成揚琴曲收進了我編寫的《青少年學揚琴》《兒童揚琴啟蒙》兩書中,以激發少兒學揚琴的興趣。”她的這段話基本可以反映大多數女聲彈唱成員們的體會。在創立并探索這個藝術形式的過程中,她們獲得了令她們終身受益的寶貴財富。
女聲彈唱在藝術長河中摸索著前進。憑著面向大眾和對藝術美感更新的理念,憑著這個群體不斷修煉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勇氣,在廣大觀眾和業內同行們的支持下,她成為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創建六十年歷史中一個具有突破性的、充滿朝氣和富有新意的藝術形式,以嫻熟的演奏技巧、樸實無華的歌聲和青春洋溢的熱情活躍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舞臺上,雅俗共賞的贊譽正是女聲彈唱堅持不懈努力的目標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