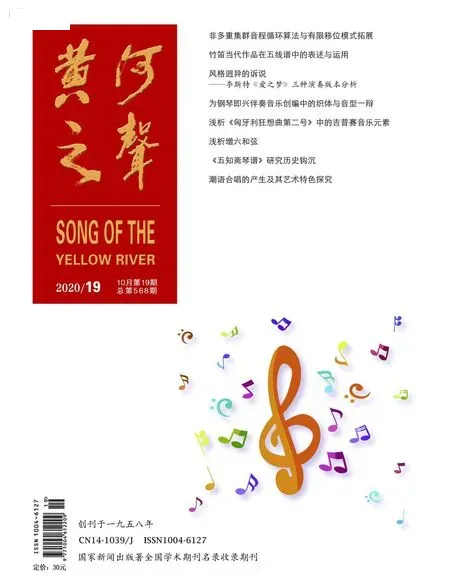箏曲《蒼歌引》的音樂分析
王舒 (河南大學)
一、《蒼歌引》的創作背景
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作曲家在作曲技術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但在創作中更加注重對中國傳統音樂民族旋律風格韻味的把握,在運用西方作曲技術的同時保留了中國音樂的總體風格。箏曲《蒼歌引》就是西方作曲技術與中國傳統音樂相結的產物。
《蒼歌引》為青年作曲家陳哲所做,作品原為古箏與管弦樂隊協奏曲,后來為方便演奏,陳哲還編配了古箏與鋼琴的版本,本文就之以鋼琴伴奏版本為例進行分析的。古箏與鋼琴協奏版本體現了中西方樂器通過精巧作曲技術完美的融合,作品把不僅體現了精湛的作曲技術并且擁有很強的可聽性。
《蒼歌引》出自唐朝詩人韋元旦所作《奉和人日宴大明宮恩賜彩縷人勝應制》詩意所引發,初名為《青韶》,意為美好的春光。“青韶既肇人為日,綺勝初成日作人”便是《青韶》曲名的來源。《爾雅·釋天》又稱:“春為蒼天,夏為昊天。”春乃萬物蒼蒼然生之季節,作為萬物伊始,它既是一天中的清晨,也是人生中的青春,清新而充滿活力。作品通過對“春”的感悟,滿懷了對生命的敬贊之情,作曲家把詩中的對“春”情感用音樂語言表達的淋漓盡致。
二、《蒼歌引》創作技術的分析
(一)定弦的設計與主題動機
傳統的古箏定弦是根據五聲循環分為四個組的模式來進行定弦,而《蒼歌引》的定弦是以D調為基礎但對最低一組的五個音進行了改動“E-#F-A-B-D”改為“E-F-G-B-C”,這樣的定弦突破了傳統古箏的定弦,在五聲中加入小二度(E-F、B-C)、大三度(G-B)的音程關系,突破五聲調式中大二度、小三度單一的音程關系,以此增加音樂的緊張性和動力性,是音樂的發展更加豐富,但《蒼歌引》的定弦依舊保留了大部分的傳統因素。作曲技術的不斷發展下,古箏早已突破了傳統的定弦模式,根據作曲家的需要可以使用各種人工調式進行定弦。
《蒼歌引》的主題動機即來自于五聲調式“#F-A-B”的“小三度”、“大二度”的音程關系,這個短小的動機就成為貫穿于整部作品中的音高材料,作品始終圍繞著“小三度”、“大二度”的關系進行發展。
(二)曲式結構的分析
中國的曲式注重樂思漸變性和展衍性,西方的曲式更注重樂思再現性,而箏曲《蒼歌引》正體現了中西曲式結構的結合,是將中國傳統聯曲體或多段式結構與西方三部性再現原則相結合的作品,體現出對中國傳統曲式的繼承和發揚。
由于作品是中西曲式結構的結合,所以可將該曲以西方作曲技術中的三部性再現原則進行一級結構的劃分,如圖一所示:

圖一:《蒼歌引》結構圖
呈示部為1-19小節,速度為散板形式Rubato?=50。展開部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20-120小節的快板部分,速度變化了五次之多,分別為?=148、?=152、?=156、?=160、?=164;第二部分只有兩小節121-122,使用了Rubato散板形式。再現部也可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123-146的慢板,其速度為?=56和147-181的急板,速度為??=96。
陳哲的《蒼歌引》借鑒了中國聯曲體使用最多的“散-慢-中-快-散”五部式的速度布局和音樂陳述方式,但做出了突破,把音樂成了“散板-快板-散板-慢板-急板”五部分,在“急板”中結束,這突破傳統結構模式中的“散入-散出”,根據該曲的創作背景和此種結構布局的安排,可以對整部作品進行如下理解:春天從萬物伊始到萬物復蘇、柳綠花紅、鶯歌燕舞,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在急板中結束更體現出大地上萬物的生機勃勃。
樂曲的第一個和弦是一個縱向的非三度疊置的五音和弦:D-E-#F-A-B,開始就明確了整部作品為D為宮音的五聲性系統中,并且樂曲的鋼琴伴奏部分結束在D為根音的非三度疊置和弦上。在古箏使用特殊技法(掃弦、拍琴板等)時,鋼琴伴奏常使用離調和弦或添加臨時變化音等,產生不協和的音響效果,增加樂曲的色彩感。這樣的和弦使用更有現代風味,同時又遵循了傳統。
作品的鋼琴伴奏部分織體總體為非三度疊置的柱式和弦,大二度、小三度這樣的和弦更加帶有中國傳統韻味,同時運用了大量的顫音技法,主要是作為背景烘托出該曲的描繪性的“意境美”。節奏多變,切分、后半拍、前半拍、三連音等節奏型的轉換隨處可見,還常與古箏的主旋律形成節奏錯位,這一點主要是吸收了現代作曲技法。雖然使用了大量不同的節奏型,但整部作品并沒有給人風格的轉變或聽感上的雜亂無章。
呈示部以散板的結構徐緩、悠遠的奏出主題動機,給人一種“空靈”的感覺,這正是體現了中國傳統中的“虛”,極其富有中國韻味,鋼琴伴奏pp的弱奏顫音作為背景烘拖更符合主題幽靜、虛幻的氣氛。之后運用掃弦、拍打琴板等演奏技術各種強弱對比最終使用快速的分解和弦上行發展,把音樂推向展開部。
展開段可以分為四個段落,在下面的段落里會做詳細的解說。展開段無論是樂譜還是音響效果都給帶有一種現代風味的感覺,但在中間又有傳統的因素貫穿,尤其是主題動機中的“小三度”、“大二度”也貫穿其中。音樂在展開部不斷地發展,運用了大量的古箏演奏技法如:拍琴板等、節奏上的錯位及重音轉移配合上鋼琴的伴奏,使音樂層層遞進,速度逐漸加快,最終在散板中收尾。
再現段從散板結構性質的呈示部開始后再現了展開部第一部分的材料,樂曲進入急板后大量的使用掃弦和刮奏,力度的不斷增強,不斷地增加樂曲的緊張度,把音樂再次推向高潮,最后連續的旋律上行到最高音一個下行刮奏接煞弦曲終,結束干凈利落,該曲最后的“煞弦”吸收了中國傳統作曲技術與中國傳統民族音樂中的“煞尾”有異曲同工之妙。由于中國傳統曲式中多以“合尾”的方式統一樂思,所以這種再現呈示部開頭的結構更像是西方的再現性質的曲式結構。再現部突破了傳統結構中的“散出”,以急板加以大量的刮奏下曲終,體現了作曲家把中西方作曲技術進行糅合的創新性。
(三)展開段的次級劃分
根據音響效果、古箏的節奏類型和鋼琴的織體變化可對展開部做次級結構的劃分,展開部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20-35小節,速度為?=148;第二部分為36-88小節,速度為?=148;第三部分為89-120小節速度改變了四次,分別為?=152、?=156、?=160、?=164;第四部分為121-122小節,速度為Rubato散板。展開部中的次級結構更像是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多段體連綴的形式。
第一部分為主題動機的片段式發展,使用了大量的休止,使音樂不間斷的向前發展,同時在這一段古箏與鋼琴的協奏運用了西方作曲技術中的復調中“你走我停,你停我走”手法,雖然古箏是動機性的不連貫旋律,但在鋼琴的伴奏下該段的音響效果輕快明朗。
第二部分是最富有展開意味的段落,使用“小三度”、“大二度”的音高材料,譜中所展示出來的音樂織體和節奏類型又可以把第III段分為三部分。36-43使用連續的十六分音符不間斷的重復加深音樂的印象,在第42小節的鋼琴伴奏處就已經預示了節奏的變換,第43小節開始節奏從4/4拍變為3/4拍,節奏型變成了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間的節奏錯位、重心轉移,鋼琴伴奏保持3/4拍的節奏,并使用了定弦中的“E-F-G-B-C”中的音,增強音樂的緊張性,使得這8小節充滿了現代感。之后的52-70小節主要以音階式的級進進行和特殊的古箏演奏技法為主,富有節奏感。71-88為延綿不斷的十六分音符級進上行,此處的旋律線在鋼琴聲部,之后鋼琴織體改編古箏使用三連音,最后兩小鋼琴的連續大跳趣味十足,接著就是下行的刮奏進入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仍舊使用了該曲的主題動機中的“小三度”、“大二度”的音高材料,再節奏上使用前四個八分、八后十六和兩個八分這三種節奏型不斷地組合,使音樂在聽覺效果上越來越緊湊,并配合速度的逐漸加快,音區不斷升高,把音樂推向高潮。
第四部分音高材料還是“小三度”、“大二度”,雖然只有兩小節但卻起到了展開段與再現段的銜接作用。筆者認為這里的散板更像是整首曲子的“散出”,與呈示部的“散入”首尾呼應,那再現段是否可以認為是再現性的補充呢?
三、《蒼歌引》中的中國傳統音樂元素
在西方傳統音樂中主要以調性的布局、主題間的對比、展開和再現、和聲功能等方面對音樂進行結構的劃分。而中國傳統音樂則更加側重于對速度的布局,“散-慢-中-快-散”就是中國典型的音樂組織方法,《蒼歌引》一曲主要就是運用了宏觀的速度布局來控制音樂發展的動力性。在展開部中節拍、節奏不斷地變化正是符合中國傳統音樂中的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當音樂情緒高漲時速度變快力度,情緒平靜時音樂悠長深遠,這樣的“彈性變速運動”體現出中國傳統中的“感性思維”。
正是由于中國傳統音樂不像西方傳統音樂那樣重視對比,“漸變性”便成為了中國傳統音樂的一個特征,筆者認為該曲的“漸變性速度布局”并不明顯,整首樂曲的速度是“散板-快板-散板-慢板-急板”這樣的布局不太符合“漸變式”的思維,所以該曲段落劃分清晰,這一點突破了中國傳統音樂“漸變式”的框架,更加具有現代作曲的特點。但在樂曲中的某些地方也體現了“漸變性”,如展開段落的節拍、速度的變換,是音樂層層漸進。
傳統音樂中的“隱結構”表現在音樂陳述帶有不確定性,這就于要求音樂必須要依靠某些細節因素,如:音程、音型、音色、核心動機等穿插在無主題的“散結構樂曲”中,使音樂在不斷地展衍中的到統一。《蒼歌引》主要運用了“小三度”和“大二度”的音高材料作為整部作品的“粘合劑”,作為“統一性”的體現。
結 語
箏曲《蒼歌引》作為現代箏曲的典范,其中中西方作曲技術的融合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這部作品也體現出中西方美學思想的碰撞,同時這部作品也體現了大自然生機勃勃和積極向上的心態,感謝青年作曲家陳哲給我們帶來如此震撼人心的視聽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