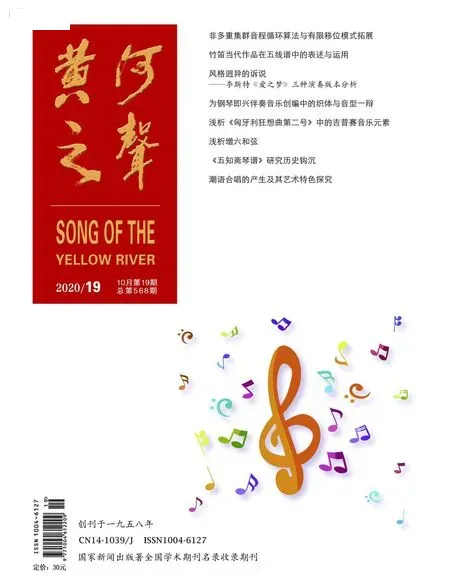竹笛當代作品在五線譜中的表述與運用
張健 (中國音樂學院附中)
五線譜作為當今通用的記譜法,其形象性、直觀性、易解性,使之成為世界上應用最廣的音樂語言。而中國傳統器樂——竹笛,自東晉桓伊曾創作的笛曲《梅花三弄》,到元末作為昆曲的主奏樂器,后至20世紀初出版的《簫笛新譜》;從新中國成立后以馮子存、劉管樂、陸春齡、趙松庭等為代表的第一代笛樂名家,到當代作曲家、演奏家創作的大量如《鷹之戀》(劉文金)、《蝴蝶夢》(關乃忠)、《花泣》(張維良)、《飛歌》(唐建平)、《愁空山》(郭文景)等作品。竹笛藝術已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僅以簡譜和口傳心授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訓練顯然無法滿足當今竹笛發展的需要。將五線譜這一世界通用記譜法列入教學范疇,無疑會對構建竹笛教學系統化、規范化及國際化等方面做出的有益貢獻。
一、竹笛演奏樂譜使用現狀
簡譜和五線譜幾乎均于近代進入中國。縱觀當今中國民族樂器所用樂譜,除古琴依然是減字譜與五線譜并存外,曾廣泛運用于民間音樂的“工尺譜”及運用于潮州音樂的“二四譜”幾近被簡譜所代替。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音樂具有單聲部、首調唱名法和轉調少等特點,而簡譜簡單易學,又與傳統音樂的首調唱法有共通之處,加之傳統器樂多數是由戲曲等聲樂伴奏樂器轉化而來的,便于一曲多調演奏。然而,以西方交響樂團體制為模板的民族交響樂團的建立,當代作曲家重奏、合奏、現代作品的創作、中西方音樂交融的需要以及打譜軟件的出現都使五線譜的學習成為必須。
目前,國內音樂院校、特別是地方院校,民族器樂專業教學中仍多以簡譜為主,甚至在合奏課訓練中也多用簡譜記譜。筆者以為,原因有二:1、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興起“新式學堂”,其中的“學堂樂歌”課直接效法日本的音樂教育,也沿襲了日本使用簡譜的做法。2、民族器樂在專業院校中設立專業教學學科,是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在藝術院校擔任專業教學的教師,大多是民間藝人或戲曲團體的演奏員,他們基本都以簡譜作為教學用譜。由民間藝人改編或創作的竹笛演奏曲也都是簡譜方式呈現。這無疑與當今社會需求產生了斷層。特別是在中國器樂與世界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掌握并熟練運用五線譜成為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加強五線譜應用,提升識譜能力
五線譜是一個嚴密而精確的記譜系統,而作為竹笛初級入門的學習者,能夠選擇的學習材料和樂譜卻不多。五線譜與簡譜之間缺乏教學上的銜接,理論與實踐不能結合,這不免有些尷尬。當下教學環境中要大量增加對于五線譜教學的實際運用。
從早年的由蔣詠荷先生于1956年編著的《笛子教材》到胡結續先生編著的《笛子吹奏法》于1965年9月出版,再到1983年由趙松庭先生編著的《笛藝春秋》也就是2001年再版的《笛子演奏技巧十講》三本權威的竹笛教材都為簡譜版本。到2000年后,市場中才陸續出現了以五線譜為記譜方式的教材,例:張維良先生編著的《竹笛教程五聲音階訓練》、《竹笛教程圓滑音訓練》與《竹笛教程氣息控制訓練六十首》、《竹笛基礎訓練裝飾音訓練》等,從簡譜到線譜的擴充及演變過程說明,了解和學習五線譜,是當今中國音樂教育與國際音樂教育交流背景下的必修課。在五線譜的訓練中,我們會發現:如以曲笛C調作為訓練,相當于從五線譜視奏的一個基本原調開始。同樣在C調上訓練,五線譜在變化音的記錄和調性轉化等方面顯得更為直觀。訓練過程中演奏者對五線譜在旋律、節奏、調式調性等音樂元素方面的體現也更加了解。
在教學過程中,筆者還嘗試借助傳統樂曲增加了五線譜的實踐運用。C調竹笛的唱名與五線譜中的固定調的唱名一樣,所以在實際運用中比較容易適應。五線譜中的音高低的圖形顯示更能夠直觀的判斷音樂旋律的走向,更易于音樂強弱變化和音樂動態表現及理解。(如圖1)

圖1
除C調竹笛以外的其他調式的竹笛在運用五線譜時需要通過系統的訓練,由淺入深的將首調唱名與固定調唱名間形成邏輯鏈接,熟悉不同調的竹笛在五線譜中的呈現方式,才能實現快速試譜的應用能力。以二人臺風格重奏曲樂曲《喜相逢》為例(如圖2)

圖2
以上圖2中重奏曲版本的《喜相逢》使用E調梆笛演奏,傳統首調的旋律唱名與五線譜中記錄的固定調唱名不同,但稍加讀譜訓練后,演奏者即可正確讀譜。
另外以上重奏作品中,五個聲部運用不同調的竹笛來演奏,通過用固定音高的記譜方式將不同聲部用一樣的標準音高來記譜,縱向形成和聲性,總譜讀譜才能成為可能。通過讀譜,聲部之間的音程關系、依次進入聲部之間的平衡關系等等都一目了然。
三、五線譜在竹笛當代作品中的記譜表述
五線譜可以準確地記錄樂曲的音高、節奏、速度、強弱等音樂要素,并且能夠在樂譜中直觀地顯示出了樂曲的旋律、調性、曲式,從而使演奏者可以直接、準確地掌握音樂本體。80年代后期新創作的眾多優秀的竹笛作品中,更多采用了五線譜的記譜方式,單一調性向多調性轉變、音樂風格也由單聲部向多聲部發展,樂曲更加突出和聲性,樂曲結構也更復雜。當然,眾多學者對于五線譜究竟是否適合民樂記譜也有眾多疑問,其中竹笛是否應該采用移調記譜法也有爭議。筆者認為,在五線譜中采用固定調記譜更有利于總譜讀譜,因為竹笛有很多支,不同調,如在重奏時同時運用,太多的移調記譜會造成讀譜困難,產生額外的復雜問題,上文已做過分析解釋就不再重述了。就現有作品來看,作曲家均采用固定調記譜法進行創作。
以下圖3是作曲家郭文景先生創作的竹笛重奏樂曲《竹枝詞》,樂曲分為三樂章,圖3為第三樂章《風竹》的部分。作曲家對于竹笛演奏技巧非常了解,譜寫的每個聲部都是竹笛中最易于演奏的部分,樂曲開始部分都是演奏E音,但每個聲部卻用不同調的笛子來演奏,這樣組合起來音高是一樣的,但音色是有不同的,增加了音色的豐富感,即統一又賦有微妙的變化,這是樂曲精妙的地方,其次聲部之間的交錯發展、節奏的對位是這首作品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同時也是難點之一。
在演奏此作品時需要看總譜演奏,而非分譜,這樣可以直觀的看到樂曲中隱藏著的律動關系,從而協調好三個聲部彼此的音響平衡。
圖4為樂曲98小節的部分,旋律線條是32分音符穿插于三個聲部中構成,同時在演奏中需要由慢至快,演奏者之間高度默契配合才能演奏下來。尤其是三個聲部之間隱藏著律動交替部分,所有的32分音符在三個聲部之間的緊密銜接。
除了五線譜在表現多聲部重奏樂曲中的優勢,在調性音樂中變化音的記錄也是簡單明了,圖5舉例作曲家關乃忠老師創作的協奏曲《蝴蝶夢》第一章中的主題部分,樂曲用D調曲笛來演奏,旋律的調性不斷轉換,升降號的運用使調性轉換變得十分簡單,這一點對于演奏者十分友好,同時對于作曲家來說也不必為零時的離調或移調作出額外的標注,樂思也不會受到記譜的局限。

圖5
在現代音樂中,作曲家設計的音響構建在樂譜中比較容易體現,以及區塊化的視覺感讓演奏者更能讀懂作曲家在音樂結構上的意圖。圖6、圖7(見第52頁)是美國作曲家霍夫曼先生為中國竹笛樂團創作的現代重奏樂曲《dizi in my life》的兩處事例,樂隊分為AB兩組,每一組分別有10位演奏家,另外再有主奏笛子和兩把大提琴構成。作曲家創作的手法也有別于傳統音樂,聽覺的感受與樂譜的視覺感緊密結合,對于演奏者來說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音樂的一種表述,由每一個聲部之間的交織形成整首樂曲中的素材之一,再又簡至繁再到簡的變化,對于這樣的創作意圖,演奏家通過樂譜就能夠一目了然。
“記譜法是一種符號體系,它通過各種符號向人們傳達著音樂信息。在文化交流日漸國際化的今日,一種記譜法僅供一種文化的局內人使用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被不同文化的人解讀、應用。”兩種樂譜的并存,既保留了傳統文化的歷史傳承。又體現了對外來音樂的兼修并蓄,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必然結果。

圖6為《dizi in my life》樂曲一開始的部分

圖7為《dizi in my life》樂曲第30小節
中國竹笛在新時代不斷地快速發展,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音樂需求與個人技術都在不斷地提升,前人總結的竹笛演奏技藝及理論也在不斷的更新。技術是表現內容的手段,當今掌握五線譜是演奏者的基本手段。樂譜作為記錄音樂的載體,隨著不同時代背景、不同的音樂需求也在不斷演變。竹笛樂曲創作理念從單一旋律性向多聲部和聲等復雜結構演變,五線譜的功能性更能滿足現代音樂創作中的需求,我們需要把簡譜和五線譜都能熟練掌握是當前的實際工作需求,本文希望能夠讓更多的竹笛學習者對五線譜的學習及運用引起一定的重視,也希望更多的專家老師創作更多的五線譜的訓練教材,愿更寬廣的音樂交流不再有語言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