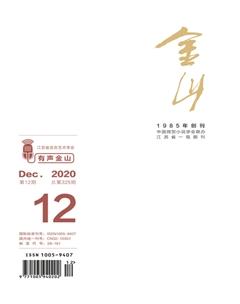一把米
丁運山
編者按:
我們在金山高級寫作班成立之初到現在,就一直堅持一個創作理念:深入觀察生活,從現實出發,絕不憑空編造情節。學員長期遵守,因此作品寫得扎實、豐滿。本期發表的小說,既體現了這一特色,題材豐富多彩,在情節的設置上又有了新的進步,新穎、巧妙、引人入勝。
平兒在家排行老三,屬老幺。鄉下有句俗話:辣的胡椒,疼的幺。這話無非就是說老幺在家受寵,惹人疼愛。
那年代窮人多,隔三差五總有人來村里挨家挨戶乞討。那時候平兒還小,也學著村里人把那些“乞討者”叫做“討飯的”或“叫花子”。娘不讓他那么叫,娘說那是對人不禮貌,無禮。娘還說:“討飯不為孬,只要不偷不搶,放下棍子一般高。”有幾戶人家養的狗很兇,見到那些“乞討者”連“汪汪”都懶得叫一聲,直接撲上去。平兒和娘見了,就撿起石塊朝那狗猛砸過去,狗就被嚇退了。
見討飯的到家門口,娘就會從廚房盛出一碗米飯,然后用筷子夾些菜蓋住,端出來遞到那可憐的人手中,催促對方趁熱吃。那些沒趕上飯點的,娘就會從米缸里抓出來一把米,塞進那用顫巍巍的雙手撐開的布袋里。
平兒有時候也責怪娘,說:“咱家的米也不是白來的。”娘就說:“五百年修得同船渡,別人走到家門口要說也算緣分,只當自己少吃那幾口。”平兒似懂非懂地看著娘,不再言語。
平兒記得那是個晴好的中午,天氣異常悶熱,家里剛收下碗筷,門口出現一位衣著破舊的老人。老人手里拄根木棍,胸前掛著一個縫補過的藍色舊布袋,一聲不吭,眼巴巴地立在那兒,像尊雕塑。娘當時正在切豬草,一時騰不出手來,就喊:“家里來客人了,趕緊出來吧,平兒!”
聽到娘喊,平兒心里便清楚是怎么回事。小跑著去廚房抓了一把米,而后慢吞吞走到老人跟前。老人用雙手來接,平兒抓米的那只手卻攥得緊緊的,指縫間的米粒還不時地往下掉。老人把掛在胸前的布袋撐開,平兒順勢將抓米的那只手塞進布袋,再松開。老人對著平兒咧咧嘴,又點了點頭,腰彎成了一張弓,顫顫地離去。
待老人走后,娘夸平兒懂事,長大了。還特意煮了個雞蛋給平兒,說是獎勵。平兒拿著熱乎乎的雞蛋放到鼻子跟前聞,又往空中扔,雙手接住再扔。幾個回合下來,一失手,“叭”的一聲,雞蛋趴地上摔癟了。平兒撿起來,噘起嘴“噓噓”吹了幾下,剝殼扒出蛋黃遞到娘嘴邊,娘推開他的手,他又把一塊蛋白往娘嘴里塞,娘把頭一扭,嗓子里瞬間像是被異物噎著。
平兒對娘神兮兮地說:“我有個小秘密,說出來你得替我保密。”
娘嬉笑道:“保密,保密。”
平兒又囑咐娘:“不許告訴任何人,一定。”
娘又說:“嗯,一定,一定!”
平兒還是有點放心不下,說:“拉勾。”
娘就伸出了小手指。那手指連同其他手指一樣,粗糙堅硬,如同茶樹根。拉完勾,娘就被平兒引到廚房。平兒揭開盛米的缸蓋,用一只手張開五指在娘的眼前晃了晃,然后攥緊拳頭往米缸里杵,還輕輕地扭動了一下,再抽出來,伸到娘的面前。平兒說:“下次再有客人來,我還這樣。”
娘頓時明白:那指縫中夾滿了白花花的米粒,待平兒將攥緊的拳頭展開時,掌心里卻空無一粒!
娘舉起巴掌在平兒頭頂上晃了下,劃了個弧,重重地落在自己的大腿上,嘴里喃喃低語道:“你咋能這樣,咋能這樣呢,這可不是一把米的事。”說罷,抓了滿滿兩把米裝進布袋里,然后急慌慌追趕老人去了。
娘回來已是后半晌了。平兒看到娘的上衣已被汗水濕透,頭發披散著,冷不丁一看,像是個叫花子。
娘說:“我攆了兩個村才找到那老人。”
平兒有些愧疚:“娘,今后我改。”
“知道錯了就好。” 娘把平兒攬在懷里,輕輕撫摸著他的頭發。
許多年后,平兒記得娘都走了五周年,村里來了一個年輕人,用自行車馱了一袋大米,說當初多虧了一位大娘……他是來感恩的。
平兒沒承認,村里也沒人承認。
點評:
小說的主線分明:通過“一把米”寫出人間的大愛。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卻有樸實無華的真情。特別是,同時刻畫出兩個人物,平兒和她的母親。通過具體的物品和細節來刻畫人物,給讀者留下清晰的印象,是這篇小說很突出的特點。小說敘述真實,語言質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