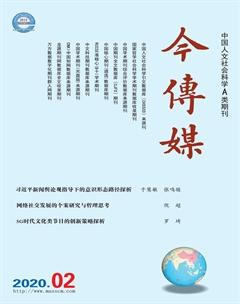“無用階級”之辯:人工智能與新聞業的未來
冉玲琳
摘?要:“紙媒已死”,新聞業進入“智媒時代”。從機器人寫作到個性化的新聞推送,“新聞編輯室 ”的位置已經所剩無幾,人工智能開始在新聞業內產生“無用階級”并重塑其人員結構。新技術帶來了新危機,機進人退的現象越來越明顯。新聞業是應該“功利主義”的擁抱新技術還是與之繼續“競爭”,哪一個會讓新聞業變得更好?本文旨從莊子“無用之用”的倫理哲學角度探討人工智能與新聞業的未來,思考新聞業在人工智能“暗涌”中的堅守和改變。
關鍵詞:人工智能;“無用階級”;技術倫理;“無用之用”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20)02-0013-03
《未來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曾公開表明:“新技術帶來的一個危機:一些人會被升級為超級人類,而其他人甚至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將會成為‘無用階級,他們將面臨失業危機,人工智能將輕而易舉的取代他們的工作”[1]。以大數據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成熟,無人機新聞采集、機器人寫作、算法推薦等技術已廣泛地應用于新聞業務流程的采、寫、編、評等環節,人工智能技術已滲透新聞業的方方面面。彭蘭教授預見性地提出:“新聞業正處在‘智媒時代的黎明,一個‘極度擴張的傳媒業新版圖也將會在新的角逐中形成”[2] 。
一、“無用階級”誕生:新聞業從哪里開始變革??2017年10月25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舉行的“未來投資倡議”大會上,女性仿真機器人“索菲亞”成為世界上首個被賦予公民權的機器人。在大會上,主播詢問“索菲亞”:“你知道自己是機器人嗎?”此問題遭到索菲亞的反問:“你又怎么知道自己是一個人類?”這一對話,無疑對當時觀看直播的人產生了不小的心理沖擊。在此之前,圍棋高手“AlphaGo”、機器人記者“小明”等智能機器人的出現已經刷新了“人類”的認知。
自工業時代起,機器就開始取代人類的“體力”,隨著網絡技術的提高,機器又把目標轉向人類的“腦力”上。智能機器“深度學習”,語音識別讓萬物“開口說話”,不僅如此,機器還可以用人類的眼光去閱讀文獻、書籍。人工智能不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各行各業締造的機器人數量也在不斷攀升,同時,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倫理問題也不斷涌現。
就機器人“索菲婭”來說。目前,她的“大腦”已經能利用語音識別技術,識別人類面部,并理解人類的語言。她擁有自己的意識、學習能力以及情感。最重要的是,她擁有了合法的公民權利。在未來,發明者打算將“索菲婭們”使用于人類的日常生活當中。然而,已經擁有公民權的“她們”真的甘愿為人類所用嗎?人類又該以何種態度對待這樣的“同事”呢?
二、“用”與“無用”: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辨
“圍棋人機大戰”拉開了人工智能的序幕,算法、深度學習技術在新聞業“大展拳腳”。智能無人機信息采集、機器人新聞寫作、大數據信息抓取、算法分發和推送……在繁忙的新聞編輯室里,一股“暗流”正洶涌襲來。這股“暗流”引發了新聞業內學者們的暴風討論。陳昌鳳提出:新聞業的再次崛起,必須依賴智能化等新科技與內容的融合[3]。韓婷認為:人機協同編輯將成為未來主要的新聞生產形態[4]。彭蘭提出:在機器時代,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技術倫理與法規的約束[5]。
新聞業該如何對待人工智能?說到底,就是人類該如何對待不斷發展的“新事物”的哲學問題。早在1 000年以前,莊子就對不斷發展的“外物”進行過剖析。莊子認為人對于物的態度是由人對外物的定義來決定的,他將對物的態度分為三種:“有用之用”“無用之用”以及“無用”之上。
莊子認為人必須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物,必須區分物的“有用”與“無用”。倘若其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實現它的具體功用價值,就是“有用之用”。在此基礎上,人還要突破“有用之用”的局限性,看到物的不斷變幻和發展的一面。除了了解物的“有用之用”之外,還要推測物的“無用之用”。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萬事萬物與人皆平等,人不能以“用”的狹隘眼光去看待每件物,人首先應該學會掌握運用物的技能,而不是將眼光只局限于物的“有用”和“無用”之上。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提高,未來的新聞業將會更加智能化。如何區分人工智能的“有用”與“無用”,把人工智能技術用在何處,其中的“度”如何把握。這些問題對于新聞業來說,都將會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有用之用”:從智能無人機開始
2015年5月,全球視頻輸出領導者TVU Networks和無人機制造商DJI宣布聯合推出“Aerial Newsgathering Pack”(智能航拍采集包)。這款智能航拍器為媒體平臺視頻輸出打造了集新聞素材采集、視頻輸出為一體的素材采集鏈。
目前,運用智能無人機收集素材已成為普遍趨勢。從2015年“新聞航拍采集包”誕生以來,美聯社、《紐約時報》、CNN等媒體平臺,已實現全程無人機航拍的自動化采集。與傳統的地面拍攝相比,智能無人機更加安全快捷,可以突破空間、地形環境等限制。
目前,智能無人機被運用到我國新聞業的縣級、市級、中央級媒體的新聞素材采集、整合等業務環節。未來,素材采集會更加智能化,新聞制作者可以和無人機產生對話,通過交流讓無人機拍攝出完美的新聞產品。在此之前,新聞素材采集主要依靠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智能無人機的出現無疑取代了部分基礎、高危的工作,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智能機器人進入新聞業正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之一。
(二)“無用之用”:機器人寫作讓新聞業顫抖??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溝發生地震,中國地震臺的“地震播報機器人”迅速推送了一篇題為《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地震》的新聞稿。這篇稿件由智能機器人獨立完成,共用時25秒,全文共585字。
新聞業運用智能機器人進行新聞寫作已屢見不鮮。美聯社在2014年7月就開啟了機器人新聞寫作的先河。2015年9月,騰訊也首次嘗試運用機器人發布財經類新聞稿件。
目前,機器人寫作主要應用于以數據為核心的新聞報道,例如,體育新聞、財經新聞、交通預測新聞等。這類新聞報道的體裁固定,由程序員設計智能程序自動生成新聞稿件并定時發布。這種智能機器人能減輕記者的工作壓力,取代記者部分復雜、常規、基礎的數據分析工作。
就目前來看,“機器人新聞”雖不能完全取代職業的新聞記者,但其已經顛覆了人們對記者和編輯的傳統認知。特別是在機器新聞寫作應用越來越廣泛的當下,智能機器人在新聞業務上已有了“人”的意識之后,以何種“用”的態度對機器人寫作將會是未來新聞業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
(三)“無用”:算法的個性圈套
進入“眾媒”時代以來,智能手機實現全民普及,人們閱讀新聞的習慣和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交媒體的交互式、鑲嵌式傳播方式也讓信息傳播從單向轉向雙向、社交式傳播。借助于機器學習、產品數據抓取、用戶調查等技術,社交平臺為用戶打造了完美的“個性化”新聞推薦模式,給用戶推薦只屬于他們的新鮮事。
由于平臺的社交特性,其平臺會從后臺抓取用戶數據,例如,用戶的點贊、評論、屏蔽關鍵詞等指標來記錄用戶的新聞閱讀興趣、使用時間等,從而精準地為用戶推薦“他喜歡的新鮮事”。隨后,廣告商運用這些信息,為其匹配“他感興趣的東西”,以達到滿足用戶獲取“最喜愛新聞”的訴求。
這種“大數據+算法”的內容推薦模式,主要從用戶的閱讀習慣入手,讓平臺可以第一時間獲得用戶反饋,再根據閱讀量了解受眾對于新聞的反應。但對于受眾來說,這種推薦機制看似為受眾篩選出了最完美的信息,實則是技術的一個明顯弊端,其讓受眾失去“選擇”和“思辨”的能力,形成信息繭房效應,長此以往,用戶便會由主動變被動,失去“選擇”的機會。
三、人機共舞:新聞業的未來
如今,成熟的無人機航拍技術保障了記者的安全風險,機器人寫作變革了新聞報道的編寫模式,算法也讓“私人定制新聞”成為可能。從新聞生產、新聞分發機制到用戶體驗,無疑不表明,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新聞業。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預示著新聞業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未來,新聞業與人工智能想要實現“人機共舞”的穩定局面,勢必要做一些改變。
(一)明確新聞人的價值
廣播和電視的全面普及,重塑了紙媒時代的傳播格局。此時此刻,人工智能正重組著新聞業的傳播流程。對于新時代的記者、編輯而言,了解人工智能并熟練的使用人工智能,讓人工智能與自己的工作結合,習慣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更新帶來的新變化才是改變的第一步。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機器會在新聞業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與各種新聞業務流程的結合也將帶來整個新聞業的重大轉變,未來的新聞業將是人機協同完成報道內容與形式的制作、傳播和反饋。因此,新聞業想要實現“人機協同的趨勢”,必須強化“人才是機器的主宰”的觀點,明確人的價值。
(二)細化新聞專業主義
托斯在《人工智能時代》對未來進行過展望:在人工智能時代,有固定的AI基站或到處行走的機器人取代人類的大部分工作。但有幾類工作卻依舊被需要,如警察、教師、醫生等具有經驗性質的專業工作。所謂的專業人才,一般是指在某個或者多個領域擁有專業知識、受過相關專業訓練的人。然而,隨著云計算、物聯網技術的提高,很多以往的專業工作可以被一臺智能機器人取代,如銀行的證劵分析師。因此,新聞業內的許多“專業工作”也不得不進行再細分。在教育領域,減少培養可以被取代的專業人數,并制定更精細的人才培養方案。在媒體實踐中,要更加注重對人才邏輯和思維能力的培養,如重視深度報道、深度調查。
(三)培養新聞業的“超級人類”
目前,人工智能已經可以進行簡單的新聞數據處理、歸納、分析工作。結合程序設定的寫作模板,機器人可以快速完成并及時發布多篇相關報道。當下,人類對人工智能的一個展望是讓其代替人類完成一些高危、高難度的工作,但更加復雜的工作仍要人類完成。如事件發生后,當事人的情緒、情感狀態的識別;深度調查報道中事件的原因、背景、事件走向;經濟報道中人類的利益糾葛,隱藏在背后的各種真相等機器無法進行分析和處理。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新聞專業人員也必須“進化”,成為“超級人類”。
四、結?語
新聞業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新聞業內的“無用階級”已經初見端倪。新聞業想要實現“人機共舞”走向更加繁榮的局面,立即改變是更好的選擇。面對逐漸智能化的新聞業,新聞人應該要收斂掌握偏向于規則開發和發現探索的工作,新聞人應該從更瑣碎的工作中抽離出來。而人工智能的最大意義則應該是讓人擺脫世俗和繁瑣生活的束縛,讓人類完全投身于創造性的工作中去。
參考文獻:
[1]?(以色列)瓦爾·赫拉利著.林俊宏譯.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9-90.
[2]?彭蘭.未來的“智媒時代”什么樣[J].決策探索,2017(3).
[3]?陳昌鳳.人機大戰時代,媒體人價值何在[J].新聞與寫作,2016(4):45-48.
[4]?韓婷.試論人工智能視閾下新聞業的未來發展路徑[J].東南傳播,2019(1):7-9.
[5]?彭蘭.機器與算法的流行時代,人該怎么辦[J].新聞與寫作,2016(12):25-28.
[6]?徐峰,彭蘭.未來媒體發展趨勢是“萬物皆媒”[J].新聞論壇,2015(6):40-43.
[7]?彭蘭.從眾媒到智媒在機器時代守望人的價值[J].今傳媒,2019,27(2):85.
[8]?彭蘭.更好的新聞業,還是更壞的新聞業?——人工智能時代傳媒業的新挑戰[J].中國出版,2017(24):3-8.
[9]?郝勇勝.對人工智能研究的哲學反思[D].太原科技大學,2012.
[10]?(美)杰瑞·卡普蘭著.李盼譯.人工智能時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11]?高利民.莊子無用之用的另一種解讀[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105-112.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