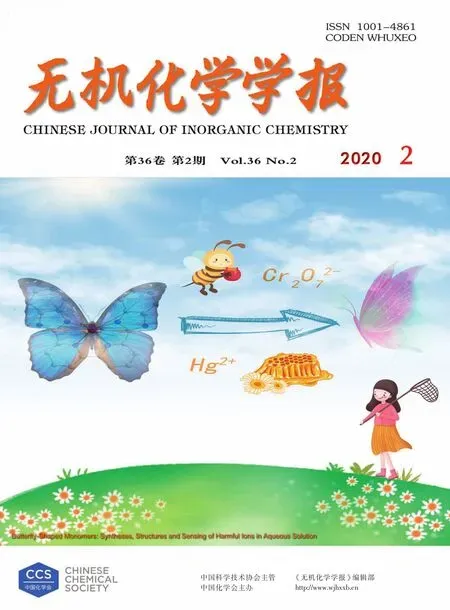碳纖維表面羰基鐵的原位生長及吸波性能
劉 淵賈 瑛 李 茸
(火箭軍工程大學作戰保障學院,西安 710025)
碳纖維(CF)是功能與結構一體化的優良吸收劑,具有質輕、硬度高、高溫強度大及耐腐蝕等特點,是當今碳系吸收劑研究的重要支撐[1]。然而,CF不具有磁性,單獨使用時存在阻抗匹配特性較差、吸收頻帶窄等缺點。為了進一步改善其性能,增加其對電磁波的吸收能力,使其優異的力學、電學性能得到充分發揮,通常將其與磁性吸收劑復合制成磁性復合吸收劑[2-5]。這些復合吸收劑中,在碳材料表面包覆 Ni、Co等磁性金屬吸收劑制備成核殼結構復合吸收劑[2,4,6],是目前值得關注的熱點研究方向。
性能互補的不同種類吸收劑之間的復合是當前改善吸波性能的有效手段之一[7-9]。核殼型磁性吸收劑由于獨特的結構和可設計性可使材料具備協同性,近年來成為研究的熱點[10]。在眾多的磁性金屬吸收劑當中,羰基鐵粉(CI)的吸波性能是公認最為突出的。采用質輕的碳纖維,在其表面包覆羰基鐵,從而實現兩者之間性能的取長補短,一方面可使碳材料吸收劑具有磁損耗,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密度小于羰基鐵的復合粉體,從而有望得到替代純CI吸收劑的理想輕質復合吸收劑。
為了實現該類型核殼粉體的規模化制備及其在吸波材料領域中的實用,我們利用金屬有機化學氣相沉積(MOCVD)工藝在碳纖維表面原位生長納米羰基鐵殼層,并對MOCVD工藝中沉積溫度對核殼形貌及吸波性能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研究。通過改變沉積溫度,在微納米尺度下調控核殼粉體的形貌結構,從而有序調控吸波性能,最終優選出最優的沉積溫度和具有最佳吸波性能的復合粉體。
1 實驗部分
1.1 樣品制備
1.1.1 試驗原料
碳纖維為日本產T300-1k(單絲直徑6.5 μm,每束1 000根),由江蘇森友公司提供。試驗用Fe(CO)5由陜西興化羰基鐵粉廠生產,純度99.9%;市售N2的純度為99.99%;濃硝酸(分析純,d=1.37 g·mL-1),西安化學試劑廠;濃硫酸(分析純,d=1.84 g·mL-1),西安化學試劑廠;氫氧化鈉(分析純),西安三浦精細化工廠。
1.1.2 碳纖維的預處理
對碳纖維進行如下處理:(1)去膠除油。在真空管式爐內N2氛圍保護下,灼燒溫度420℃,灼燒時間25 min。然后將高溫灼燒后的碳纖維置于濃度為10%的NaOH溶液中浸泡5 min以除去碳纖維表面的油漬;(2)粗化。在室溫條件下,將HNO3(d=1.37 g·mL-1)和 H2SO4(d=1.84 g·mL-1)按照體積比 1∶1 混合后,投入碳纖維,粗化時間控制在10 min。(3)中和水洗。將經粗化處理后的碳纖維放入10%的NaOH溶液中,在室溫下浸泡3 min,以中和方法去除粗化時殘留在其表面上的酸根離子。取出后用去離子水進行清洗,然后置于恒溫干燥箱內烘干待用(60℃)。
1.1.3 MOCVD工藝步驟
將1 g預處理后的CF分散纏繞在支架上和15 mL五羰基鐵[Fe(CO)5]分別加入到反應器和蒸發器中,接通N2,將管路中的空氣全部吹出,關閉氣源,同時關閉反應器和蒸發器之間的閥門。將Fe(CO)5加熱到80℃,同時將CF加熱到預設溫度(180、210、240及270℃)后,打開反應器和蒸發器之間的閥門,同時氮氣源以30 mL·min-1的流量將Fe(CO)5蒸氣吹入到反應器中。N2的流量大小通過氣體流量計控制;Fe(CO)5采用HH-SA數顯恒溫油浴鍋加熱,氣態Fe(CO)5進入反應器之前的管路都包覆有一層保溫套,防止氣態的Fe(CO)5在低溫處凝結,造成管路不暢。Fe(CO)5蒸氣吹入時間為30 min,最后樣品在N2保護下冷卻、收集。
1.2 粉體表征
采用Rigaku D/max-2400X型射線衍射儀(XRD)進行物相分析(Cu靶,Kα射線,λ=0.154 18 nm,靶電壓 40 kV,靶電流 100 mA,步進掃描,步長 0.02°,掃描速率 15°·min-1,掃描范圍 15°~80°);使用 VEGA膊XMUINCN型掃描電子顯微鏡(SEM)研究碳纖維表面及截面膜層形貌;使用HP8720ES型矢量網絡分析儀(VAN),用同軸法測量電磁參數。
電磁參數測試樣品的制備過程如下:分別稱量所需的基體石蠟和吸收劑(質量分數為4%),將吸收劑加入到熔融的石蠟中并充分攪拌,冷卻后用研缽研磨,再熔融攪拌,冷卻研磨,以上步驟反復3~4次,以使吸收劑與石蠟均勻混合;再加入適量酒精,在高速乳化機中剪切分散,然后蒸干研磨成粉末,壓制成外徑為7 mm、內徑為3 mm、長度為2~5 mm的圓形同軸試樣。
2 結果與討論
2.1 碳纖維-羰基鐵樣品形貌結構分析
圖1為CF及不同沉積溫度下(180、210、240、270℃)樣品的形貌分析SEM圖和XRD圖,圖1(b)、(c)、(d)和(e)中插圖為不同沉積溫度CF-CI復合粉體的截面SEM圖。由圖1(a)可見,CF經過預處理后表面有少量的凹槽,粗糙度增大,有利于后續CI的沉積。由圖1(b)可見,當沉積溫度過低時(180℃),CF表面僅見離散細小的CI顆粒,未形成完整的核殼結構,此時樣品 XRD 圖(見圖1(f))顯示 2θ在 20°~30°范圍內有一個明顯的“饅頭峰”,為C(002)晶面的衍射峰,衍射峰寬化,說明沉積到CF表面的CI較少;在2θ=44.6°左右出現了明顯的α-Fe特征峰,生長方向為(110)。沉積溫度為210~240℃時,CI沉積薄膜均勻完整地覆蓋在CF表面,連續致密、沒有裂紋等缺陷(圖1(c)和圖1(d)),α-Fe(110)晶面取向生長明顯增強,C(002)晶面衍射峰逐漸減弱,由截面SEM分析可見,此時形成了完整的薄膜包覆型核殼結構。由圖1(e)可見,隨著溫度的升高(270℃),沉積的CI顆粒呈球狀或瘤狀大顆粒,涂層表面顯得很粗糙并且出現裂紋,易使膜層開裂,脫落。綜合分析,沉積溫度不宜高于240℃。
Fe(CO)5氣相分解沉積羰基鐵殼層的過程中包含了新相的形成,必然會引起反應體系自由能的變化[11-12]。本節借助晶體形核-長大理論,結合熱力學分析,主要研究沉積溫度與臨界核心半徑(rc)、臨界形核自由能(ΔG*)以及形核速率(I)的關系,從理論上分析沉積溫度對羰基鐵殼層微觀形貌的影響。

圖1 CF及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核殼粉體的SEM圖和XRD圖Fig.1 SEM and XRD diagrams of CF and CF-CI core-shell powders at different deposition temperatures

當r<rc時,形成的新相核心處于不穩定狀態,可能再次消失,當r>rc時,新相核心將處于可以繼續穩定生長的狀態,生長過程將使自由能下降,當r=rc時,ΔG*為:

隨溫度的改變,相變自由能ΔGv和新相表面能γ的變化是rc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由于殼層核心的成長要有一定的過冷度,即溫度一定要低于涂層核心與其氣相保持平衡時的溫度Tg,令ΔT=Tg-T為涂層沉積時的過冷度,則溫度與S有如下關系式:

式中z為常數。由(3)和(7)可知,隨著沉積溫度上升,ΔGv的值將降低,使得新相rc增加。由(8)可知,隨著沉積溫度升高,I呈現出增加的趨勢。因此,在MOCVD制備羰基鐵包覆式核殼粉體的過程中,沉積溫度過高,羰基鐵晶粒長大迅速,呈球狀或瘤狀,進而形成粗大的島狀組織,使得沉積的羰基鐵殼層表面形貌結構變差。低溫沉積有利于形成晶粒細小而連續的羰基鐵殼層,這主要是由于此時相變過冷度大,rc和ΔG*下降,臨界形核速率加快,形成的核心數目增加,所以沉積的羰基鐵殼層會相對光滑平整。但是,沉積溫度不能太低,否則活化分子太少導致反應速率太慢,臨界核心半徑太小導致晶粒長大的速度很慢,短時間內羰基鐵顆粒之間無法完成形核、長大、成膜的過程,將無法形成連續的羰基鐵殼層。
2.2 碳纖維-羰基鐵樣品磁性能分析
圖2為CF-CI核殼粉體的磁滯回線。由圖可見,與CI復合后,CF-CI顯示出CI所具有的鐵磁性。隨著沉積溫度的升高,復合材料的飽和磁化強度Ms隨之先增大后減小。沉積溫度為240℃時,CF-CI核殼粉體具有最大的 Ms,達到 44.34 emu·g-1。
2.3 碳纖維-羰基鐵樣品電磁參數分析
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復合粉體的ε′和ε″在2~18 GHz頻段的變化如圖3(a)和圖3(b)所示。從圖3(a)和圖3(b)可以看出,CF表面生長CI薄膜后對其介電常數的變化有明顯影響。CF-CI核殼粉體的ε′在測試頻段內明顯大于CF的ε′,并且隨著沉積溫度的升高而增大;與CF的ε″相比,CF-CI核殼粉體在10 GHz處的峰值消失,在整個測試頻段呈現下降趨勢。這是由于,在CF表面沉積納米CI殼層后,增強了樣品的界面極化,增大了樣品的電導率,從而使 CF-CI復合粉體的 ε′和 ε″發生了改變[14]。

圖3 CF和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核殼粉體的介電常數(a,b)和磁導率(c,d)Fig.3 Permittivity(a,b)and permeability(c,d)of CF and CF-CI core-shell powders at different deposition temperatures
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復合粉體的μ′和μ″在2~18 GHz頻段的變化如圖3(c)和圖3(d)。μ′和 μ″呈多重共振現象,并隨著沉積溫度的增加而呈現出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μ′隨著頻率增加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在11和16~GHz附近存在明顯的峰值,而μ″數值分布在9和14 GHz附近出現明顯峰值。吸收劑在微波頻段的磁損耗主要來源于渦流損耗、自然共振和磁疇壁共振[15-16]。在微納米尺度下,磁疇壁共振產生的損耗會很小[17]。因此,CF-CI核殼復合粉體對電磁波的損耗主要由自然共振和渦流損耗引起。渦流損耗依賴于材料的厚度(d)和電導率(σ),表達式為[15]:
μ″(μ′)-2f-1≈πμ0d2σ

圖4 CF-CI復合粉體的 f-1(μ′)-2μ″值與頻率 f的關系圖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f-1(μ′)-2μ″value and frequency f of CF-CI composite powders
其中μ0為真空磁導率。如果CF-CI的磁損耗主要由渦流損耗引起,f-1(μ′)-2μ″的數值應該是個常數。圖4為CF-CI復合粉體的 f-1(μ′)-2μ″值與頻率 f的關系圖。可見,在2~18 GHz內,隨著頻率的升高,其數值呈現出波動變化,因此可以得出CF-CI的磁損耗以自然共振為主,渦流損耗為輔。
2.4 碳纖維-羰基鐵樣品吸波性能分析
CF及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樣品的吸波性能與頻率和厚度的關系,如圖5所示。單純的CF匹配厚度在4.0 mm以上(圖5(a))。CF表面生長CI薄膜后,吸波能力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不同沉積溫度下制備的樣品具有多個匹配點。隨著沉積溫度的增加,樣品的吸波性能先改善隨后惡化,沉積溫度為240℃的樣品具有最佳的吸波性能。電磁波在導電性較好的材料中傳播時,隨著頻率越高,傳輸距離就越短,這種現象稱為趨膚效應,通常用趨膚深度(δ)來表征[18]:

隨著溫度的升高,沉積到CF表面的CI呈現增多趨勢(如圖1所示),其電阻率相應呈現出變小趨勢,在微波頻段使用時,其趨膚深度也會逐漸減小,從而導致吸波性能受到趨膚效應的影響而惡化。另一方面,介電常數隨著沉積在CF表面的CI的增加而增大(如圖3(a)),同樣會影響樣品與自由空間之間的阻抗匹配。

圖5 CF和不同沉積溫度下CF-CI核殼粉體的吸波性能與頻率和厚度的關系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and thickness of CF and CF-CI core-shell powders at different deposition temperatures
根據電磁波傳輸線理論[18-19],當頻率為f的均勻平面電磁波垂直射入底層為金屬板的單層吸波涂層時,涂層對電磁波的功率反射率R為[20-21]:

式中,Z0=(μ0/ε0)1/2=120π為空氣阻抗,Z為材料的輸入阻抗。

式中,μr=μr′-jμr″為相對磁導率,εr=εr′-jεr″為相對介電常數;為材料的特征阻抗;γ=j2πf為電磁波在材料中的傳播常數;d為材料厚度。
結合沉積溫度為240℃時所獲樣品的電磁參數,由式(9)和(10)計算了厚度為0.9~3.9 mm之間的反射率,如圖6所示。隨著厚度的增加,反射率峰值先減少后增加,逐漸向低頻移動。厚度為0.9 mm時,吸波帶寬(<-10 dB)最大為4.6 GHz,在厚度為2.0 mm時,反射率達到最小值為-21.5 dB。涂層厚度為0.9~3.9 mm時,在2~18 GHz均能實現吸波強度低于-10 dB。

圖6 不同厚度下CF-CI核殼粉體(240℃)的吸波性能Fig.6 Microwave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CF-CI Core-Shell powders(240℃)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3 結 論
在微米級CF表面成功原位生長了CI殼層,得到了CF-CI核殼結構復合吸收劑,利用XRD、SEM及VNA等分析手段,重點研究了沉積溫度對CF-CI鐵核殼粉體微觀形貌、晶體結構、電磁參數及吸波性能的影響,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沉積溫度為180℃時,在CF表面原位生長的羰基鐵顆粒較少,復合粉體呈粒子包覆型核殼結構;隨著沉積溫度升高(210~240℃),沉積到CF表面的羰基鐵顆粒互相“吞并-融合”,此時CF-CI形成了完整的薄膜包覆型核殼結構。沉積溫度太高時(270℃)會造成CF表面羰基鐵殼層形貌的惡化。
(2)在CF表面原位生長納米羰基鐵顆粒后,由于核殼結構增強了樣品的界面極化,同時引入以自然共振為主的磁損耗,明顯改善了CF的電磁性能。
(3)沉積溫度為240℃,CF-CI核殼結構復合粉體具有最佳核殼形貌及吸波性能。結合測試所得的電磁參數優化設計可知,涂層厚度為0.9 mm時,小于-10 dB的吸波帶寬最大為4.6 GHz(13.4~18 GHz);涂層厚度為2.0 mm時,反射率達到最小值為-21.5 dB;厚度為0.9~3.9 mm 時,在 2~18 GHz均能實現吸波強度低于-10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