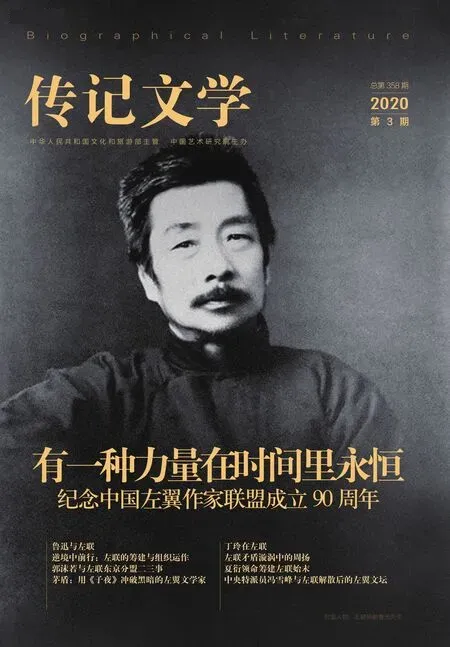為明國粹大道 不惜繼晷焚膏
——我的戲曲研究之路
安 葵 口述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
李志遠 整理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
安葵先生,本名王安奎,亦作王安魁,筆名安葵,1939年6月出生于遼寧省蓋州市。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昆劇研究會副會長、《戲曲研究》主編、《中華戲曲》主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安葵先生堅持理論聯系實踐的學術理念,時刻關注戲曲創作實踐的發展,對作品、劇作家、創作現象的研究貫穿始終,同時致力于當代戲曲理論體系建設,并在戲曲美學領域進行了不懈的研究。2020年春節期間,80歲高齡的安葵先生向我們講述了他的戲曲研究之路。
因熱愛文學 與戲曲結緣
我出生在遼寧省蓋州市(原來叫蓋縣)的一個小山村,那里有一個老壽星山,老壽星山下就是頭道溝村。祖父王文林中過秀才,但沒有再“進步”,只在農村教書,并且家境越來越貧窮。我沒有見過祖父,我出生時他早就去世了,但我看過他留下的一箱線裝書。父親王肇遠弟兄四人,他行大,只念過幾年私塾,很小就務農。山里沒有多少耕地,父親主要侍弄果樹,房前屋后嫁接了多種水果樹。我的家鄉很美!一到春天,山坡上就紅紅火火開遍了映山紅,一團團、一簇簇,遠看像燃燒著的火焰。映山紅謝了,便有杏花、桃花、梨花、蘋果花等開放,這些花謝了,赤、橙、黃、綠各種顏色的果子掛滿枝頭,那是父親勞動的結晶。我有兩個哥哥、四個姐姐,他們都很聰明好學,但沒有條件多讀書,哥哥們很小就外出工作,三個姐姐都早早嫁人,四姐讀了師范,加上勤奮自學,成為一名優秀的高中教師。我讀書時新中國已建立,家里生活條件好了,因此得以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父母在家里辛勤勞動,上中學后兩位哥哥負責了我的生活費用,姐姐們對我也非常關心,因此我永遠感恩父母和哥哥姐姐們。我的小學離家五六里路,天不亮就要去上學,母親每天都站在院墻邊看我走遠,直到看不見為止。中學則是到四五十里以外的熊岳城蓋縣第二中學住校,高中是在熊岳高中。
我走上戲曲研究之路有一定的偶然性。從小沒有看過戲曲演出,對戲曲也不了解。從小學到中學,我的各門功課是“全面發展”的,考初中時是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入的,還成了三里五村的大新聞。但我更喜歡文學,小學時寫作文,宋慶鴻老師曾寫批語:“有造之才,勉之勉之。”這對我是很大的激勵。中學時期,夏鴻明、郭增益、宮鳳閣等語文老師水平都很高,學校也都有很濃的文學氣氛。初中時學校有一份《學習生活》油印小報。開始是蘇芳桂做主編,發表了我不少小文。蘇芳桂畢業后(他后來到了廣東惠州,是優秀的小說家),我接任了主編。高中時,宮鳳閣老師曾出作文題:寫杜甫《兵車行》的評論,把古詩《十五從軍征》改寫成新詩的形式等,都激發了我評論和創作的熱情。還曾聽蓋縣的劇作家田心上(本名由志正,遼寧著名劇作家)在文化館的講座,因此便萌生了當作家的夢想。1960年,我高中畢業的時候,藝術院校提前招生,一些喜歡文學的同學就相約報考了中央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兩院校聯合招生)。說起來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東北地區是在沈陽集中考試的。復試時中央戲劇學院的克瑩老師問我:“你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嗎?你讀過莫里哀的劇本嗎?”我都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她說:“入學后得多讀一些書啊!”這似乎是一顆定心丸。不久,我就接到了中國戲曲學院戲曲文學系的錄取通知書。
那時的中國戲曲學院是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組建的,一個單位掛兩塊牌子。地址在東四八條52號。開始國務院任命張庚為中國戲曲學院院長,后來撤銷中國戲曲研究院,合并到中國戲曲學院,院長是梅蘭芳,副院長是張庚、晏甬、羅合如。在“大躍進”之后,國家實行調整政策,許多高等院校被撤銷。中國戲曲學院的牌子又被摘掉,恢復中國戲曲研究院建制。我們也提前于1963年畢業,叫作“實習在外”。我們是“文革”前唯一的一批正式的戲曲專業的大學生。
開學時,梅蘭芳院長和張庚先生都對同學們講過話,不久張庚先生下放到江蘇沛縣,教學工作主要由晏甬副院長負責。張庚、晏甬提出按延安魯藝精神辦學,進行學院式教學。戲曲文學系系主任是郭漢城先生,副主任是張為先生,先后擔任我們班主任的有王彤、吳瓊、簡慧等老師。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大部分是本院的研究人員:吳瓊、簡慧、王芷章、劉念茲、林涵表、王淑蘭、余從、黃菊盛、李振玉、鄧興器等,并請了外面許多專家來講課。郭漢城先生給我們講過一次話,內容大多不記得了,只記得他說,你們要“多讀書,少生氣”,當時很不理解,并且覺得挺奇怪,后來漸漸覺得這句話,特別是對于年輕人,是很有深意的。老師們認真負責地進行教學。吳瓊老師指導我們寫劇本,劉念茲老師用“箋注”的方式講《牡丹亭》,簡慧老師細致地解析《雷雨》《梁山伯與祝英臺》等戲劇名著。記得學習期間曾到雙橋農場參觀,回來后同學們寫詩,我寫的一首“五律”的頭兩句是:“農村舊印象,今日一掃光”,王芷章老師給我改為“農場陳印象,今日掃來光”。使我開始意識到寫詩需調整用字以符合平仄規律。讀書期間正值國家開放傳統劇目的演出,因此得以觀摩了京劇和各地方戲的許多優秀傳統劇目,使我的文學夢與戲曲藝術逐步結合了起來。我曾擔任班干部、團支書,還擔負著輔導3 個越南留學生學習的任務。同學相處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這里不能一一盡述了。畢業前,班里的調干同學王登山、張巧蘭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晏甬副院長參加了我的入黨討論會,講了很多語重心長的話,同志們也都對我提出了殷切的期望,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1963年畢業后,我留在中國戲曲研究院劇目室工作。秋天,我與譚志湘、蘇明慈等青年同志(后來鄧興器也加入)被安排到山西“學毛著”先進典型地區絳縣南柳村和昔陽大寨去“勞動鍛煉,體驗生活”。臨行前晏甬副院長與我們談話時說:“勞動鍛煉很重要,也要強調體驗生活。你們趁年輕時要好好體驗生活,為今后的創作打下扎實的基礎。”在農村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很愉快。我從小就參加勞動,上中學后,假期也與鄉親一起干活。在家里干活時,父親常說我笨,到農村卻常常得到寬厚的鄉親們的稱贊。老鄉們不但有豐富的生產知識、自然知識,而且能講出很多人生的哲理。這一年的春節沒有回北京,在絳縣過的“革命化的春節”。1964年京劇現代戲會演期間,我到北京觀摩會演,之后又返回南柳。當年冬天河北發洪水,水災過后,文化部布置寫抗洪劇本的任務。我隨郭漢城先生等人到河北、天津等地采訪了一段時間,回來后我先寫劇本初稿。初稿寫成后,又有新的任務來了。領導說,劇本放一放,先搞“四清”去。于是,我們先后到北京郊區樓梓莊、延慶和河北邢臺等地搞“四清”。在南柳,我還擔任了生產隊的副指導員,“四清”時擔任過副隊長。在這些農村工作中,我與當地的農民結下很深的感情,對農民的生活有了更多切身體會,也向他們學習到很多東西。接著就是1969年秋天開始,下放到“五七”干校七八年時間。干校后期,勞動之余,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之前在讀中學期間,我就讀了《毛澤東選集》的一二三卷,毛澤東同志熱情、雄辯的語言和強大的邏輯力量對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干校后期“待分配”期間,我開始抓緊時間讀書,向本所的姜永泰同志(他是郭漢城先生60年代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借了莎士比亞的劇本和希臘悲劇、喜劇劇本來讀,并讀了魯迅雜文的全部單行本。“文革”期間批判周揚、林默涵在《魯迅全集》的注解中做了“歪曲”,所以那時出版的魯迅著作的單行本都沒有注解。我借來老的版本對照讀,并把某些注解抄到單行本上。當時雖然沒有失去信心(我曾寫詩說:“自知不是經綸手,亦不甘為酒飯囊。”),但不知道將來能做什么,當時讀這些書都還不能有深刻理解,但對我的學術修養來說是重要積累。
彌補光陰逝 明晰研究路
“文革”后,文化部組建了“藝術研究機構”(后改稱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原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一個所。我是1976年春回到戲曲研究所工作的,從這時起才開始正式搞專業工作(此前只發表過粵劇《山鄉風云》的評論等一兩篇文章)。
這時張庚、郭漢城先生在全國招收研究生,我對張庚先生說,我想考您的研究生。張庚先生說:“你不要考了。我們招研究生主要是想從外邊招一些人來,擴大戲曲研究的隊伍。你有什么問題我可以幫助你。”于是,我便沒有報考。
根據戲曲研究工作的需要和各人的特長,戲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分在不同的研究室組,開始我是在當代戲曲研究室,此后便重點研究當代戲曲、戲曲文學、戲曲創作,也做評論。
回顧我的學術道路,有一些與前輩相同的特點,即并不是單純地搞研究,而是與戲曲創作的實踐緊密結合,具體地說,是與教學、編輯、評論等工作相結合。20 世紀80年代,《劇本》月刊刊登一些劇作家、理論家的照片,并要各人寫一句話。我寫的一句話是:“從實踐中探真知,經積累而求建樹。”這正是我想要達到的目標和遵循的道路。
這一期間,我參加的重大集體項目是張庚先生主編的《當代中國戲曲》,編寫組主要由戲曲研究所一批青年同志組成,我擔任編寫組負責人。張庚先生對中國戲曲史論體系有完整的構想,《當代中國戲曲》是繼《中國戲曲通史》之后,這一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后來我們又編寫了《中國當代戲曲史》;《中國近代戲曲史》因故這時沒有完成)。新時期以來,全國和各地的戲曲活動較多,相繼成立了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中國戲曲學會、中國近代戲曲文學研究會、中國昆曲研究會等組織。我積極參加這些學會的工作并撰寫論文。我開始是受戲曲研究所指派擔任與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的聯絡員,后來則擔任了研究會的編輯委員、副會長、常務副會長。在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先后擔任秘書長和會長的何孝充同志為人很好,善于聽取和吸收大家的意見,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從1980年研究會成立到現在,幾乎每一屆年會我都參加了。期間我為大家服務,也從各地從事戲曲創作演出和研究的同仁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具體感受到現代戲的發展進步。在中國戲曲學會,我繼龔和德先生之后,擔任了秘書長,再后擔任了副會長。除日常工作外,還和湖南的同志一起,連續組織和舉辦了數屆映山紅民間戲劇節。“劇壇寥落正彷徨,弦歌揚,起瀟湘,杜鵑如火,爛漫遍城鄉。”(安葵《江城子》)民間戲劇確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從1980年開始,我對陳仁鑒、翁偶虹、范鈞宏、馬少波、黃俊耀、楊蘭春、王肯、胡小孩、顧錫東、徐進十位在當代戲曲史上影響較大的老一代戲曲作家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總結他們從現實和歷史中提煉素材創作劇本方面的經驗和對戲曲傳統挖掘整理方面的經驗,撰寫成《當代戲曲作家論》一書。我讀他們的作品,觀看演出,訪問他們本人和相關的人,使我對戲曲創作有了更深的認識,打下了我研究戲曲創作論的基礎。在研究的過程中,我與這些老劇作家們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現在這十位劇作家中只有胡小孩健在了!那些已故去的老劇作家們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我的眼前。

1997年在浙江海寧王國維故居題字留念
在研究戲曲作家的過程中,對戲曲創作的規律、特點逐步有所了解后,使我認識到戲曲創作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即如汪曾祺先生說的“用韻文想”,因此可以叫做“戲曲思維”。我感到要真正把握戲曲思維的特點和規律,單獨研究戲曲還不行,還得進行戲曲藝術與姊妹藝術的比較研究,于是就撰寫了《戲曲“拉奧孔”》一書。
此后一段時間,我將所寫論文輯為《新時期戲曲創作論》和《戲曲理論與戲曲思維》,嘗試把當代的戲曲創作研究與古代的戲曲創作研究貫穿起來,試圖在古代戲曲理論和創作里梳理出與當代戲曲創作相對應的理論命題,以期更好地推動當代的戲曲創作,并通過把古典戲劇創作論與當代的創作結合起來以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民族戲劇理論體系。

安葵著作
研究戲曲理論必須研究戲曲理論家和戲曲藝術家的理論貢獻,因此我結合一些學術會議和紀念活動,先后撰寫了論述王國維、吳梅、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俞振飛、歐陽予倩、張庚、阿甲、郭漢城等戲劇家的文章,特別是對張庚先生的研究,撰寫了《張庚評傳》一書。因為多年的戰亂環境,張庚先生解放前的很多文章和作品都找不到了,為了搜集盡可能多的資料,我到各大圖書館查閱,還利用出差的機會訪問張庚先生工作過的地方,查閱當地有關資料。先后到過長沙、武漢、泉州、上海、延安、張家口、哈爾濱、佳木斯、通化、沈陽、大連等地,訪問了與張庚先生共過事的人,如呂驥、趙銘彝、陳錦清、干學偉、陳明中、石凌鶴、姚時曉、葛一虹、鐘敬之、張水華、田川、張瑋、胡沙等在現當代戲劇史上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訪問和閱讀的筆記記了十幾本。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這不只是張庚先生一個人的傳記,而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戲劇的歷史進程,通過寫這本書,使我對現當代戲曲的發展進程和老一代戲劇家的杰出貢獻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服務戲研所 往事可追憶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是郭漢城先生。他與張庚先生一起,在“文革”后領導大家重建隊伍,撥亂反正,做了很多艱苦的工作,為后來的研究工作開展打下扎實的基礎。第二任所長是蘇國榮先生。他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他與沈達人先生一起,主編了“戲曲史論叢書”,組織和推動戲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拿出第一批個人研究成果。我的《戲曲“拉奧孔”》就是這套叢書中的一種。那時出國考察的機會很少,他與院外事處的同志一起與文化部積極聯系,爭取到去印度做學術交流的項目。事后我知道他是很想去的,并做了很多學術準備,但最終他還是把這個“機會”留給了別人,讓沈達人、余從、我和孫玫四人去了。我參加了這次學術考察,收獲很多,在歷史文化的比較中加深了對中國戲曲和東方戲劇特點的認識。蘇國榮之后,余從擔任所長,我擔任副所長;余從退休后,我擔任所長。在此期間,我努力學習和繼承前輩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限于水平,成績不大。日常的工作很多,特別值得回憶的有幾件事。一件是與河北省文化廳聯合舉辦了“東方戲劇展和學術研討會”。1987年張庚、郭漢城先生曾策劃召開了“中國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使中國的戲曲研究與海外學者的研究緊密聯系起來。我們舉辦“東方戲劇展暨學術研討會”是想把這一工作繼續做下去。當時邀請了印度、日本等國的戲劇團體演出了印度戲劇、舞蹈和日本的能劇和狂言,研討會邀請海內外戲曲專家共同探討東方戲劇的特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件是連續舉辦了8 屆戲曲編劇培訓班以及戲曲導演、戲曲音樂、戲曲舞美各一屆培訓班。新時期以來,各地都有提高本地劇作家、導演等創作水平的迫切要求,我們辦培訓班正是適應這種要求。我擔任培訓班的班主任,吳毓華、陳靜擔任副班主任。我們請來北京的戲劇、文學、社會科學各方面的專家來教學,組織學員觀摩劇場演出和重要作品的錄像。對于外請的專家,我都在門口迎候,并和學員們一起聽課。學員們因為有很強的使命感,學習都非常努力,頗有“三更燈火五更雞”的氛圍。每一屆培訓班都組織游覽一次長城,我和大家一起登長城。一幅幅長城上的合影,記錄著大家共同學習的歡樂和友誼。這些學員中有很多人此后都成為各地創作的骨干力量。他們確實認為,在“前海”的這一段學習對他們的創作道路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一工作也繼承了中國戲曲研究院舉辦戲曲演員講習會和編劇講習會為全國的戲曲創作服務的傳統,加強了戲曲研究所與各省同志的聯系。這一階段還有與臺灣及香港、澳門同行的學術交流。在與臺灣的交流中,薛若琳副院長做了很多工作;在與港澳的交流中,田本相同志做的工作很多。我作為戲曲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也承擔了相關的任務。我曾帶臺灣的戲劇家到大陸觀摩戲曲演出,并推薦大陸的劇團到臺灣演出;作為副領隊和大陸學者一起到臺灣參加學術研討活動等。在這個過程中,大陸的戲曲研究者與臺灣的同行結下了友誼,也推動了兩岸戲曲研究交流的開展。

1998年,與編劇班學員合影,前排左一安葵,左二張庚

后排左起:安葵、郭漢城、劉厚生、龔和德
這期間,中國戲曲學會還組織了一些大型學術活動。1990年,中國戲曲學會與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了徽班進京200周年紀念活動,我擔任學術組副組長(龔和德任組長)。2001年,中國戲曲學會在南京舉辦了紀念毛澤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題詞50周年學術研究會,我作為秘書長負責具體組織工作,并撰寫了《推陳出新五十年》及《戲曲研究五十年》等文章。
為了激發青年學者研究戲曲的熱情,我們還與浙江的同仁一起舉辦了王國維戲曲論文獎的評獎,吸引了海內外很多青年學者參與。我退休后,后面幾任所長都繼續了這一活動,現在已舉辦了8 屆,這些參評的論文從一個側面記錄著戲曲研究前進的足跡。
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各國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文化部向全國各文化廳(局)發了通知,要各地認真準備申報材料。文化部又委托中國藝術研究院負責評審。我國符合條件的項目有好幾個,最后根據專家和文化部領導的意見,確定要申報昆曲,并組織專家組進行了多次討論。我當時任戲曲研究所所長,具體負責昆曲申報文本的撰寫工作。音樂研究所的專家、錄音錄像室的同志,對于文本的翻譯和相關的錄像資料,都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協助。文化部外聯局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外事處及時地轉達教科文組織有關專家的意見,我們再根據意見修改補充。2001年5月18日,昆曲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的全票通過,列入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1年6月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保護和振興昆曲藝術座談會,大家對昆曲被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意義和今后昆曲的保護和發展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同志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后文化部公布了《文化部保護和振興昆曲藝術十年規劃》。我為能參與這一工作深感榮幸。昆曲申遺的成功,是由于中國的昆曲藝術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全體昆曲人的努力,我所做的只是一項“職務創作”。此后,我還被聘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參與了文化部非遺評審、督導和調查研究活動。

與所指導的研究生合影,前排安葵先生和夫人,后排右起謝擁軍、何玉人、魏強、柯凡、朱俊玲
在學術研究方面,這一階段的集體項目有我與余從共同主編的《中國當代戲曲史》,這是在張庚先生的直接指導下由我負責組織大家共同完成的。2007年,我與薛若琳共同主編了《中國當代百種曲》,這是中國戲曲學會根據劉厚生先生的提議經集體討論確定選目后編輯而成的,我撰寫了“前言”。通過這些作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戲曲創作的成就和經驗作了系統的總結。
教學方面,我1995年開始帶研究生,先后指導了碩士生謝擁軍(她之后又隨郭英德先生讀了博士)和博士生何玉人、朱俊玲、柯凡,藝術碩士生魏強。退休前我曾擔任戲劇戲曲系主任,除給本院研究生講課外,還給中國戲曲學院的研究生講課,并給中國戲曲學院的貫涌老師、郝蔭柏老師、中央戲劇學院的彭隆興老師的研究生上“小課”。教學相長,學生們活躍的思維、睿智的思考對我常常起到啟發和推動作用。編輯方面,我先后擔任過《戲曲研究》的副主編、主編,《中華戲曲》主編。

授課中的安葵先生
退而未曾休 心懷使命感
2002年退休后,很想過清閑的生活。我曾向朋友們散發我寫的一首打油詩:“老驥伏櫪,慢慢吃草,烈士暮年,不能快跑。不貪事多,不嫌錢少,隨遇而安,怎么都好。”但文化部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領導對我很關照,給了我一些學習的機會。如文化部的一些觀摩研討、評審等工作,使我退休后仍沒有脫離戲曲人奮斗的實踐。直到2015年,我每年都應報刊之約撰寫本年度戲曲狀況的回顧、總結性文章。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我也都撰寫了回顧、總結的文章。我認為,在學術研究中總結歷史經驗是很重要的,只有充分肯定取得的成就,才能堅定我們的自信;只有深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更好地前進。退休后,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又讓我擔任了《昆曲藝術大典》的副總主編兼歷史理論典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第三版副總主編兼戲曲文學分支主編。除了參與設計整體結構、認真審讀所負責部分的文稿外,我自己也撰寫了一些文字,在工作中得到學習和提高。這些年,我也承擔了文化部“國家昆曲搶救保護和扶持工程”的很多工作,昆曲研究也成為我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2009年被文化部評為“國家昆曲搶救保護和扶持工程昆曲優秀理論研究人員”。

全家福
戲曲理論研究方面的許多問題,至今仍然吸引著我不能放棄思考。如戲曲理論體系的建構、戲曲美學的研究,都是張庚先生等前輩的未竟之業,需要我們繼續盡力。因此這些年,我又撰寫了關于戲曲理論建設和戲曲美學范疇的文章。我認為,現代戲曲理論建設必須立足于中國戲曲的實際,以中國古代戲曲理論為主要資源,吸收借鑒外國的戲劇理論,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并提升到理論的高度。我撰寫了《中國現代戲曲理論的構成和新的建設》《如何對待西方戲劇理論》等文章,后者獲得了中國劇協的理論評論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應該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三方面是緊密聯系的。戲曲美學范疇既屬于話語體系,也是建設戲曲美學體系的必需的一環。我把戲曲美學范疇梳理為形神、虛實、內外、功法、流派、悲喜、雅俗、新陳、美丑、教化十個范疇(已結集為《戲曲美學范疇論》,即將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這些論述是否符合戲曲藝術的實際,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退休后所以還能做一些事情得益于我有很好的家庭環境。老伴王秀琴與我是高中時候的同學,她從中國醫科大(沈陽)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是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的主任醫師,能對我的健康“保駕護航”。幾十年來我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生有一女一子,都是普通勞動者,包括女婿和兒媳,他們都勤懇工作,全家團結和睦。現在我的外孫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大孫女讀初中,二孫女在幼兒園。孩子們的天真活潑、不斷進步給我帶來欣慰和歡樂。因此可以繼續做力所能及的學術研究。
八十初度,我曾寫一首詩(步葉劍英元帥韻)表達自己的心情:
八十欣逢國運興
龍騰虎躍涌新人
開山蓽路仰前輩
繼晷焚膏步后塵
須教園花齊絢麗
誰言國粹向沉淪
渾然不覺黃昏近
大道精深尚未明
耄耋求精義 心得贈后學
因為有很多成績卓著的老前輩,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后生晚輩,但看到比我年輕的一代學者的成長,更是感到十分欣喜。如前所述,我是年近四十才真正開始專業工作的,現在不少四十歲的同志已經有豐碩的成果了。我也深知現在的青年學生和學者有與我們那一代不盡相同的生活壓力,社會的競爭也更激烈,所以要讓他們完全做到“心無旁騖”是不容易的。但我希望以學術研究為職業的人還是盡量能“心少旁騖”,趁身體好、記憶力好的時候,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學術研究包括我們的戲曲研究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做下去的。我在讀《張庚日記》后曾寫下這樣一段感想,寫在這里與大家共勉:
學術的發展要靠積累,但社會科學,包括藝術理論,研究的成果體現為一種認識的水平,它存在于個體的學者的頭腦之中,老一代的學者不可能直接把這些成果傳給下一代;年輕一代的學者必須從頭學習,并能體會到老一輩的心路歷程,才能把老一代學者研究的成果承繼下來,變成自己的積累。所以要“站到巨人的肩上”是不容易的。張庚先生 用畢生的心血把戲劇研究事業推向了前進,但藝術研究工作永遠在路上。我們要想在張庚先生等前輩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就不僅要學習他們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
最后再補充一點:李學勤先生談治學說,對于重要的學者,需要讀他們的全集。我認為很重要。只有讀了他們的全集,才能全面了解他們的學術思想和貢獻,也才能從他們的新貢獻中認識學術的進展。張庚與郭漢城先生,我都是讀了他們的“全集”的;在撰寫其他戲劇家的研究文章時,我也盡量多讀他們的著述,在這個過程中受益甚多。當然這是苦功夫。如同做考據一樣,不能指望每讀一篇資料都會得到想要的結果。有人把考據和義理(思想)的關系比做蠶吃桑葉和吐絲,只吃桑葉不吐絲沒有意義,但想不吃桑葉或吃很少的桑葉就吐出很多的絲來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