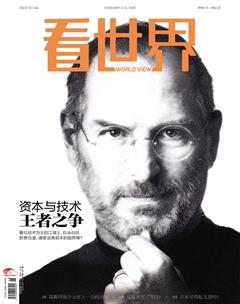社交網絡:“老大哥”與“刺頭青”
莫奈

Telegram創始人之一保羅·杜洛夫(Pavel Durov)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熱愛創造和運用社交軟件的年輕人,因此這里誕生了眾多影響深遠的科技公司。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巨頭的地方,就有應聲而起的挑戰。
刺頭小弟
虛擬社交網絡在出現之初,就懷抱著無限接近社交真實的愿景。從這個層面而言,每個軟件都以為自己找到了答案。
2011年,臉書(Facebook)、Twitter和LinkedIn分足鼎立,成為社交界的三座大山。它們在構建熟人連接、媒體關系連接和職場社交關系上各有千秋,成為人所皆知的“巨頭”。當然,在此之前也不是沒有過挑戰者,而這一年出現的小弟尤為刺頭,至今仍然困擾著臉書。
斯坦福大學的課堂上,為了交上班級作業,一位叫雷吉·布朗(Reggie Brown)的同學提出了一個想法:做一個允許用戶互相發送圖片,但不久后就自動刪除的社交應用。
這項在后來被命名為“閱后即焚”的功能相當刺激,像是喚起了每個人都會有的、在課堂上傳紙條的記憶。布朗邀請了擁有商業經營經驗的斯皮格爾(Evan Spiegel),還有墨菲(Bobby Murphy)一起編寫這款應用程序,并命名為Picaboo。2011年9月,程序正式在斯皮格爾父親洛杉磯的家中上線,成為了Snapchat的原型。
最初,Snapchat的吉祥物是一只純白的幽靈外殼,名字則和前Wu-Tang Clan樂隊成員的藝名一樣,是“鬼臉殺手”(Ghostface Killah)。幽靈的標志與軟件所提供的理念非常相似,寓意是信息如同幽靈一般轉瞬即逝。Snpachat在它出生之日起就帶著叛逆的基因,以“信息的‘消失才是真實”為噱頭,從此打開了社交界的新大門。
半年后,Snapchat的受歡迎程度已經遠超想象,每秒就有25張快照從Snapchat上發出。2017年3月,Snapchat的母公司Snap登錄紐交所,成為2012年臉書上市后規模最大的美國科技業IPO公司。七年多來,Snapchat還能屹立于社交江湖,本身已經是一個奇跡。
七年多的時間里,Snapchat有著為人稱道的創新手段。它發展出了兩項和閱后即焚一樣受歡迎的功能,分別是濾鏡(Lenses)和快照(Stroies)。
2013年推出的快照功能,本質上和Snapchat提倡的閱后即焚概念是一致的,就像是賦權用戶發布一個可以增加動畫效果和貼紙、但會實時消失的朋友圈內容。
快照的功能,一開始不像濾鏡那樣受到熱捧。人們無法揣測用這樣的方式來發布動態有什么樂趣,但是在一些新聞和社交現場,快照發揮出了獨特作用—如果同一個地理位置的人的快照聚合起來,能形成類似“眾包新聞”的概念,大大增強了活動的現場感和人的存在感。“快照”因為可復制性強,后來被大部分我們熟知的社交軟件抄襲,成為信息流的未來趨勢,“微博故事”也來源于此。
幽靈的標志與軟件所提供的理念非常相似,寓意是信息如同幽靈一般轉瞬即逝。

Snapchat的創始人墨菲(左)和斯皮格爾
過去的社交軟件,總是提倡“虛偽的完美”。不走尋常路的Snapchat忽略了刻意做作的濾鏡和生活瞬間,這是它生存的縫隙。不久之后,它就被臉書盯上了。
老大哥“賭氣”
在Snapchat推出一年后,臉書和扎克伯格本人敏銳地意識到后起之秀的存在。他們為此成立了創意實驗室(Creative Labs)。2012年12月,這群人就像賭氣一樣,只用了12天就開發出對標Snapchat的新軟件Poke。在使用者看來,Poke無論功能還是外觀都和Snapchat相差無幾,像是同一個模板下的兩款產品:不僅發送的文字、照片或短視頻可以在10秒內自動消失,而且還都能收到對方在手機上截圖的警報。
Poke在推出后一度令人驚喜,初始用戶量和下載量龐大,扎克伯格還親自為此編寫代碼,希望收獲人氣。但是經過Snapchat的一輪宣傳攻勢,Poke的活躍度便如過山車一般直線下降,還在2014年遭到下架的命運。所謂的創意實驗室,被外界戲謔為抄襲實驗室。
如果競爭失敗,不如嘗試把它買下?扎克伯格的確是這樣想的。畢竟一直以來,臉書就是這樣干的。
2012年,臉書以10億美元的報價,成功收購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圖片平臺Instagram,從此掌握了圖片分享平臺的話語權。
2013年,臉書用類似的方式向Snapchat提出了邀約,價格是30億美元,但斯皮格爾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筆交易。關于拒絕的理由傳聞不少,有人說斯皮格爾年輕氣盛,他和扎克伯格有著相同的出身背景,都是中產階級里的白人家庭,名校出身;臉書當年也拒絕被雅虎收購,Snapchat也不想輕易低頭。
無論如何,這次拒絕有著金錢利益上的先見之明,因為Snapchat上市后的市值立刻上漲到250億美元,和當年的30億美元已不可同日而語。
有報道披露,2016年扎克伯格曾經再次嘗試收購Snapchat的母公司Snap,依舊遭到拒絕。倔強的Snapchat不愿意被收購,反而深化了其獨立和前衛的標簽。
社交巨頭的臃腫程度和丑聞出現頻率,以正相關的關系呈現出來。

Snapchat的相機濾鏡很有趣,吊足了年輕人胃口
前文提及,濾鏡和快照是幫助Snapchat鞏固地位的兩項重要功能,快照更是Snapchat的王牌項目。2016年美國媒體Variety做的一項調查問卷顯示,在Snapchat里創建Stories是年輕用戶最喜歡的一項功能。
于是,臉書行動了。2016年開始,臉書及其旗下的Instagram、Whatsapp紛紛開啟了這項信息流嘗試,除了WhatsApp把名字換成狀態(Statuses)以外,另外兩款軟件直接就用“Stories”上馬“故事”功能—雖披著抄襲的外衣,還是受到了用戶的歡迎。
但是,“遇到對手先收購一波,收購不了的直接模仿”—一輪操作過后,臉書在業內的名聲一落千丈。
此消彼長
如果說Snapchat的橫空出世,滿足的是Z世代喜歡刺激、虛無的新鮮感,那么Telegram的出現,則是用戶對隱私和加密主義的極致追求。
Telegram在2013年由俄羅斯杜洛夫兄弟(保羅·杜洛夫和尼古拉·杜洛夫)正式發布。這對兄弟天生適合科技創業,尼古拉比保羅年長4歲,他不但3歲就開始看書,而且還曾贏得三屆國際奧數金牌。有如此優秀的哥哥,保羅符合了一位弟弟慣常有的習性—叛逆,不服從權威,上學時經常黑入學校的網絡,有一次,還將他最討厭的老師的照片和“該死”兩個字并排。
2006年,臉書的風潮橫掃世界。剛從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畢業的保羅發現,俄羅斯的年輕人并沒有非常踴躍地使用臉書,于是他在使用習慣和語言上做了改進,22歲那年創辦了俄羅斯最大的社交網站VKontakte(簡稱“VK”,意為“與你聯系”),被人稱為“俄羅斯的扎克伯格”。
隨后的幾年,VK成了俄語區最流行的社交網站。創始人不止一次自豪地說,VK是唯一一個在自由市場競爭中勝過臉書的產品。
但生活在俄羅斯,一家社交公司很難自由自在地野蠻生長下去,保羅不斷遭到無名的騷擾和來訪。回憶起過去,他說,第一次被警察突襲住處的經歷讓他喪失了安全感。他很快發現,沒有任何通訊方式可以保證他想要的安全和隱私。

很多極右派組織會利用Telegram群組的方便性和加密性招攬成員,這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心頭大患”
Telegram就是在這樣的縫隙中誕生的。不僅用戶的通訊被加密,而且用戶資料還會被分割成好幾份,儲存在隸屬于不同司法管轄區的主機上。軟件里,用戶還能選擇使用能夠自毀消息、照片和視頻的秘密聊天,并能使用其他密碼鎖定應用。
在社交關系愈加被暴露和展現的年代,Telegram就像是饑民們迎來的美食。無怪乎在2014年1月24日,臉書宣布收購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后的5天里,Telegram增加了800萬用戶。
社交巨頭的臃腫程度和丑聞出現頻率,以正相關的關系呈現出來。2018年3月,《紐約時報》和《衛報》稱,臉書上5000萬用戶的信息數據被一家名為“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泄露。
報道稱,2014年,27萬臉書用戶下載該平臺上一款個性分析測試的應用軟件;應用軟件開發者將這些用戶及其臉書好友的數據,賣給“劍橋分析”公司。數據包括用戶檔案信息以及他們“點贊”的內容。
此后,臉書更改了開發者可通過此種方式獲取數據的數量。但事件披露者稱,“劍橋分析”在臉書收緊“用戶同意”規定之前,就已獲取了約5000萬用戶的數據。
相比于有可能通過商業模式透支隱私的科技企業,近似公益項目的Telegram無疑是一匹黑馬。它不僅宣稱不靠出售用戶信息盈利,并且完全使用自有資金來維持研發和服務器運營開支。迄今為止,它的確沒有曝出過存在后門、用戶信息泄漏等安全方面的負面消息,保持著向第三方披露0字節用戶數據的記錄。
當然,這個功能也有被濫用的風險。很多極右派組織會利用Telegram群組的方便性和加密性招攬成員,這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心頭大患”。
饒是如此,每次臉書有新情況出現,Telegram就會經歷一波用戶增長潮。
2019年3月15日,臉書因為遇到技術問題,幾乎所有產品停工,用戶報告無法訪問Instagram、WhatsApp和臉書本身以及其所有內容。
雖然在超過24小時后,臉書最終控制了問題的蔓延,但在停機這段時間里,Telegram新增了300萬新用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