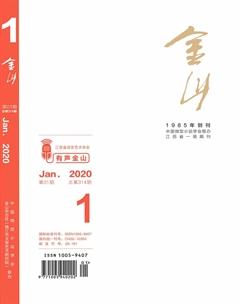隔洋仰望賽珍珠
銀笙,原名師銀笙,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延安市作協原主席,延安市委原常委兼宣傳部長。出版長篇小說《狼煙》、散文集《銀笙散文選》《情滿陜北》等十多部,主編16卷《黃陵文典》。高級記者職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編者按: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在鎮江度過了童年、少年,進入到青年時代,前后長達18年之久,她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她的創作靈感、思想觀念、寫作素材深受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影響。坐落在鎮江風車山的崇實女中,不但是賽珍珠就讀的母校,也是她大學畢業后曾執教的學校。
賽珍珠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倡導文化自主、文化平等、文化尊重、文化寬容,是中美及中外文化交流中一個不可忽視并應大力推崇的文化使者,是城市文化包容、中西融合的一個見證,被稱為“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
《金山》作為鎮江市唯一具有國際國內刊號的純文學期刊,也是對外文化交流的一扇重要窗口。本刊與鎮江市賽珍珠研究會聯合開設“風車山下”欄目,緬懷賽珍珠的文學貢獻,弘揚賽珍珠入橋精神,推進賽珍珠文化研究、傳播與傳承。
賽珍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給她帶來極大的榮譽和實惠,但也招來相當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和不滿,大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如果她都能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么每個人得獎都不應該成為問題。”另一位后來也得了諾貝爾獎的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則更為尖刻地說,情愿不拿獎,也不愿同“賽中國通夫人”為伍。她被貶損有多方面原因,她寫的是中國的事情,遠游離于美國的主流文學題材。而且學的是講故事的中國“章回體”,缺少西方現代作家看重的“意識流”,認為她犯了大忌,成了美國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作家之一。
在美國被貶也許還可理解,但在中國也屢受責難。《大地》在美國出版不久,中國《東方》雜志便開始譯載(胡仲持翻譯)。其后幾年,上海、北平、重慶等地書局出版了8種不同版本,不少人對該作產生濃厚興趣,報刊雜志發表了50多篇介紹和評論文章。但不少文章卻從根本上否定她的小說,認為作者表現的是一幅諷刺中國的“漫畫”乃至不屑一顧。出現這種現象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不能不說魯迅的短短的一句話起了重要作用。他說過:“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女傳教士的立場而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才能留一個真相。”后來經魯迅博物館姚錫佩研究員考證,魯迅看到的可能是當時翻譯質量不太好的部分中文譯本,看了后面兩部曾給日本朋友增田涉寫信,準備對賽珍珠作新的評價……
截然對立的評價和激烈的批評觸動了我文學的探疑神經。那年我旅行經過鎮江,認識了在文化部門工作多年的王玉國先生。在講說鎮江名勝古跡時專門介紹了自稱鎮江為“故鄉”的賽珍珠,使我對這位傳奇作家產生了濃厚興趣。我對于傳播中國文化和故事的美國作家是非常尊崇的,曾寫過斯諾、斯沫特萊、馬海德等人,自然把賽珍珠列入研究對象,拜讀了他的《大地》《東風,西風》《我的中國世界》以及《賽珍珠傳》等作品,我贊成她是“第一流的小說家”的評價,也不由得向更多朋友來介紹她。
一
賽珍珠,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她的父親是傳教士,取中文名字賽兆祥,真誠地獻身于宗教事業,以滿腔的熱忱從事他所熱愛的工作,不關注家務等雜事,母親名凱麗。
賽珍珠出生4個月時離開家鄉,隨父母來到中國上海,4歲時遷居于長江和古運河邊的鎮江,輾轉多處,后居住在登云山一座古樸典雅、格局別致的磚木結構的二層樓宇里,占地面積約400平方米,帶有白扶手的松木樓梯。二樓前面右首的一間是母親凱麗的房間,“從這里可眺望小平地,一片平坦的林地翠綠地伸向遠方的群山,花園過去是那棵槭樹。圍墻外是城市骯臟的街道、瞎眼的乞丐、擠作一團的房屋。而圍墻內除了樓房有凱麗精心打造的美國式花園,花園里種的是美國花卉,砌的是美國紫羅蘭花壇。”那道圍墻把兩個世界截然分開:西方與東方,基督教與異教,白人與黃種人,文明與落后。在鎮江她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時代,長達18年,她能講一口流利的鎮江話,最喜歡品嘗鎮江買的蜜橘,還津津有味地吃仆人的午餐,她的腸胃早已習慣鎮江的各種美食,她在《自傳》中詳細記敘過兒時的難忘記憶。在中國前后生活了近40年,中文成為她的“第一語言”,她自豪地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
凱麗祖籍荷蘭,多年生活在中國,富于熱情和感情,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漸漸愛上中國。讓女兒先后在私立鎮江崇實女子中學(后改為鎮江市第二中學,現已恢復原名)和上海讀書,為了讓她能進入美國大學,凱麗親自擔任女兒的老師,訓練她的英文寫作能力。賽珍珠10歲時,上午在母親指導下閱讀美國的教科書,下午接受私塾孔先生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中西方文化教育培養了賽珍珠多角度看問題的方式,使她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濃厚興趣。18歲時回美國弗吉尼亞市倫道夫—梅康女子學院學習4年,開始顯露了寫作才華,在一次全校有獎征文活動中,獲得小說和詩歌兩項第一。因母親有病她畢業后返回鎮江,于25歲那年和農學家布克結為夫妻,隨丈夫到安徽宿縣等地做農業研究工作,廣泛接觸了農村和農民。多年的生活使她融洽地融入中國社會,不僅愛上中國的山川景物,更深愛中國人。
母親是她的人生導師,她對母親懷有深深的感情。1921年凱麗病逝,她將母親埋葬在鎮江牛皮坡西方公墓。這年下半年賽珍珠和布克受聘于美國教會在南京辦的金陵大學(1952年并入南京大學),并住進了校內一幢單門獨院的小樓。母親的不幸病逝激發了賽珍珠的創作靈感,她想讓孩子們了解他們的外婆,寫成了《異邦客》一書,直至她成名后才發表,不料這部處女作成為她的代表作之一。
寫完這本書后,她決定將自己的“作家夢想”付諸實踐,在廬山牯嶺度假期間寫了散文《中國之美》,盡情歌頌“千般的美,萬般的柔”的“獨特可愛”的風景,揭示其“體現了最崇高的思想,體現了歷代貴族的藝術追求”的內涵,很快被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給人們畫出濃郁神秘的風景畫。在那個年代,由于列強瓜分中國疆土,不少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去美國西部“淘金”,從1870年至1880年,去美國西海岸的華人由10369人劇增到39579人,他們做牛做馬被當作奴隸驅使,仍不能滿足富人欲望,美國于1882年出臺了“排華法案”。而賽珍珠描繪的不一樣的中國,引起了媒體和民眾的關注,約稿單不斷寄來,她的創作熱情越來越高。
賽珍珠的丈夫對文學沒有興趣,身旁也沒有有共同愛好的文友,她不但要承擔孤獨的承襲,還要承受生活的壓力,開始寫文章是偷偷摸摸的。1925年,她和布克回美國度假,在輪船上終于清閑下來。晚上把女兒哄睡后,她在餐廳找了一個角落開始寫作中篇小說,因沒多大把握壓在箱底。回美國后積蓄花光,在東挪西借艱難度日的狀態下,她冒昧把中篇小說寄給《亞洲》雜志,沒想到很快發表,并寄來100美元稿費,成了他倆的救命錢。寫稿可補貼家用,她接著寫了《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獲得了豐厚獎金。幸運降臨讓她大步跨越,開始第一部長篇小說《東風,西風》(又名《一個中國女子的述說》)的寫作。
這是一個并不曲折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從中國老式封建家庭成長的女子楊桂蘭,在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的倫理道德下,不但纏了小腳,也學會侍奉公婆、丈夫。但丈夫卻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新式人物,告訴她:“我不會強迫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附屬品,不是我的奴隸。”在楊桂蘭對公婆逆來順受時,丈夫卻進行激烈反抗,最終從家里搬了出去,并讓她放腳。她接受了丈夫的新思想,夫妻恩愛,家庭和睦。這部小說把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結合在一起,強調“盡量學習洋人的好東西”,出版后獲得不錯的銷售成績,更加堅定了她寫作中國題材的信心。我突發聯想,求學的年代“東風壓倒西風”那句風靡神州的口號,可能就是從這部書中借鑒來的。
二
《東風·西風》的成功讓賽珍珠看到用寫作改變命運的機會,開始醞釀一部堪稱“史詩”的小說。
賽珍珠從小接觸的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小說,使她看到了不同于西方傳統的中國式寫作,領略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她發現,中國小說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內容和藝術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歷史上種種文化因素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她意識到一個嚴重問題: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作家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去認識中國和中國小說,大多作品都帶有偏見。她要用手中的筆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了解真實的中國人民,這才符合她一貫倡導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文化理念。
然而,社會發展卻出人意料。1927年,北伐、“四·一二”大屠殺使中國戰火重燃,社會失去控制。一支北伐軍占領南京,流血戰斗從3月23日持續到24日,教堂連遭破壞,鄰人告訴她軍隊正在屠殺白人,至少有六個外國人已喪生,嚇得全家在一位勞動婦女蘆媽的幫助下,藏進一個沒窗子的小土房逃脫劫難,不得不以“洋難民”身份奔到上海。戰事剛結束,賽珍珠冒著危險于1928年夏回到南京,整座家園成了馬廄和“公廁”,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產,卻在一個小壁櫥里驚喜地翻出木箱里存放的為母親寫的《凱麗的傳記》手稿——后來出版時書名改成《異邦客》。
在南京,她擔任幾所著名大學的英文教師。每天下午,收拾完家務,就躲到小閣樓開始創作。她以鎮江、南京、宿縣農村為背景,把目光牢牢放在了占中國人大多數的農民身上。在她之前,中國人在西方藝術作品中的形象總是和“小偷、娼妓、陰險”分不開。長期在中國生活使她被農民的淳樸、善良和頑強所感動,決心用世界級的寫作水準為“不善言辭”的中國農民說話,寫他們生活的艱辛、理想與追求,把中國普通人的形象介紹給全世界,向西方展示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國。在她之前沒有西方作家關注過中國農民,就是中國自己的作家對于農民投去的目光也十分吝惜。她的《大地》講述的是主人公王龍從貧窮的農民到富有,從受迫害到迫害別人的一生。他雖然變富了,但內心深處仍然充滿對大地的愛。他把土地看作命根子,在臨終時給三個兒子留下遺言:“我們從土地上來……我們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守得住土地,你們就能活下去,誰也不能把你的土地搶走……千萬不能賣地,一戶人家賣地之日便是他們敗家之時。”小說中的土地也是一個人物,是一個重要人物——她養育人,能使人健全,讓他們生命旺盛,財源滾滾。這部書深刻揭示了農民和土地的不可分割的依存關系。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賽珍珠的脈搏也與中國婦女一同跳動。她塑造了王龍的妻子——從財主家買回的丑陋丫頭阿蘭。她協助王龍勤儉度日,省吃儉用,指點王龍買下幾塊好地。后因連年災荒,他們被迫流落城市,父親和妻女沿街乞討。意外使他們獲得一包錢財,回家買地并成為財東。不料王龍看上妓女荷花,被冷落的阿蘭默默承受背叛最終病重死去。賽珍珠對阿蘭寄予深深的同情,她塑造的阿蘭在長長的人物畫廊中成為“形象鮮明的這一位”。
《大地》在美國出版后,引起讀者對這個異域故事的極大興趣,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暢銷的書,當年就賣出180萬冊,報刊稱贊她為“第一流的小說家”,很快有了德文、法文、荷蘭文、瑞典文、丹麥文、挪威文等譯本,出版此書的莊臺公司也因此從一個負債累累的出版社一躍而成紐約著名的出版公司。海倫,斯諾就坦言自己是讀了《大地》才到中國來的。第二年,該書獲得美國最重要的長篇小說獎項——普利策獎。
1938年夏天的一天,當賽珍珠打開家中的大門,發現不少記者擺好相機爭著要采訪她。她問發生了什么事?記者們說:“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向斯德哥爾摩打電話聯系后,才知道這是事實。獲獎作品是中國題材的《大地三部曲》《異邦客》和《東風·西風》,授獎詞中定義:“她曾在文學園地中,產生富有理想主義的最杰出的作品”,“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杰出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種族的鴻溝,并在藝術上表現出人類偉大而高尚的理想。在授獎后舉行的大型宴會上,主持人更進一步介紹賽珍珠“通過自己質地精良的文學著作,使西方世界對于人類的一個偉大而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視……賦予了我們西方人一種中國精神,使我們意識到那些彌足珍貴的思想情感。正是這樣的情感,才把我們大家作為人類在這地球上連接在一起。”我以為她的作品呈現了一個民族的情感深度,因而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強大力量。
獲獎使中國小說第一次受到西方文學界的關注,對中國文學將產生深遠影響。她清楚中國小說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內容和藝術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歷史上種種文化因素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她也意識到,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作家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去認識中國,賽珍珠要用手中的筆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了解真實的中國人民。只有這樣,她所倡導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對主義文化理念才能實現。1939年她又出版長篇小說《愛國者》、劇本《光明飛到中國》、隨筆集《中國的小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