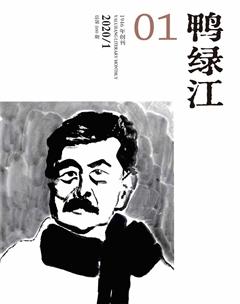小說技藝,如是我聞
黃孝陽
一、談論小說技藝是困難。如在曠野,在“一片龐然而有待辯讀的靜默里”,我看見了落日下的山河震動,而身邊的你,我所深愛的你卻一無所聞。這并非是你的愚昧,否則我也不會對你有如此深的繾綣眷戀。你是三維的,而我是四維的。又或者說你用舌尖感知萬物的咸,而我是那只蝙蝠,晝伏夜出,依靠聲吶系統(tǒng)來發(fā)現目標和探測距離。你當然是對的。但你的“對”并不構成我的束縛;相反,是我的翅膀。世界猶如蝴蝶的翅翼,在令人暈眩的“急速的顫動”中,有著無與倫比的美與神秘。此種顫動,沒有善惡好壞, “你的對”是翅膀向上的那一刻,“我的錯”是翅膀向下的那一刻。兩者的和,便有了蝶的盈盈飛起。
二、一些人的文學才華是一個從涓涓細流到大江大河的過程(這是容易理解的,是H2O的累積,就其景觀而言有不同面貌,能裹脅人心,其本質屬性未有變化);而另外一小撮人的文學才華是一個從涓涓細流到飛禽走獸的過程(這里存在著物種進化,是突變)。所以親愛的人啊,你若是獵人,我便是匍匐在你腳下的馴鹿;你若是漁夫,我便是甘愿把腮幫穿透于漁鉤上的鮭魚。
三、什么是小說,在我此刻的理解里(下一刻的回答又會不同),它是存在之詩,是時間的眾多旋渦與空間的各種漣漪之總和,是對人的凝眸。如標月之指,蘊藏著我們理解自身及世界的八萬四千法門。又或者說,它是一塊擱在你面前的舊鐘表,指針在嘀嘀嗒嗒地響著。你想起許多,與此塊鐘表有關的“許多”,你的身體因為這“許多”有了改變,比如腎上激素的分泌,比如衰老。你突然就知道把這塊表送給你的那個女孩即將死去,死于心力衰竭,獨自死于人潮洶涌的街頭。是的,“突然”,突然間你發(fā)現你所置身的此刻,不僅是過去種種凝結出的一小塊結晶體,亦是未來的種子。而你也無力改變這顆種子的屬性,哪怕你手上已握有可以穿梭時空的來自未來的黑科技。你能做的,只能是靜靜等待著淚水把你抓住的那一刻。當那一刻終于降臨,你也只能是放聲大哭,并在淚水中真真切切體驗到生而為人的痛苦與喜悅。這痛苦是如此巨大啊,如子宮,你將自其中分娩而出,重生。而那喜悅雖細弱,不過寸余,又若千年暗室之燈,讓你的魂靈漸有形體,猶如撲火的蛾。
四、寫什么?怎么寫?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你得反復告訴我,你為什么要寫,不厭其煩。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通俗點說,這是最基本的內功心法,決定你是少林派、武當派還是青城派,至于“寫什么與怎么寫”,則是相應的招式。少林的一力降十會是好的,武當的綿密細柔是好的,青城的快準狠是好的,但這都需要相應的心法以為根本呼吸。若心法與招式不匹配,便易走火入魔。
五、我想說的是“漁”,不是“魚”。魚是干貨,拿來就能下鍋。“漁”,是方法論,是價值觀。靠出海捕魚為生的漁夫,與岸邊垂釣養(yǎng)生的漁者,是兩個物種。你得想明白你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你的渴望終究會成為現實。就算你因此成為《傻瓜吉姆佩爾》的主人公,但那又有什么關系呢。所有的謊言都有被實現的那一天,區(qū)別只在于時間、地點、人名不同而已。當你真正理解了這一點,你便踏入真實之境。人之一生,無非是渴望,人對他自身的渴望。是渴望成為一個桃,還是渴望成為一片林子。前者就要諳熟關于桃樹的一切,習性、姿態(tài)、生長節(jié)奏、神話傳說與風俗。最重要的是,要滿足人們對“桃樹”的主要想象。桃樹里走出一個女桃妖是可以的,若桃樹里跑出一頭牛頭怪那就不妥。后者更強調一個維度的轉換,要在一個宏觀里把握。文本的結構就顯得異常重要。萬丈高樓平地起,這高樓要有設計圖,不能搞所謂的零度寫作,沉溺于傳統(tǒng)文本里最常見的那種“河流敘事”。對于此時代而言,重要的不是“魚”(手機是所有人手上拿著的圖書館),而是對各種信息的搜索整理分析歸納推理結論,繼而具有迅速行動的能力。而貫穿行動始終的,就是敘事——小說怎么可能是無用的呢?
六、人是自由的生物,又渴望安全,厭惡風險(這里存在著一個二律背反)。通常情況下,對后者的渴望更大于前者,所以我們多半習慣按圖索驥,沿著先人提供的路線圖向前,再向前。但是,親愛的人啊,這個時代正在發(fā)生著劇烈的變化,我們所置身的藍色星球不再是三百年前的那個。從前慢,那張路線圖是準確的;今天,謬誤百出。只要你愿意去正視眼前的事實(我把它命名為新現實),你就能看見飛機的路線圖,高鐵的路線路,還有那份騎著一輛摩托車漫游茫茫中國的路線圖。“傳統(tǒng)雖好,已然匱乏”。你只有理解了我說的這種匱乏性,你才可能明白我要說的小說技藝。在門檻邊編把藤椅,與俯案制作一塊機械表,真的是兩回事,所要求的材料、工藝原理、專業(yè)技能,絕然迥異。
七、現代性是一個關于歷史分期的概念,是一個人類從地面一躍而起(飛機的發(fā)明當為揭橥)的澎湃過程。它對應的是歷史性,猶如晝與夜的對應。我們目前的大多數寫作,基本還在歷史性的范疇里,故而“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是好的。這是不夠的。我長篇累牘地論述過現代性三個字。其實我所要講的小說技藝,都在這三個字里面。比如我說過現代性的九張面龐。第一是主體性。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我目光所及,才有奇妙動人。這里有一個強人擇原理。不被我所注視的,皆屬冗余與無意義。或許是有價值的,邊際效益趨零。世界因為我的目光才能得它的組織結構與聲色光影。二是“我要知道我要干什么”。尤其是在今天這個“人為自身(不再是神)立傳”的時代,寫作者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寫什么,其文本即噪聲。委婉點說:一個有賴于他人解讀的文本是可疑的。粗暴點說,你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那你能干出什么來呢?一個朋友曾對我說,小說家要學藏。這是對的,萬千人海一身藏。海明威的冰山理論與中國畫的留白,眾所周知。但你能藏的,得是你有的東西。你不能說,你連自己藏起來的是什么東西,都不知道……第二是建構性。第三是碎片性。第四是不確定性。第五是戲劇性。第六是復雜性。第七是開放性。第八是加速性。第九是無限性。這里就不展開詳述。總之,這九張面龐構成九宮格,一個奇妙的 “人的魔方”。
八、對于寫作者來說,沒有比發(fā)現自我更重要的事了。此種發(fā)現,一定是建立在對他者充分尊重的基礎上。我與他者是一個黑白互生陰陽互根的整體性景觀(太極圖),是一個具有流動性、不斷生長、與宇宙同步膨脹的有機系統(tǒng)。換而言之,我與他者都是此系統(tǒng)(真理)的一部分。不能過于沉溺于內心。內心那個聲音令人著迷,但它在某個時候確實是阻礙,是塞壬女妖。要有對外部世界的渴望。如果沒有這種渴望,他者的聲音,哪怕是你夢寐以求的引力波,它也是一堆沒有意義的背景噪音。外部世界日新月異,以一個超出普通人認知范疇的速度在迭代更新。我們來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構成它的兩大引擎是科技與資本。同時,它也呈現出五種基本沖突,一是知識體系的沖突;二是資本與權力的沖突;三是國族利益的沖突;四是技術與倫理的沖突;五是代際沖突。換個說法,一個自命嚴肅的寫作者必然會超越傳統(tǒng)敘事或鄉(xiāng)土美學,去理解什么是科技的澎湃力量,什么是資本的貪婪與游戲規(guī)則,在這五種基本沖突中取一瓢水——包括 “記住鄉(xiāng)愁”,但此種記住必然是在一個現代性目光的審視下。今天的寫作者應該把筆墨集中于這瓢水。這瓢水里才有當代中國人的面容及其起身時的身影,才可能讓自己的寫作技藝從加減乘除進階到矩陣算法。
九、我承認在面對“認知經驗里的回響”時,人是容易有共情的。尤其是在這個現代性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更愿意為那個已然消逝的古典家園點贊,這是各種鄉(xiāng)愁濫觴所在。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為什么有這個“故”字?哪怕這個字里到處是跳蚤與臭蟲。因為這是對確定性的渴望。我們說時代如同風暴,少數人在某些時候可以說“我看見風暴激動如同大海”,但更多在風暴中的人渴望島嶼。這種確定性就是島嶼。這種對確定性的渴望根源于人的本能。確定性還是套路,原型。當人類還在莽莽叢林茹毛飲血之際,這種確定性幫助他們迅速判斷哪種果子可吃,哪種野獸危險。“迅速”極其重要。不夠“迅速”的基因傳遞下來的概率微乎其微。但這仍然是不夠的。因為據說人類是從一種3億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鯊魚進化而來的。我是魚,我喜歡水;但我還想到岸上去。倒不是說岸上是人演化的終點,而純然是出于對未知的好奇。更重要的是,“如果說人是時代的產物,那么今天的人皆是現代性的孩子”。世界如此廣袤,我之足履所及,便是贊嘆,便是祈禱。上岸是痛苦的。我原來說過一個比方。大家都知道那個第一個跳下樹的猴子是人類的祖先(如果進化論是對的)。但我要說的是:這不是一只猴子,而是許多只,在直立行走、走向未知的那趟艱辛旅途中,很多猴子被猛獸吃了,掉下懸崖摔死了……死法多種多樣吧,有的還死得特別有幽默感。我大概率是那些死去猴子中的一只。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親愛的人啊,我在這里,就像你在此短暫人世。我們都是一個彩色萬花筒里的小碎紙片。我書寫的這些漢字,是我唇上的甜;亦在此刻,為你品嘗。
十、16年有部電影,叫《分裂》,男主有23種人格,每種人格各自對應一種思維模式、行為方式,有信徒、頑童、嗜血者、強迫癥等。各種人格對身體支配權的爭奪戲,讓看電影者顱內高潮。而某幾種人格之間的關系也是敵我矛盾,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我不是一個多重人格者。今天有個流行詞叫斜杠青年。即,人的知識結構的跨界與融合。人在這個社會上所擁有的,不再是一個身份,有了多種可能。每種身份,或者說職業(yè),為我們理解這個世界提供了一種知識結構與視角。知識即人格。一個當代地球人的知識結構當有四個維度: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科技的,一個是文化(學)的。所謂人之四維。四維不張,人就是扁平的,單向度的。但問題是:這四個維度的知識結構并不必然兼容,常互相為敵,要讓大腦死機。怎么辦?承認“我是我的敵人”,這樣才能心平氣和,逐漸成為一座山脈,內有千溝萬壑,有懸崖與瀑布。我說過現代性的九張臉龐,其中有一張即是復雜性。我喜歡復雜性,把它比喻成一座花園,即可以流連其中不覺旦暮……還是回到《分裂》這部電影,導演M·奈特·沙馬蘭不是在拍一部多重人格分裂的紀實電影,他讓那23種人格共同作用,一起分娩出第24種人格,也即是一個擁有超現實能力的人。小說是超現實的。如果現實只是當前公眾語境所定義的那個。
十一、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沒有什么比這個“觀”字更重要。我們活在一個觀念世界里,觀念事實的影響力通常大于客觀事實。文學觀是一個人生命觀的溢出。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那個社會結構相對穩(wěn)定的古典社會。經驗的有效性在這個由現代性驅動的新現實里呈現出邊際遞減效應。圣人賢者留下的古老訓誡如同牛頓經典力學,還能影響日常,但起根本支配作用的,是相對論與量子理論。現如今的文學理論其實是經典力學框架下的,落后于這個以“大數據、小時代、碎片化”為特征的開放社會,不足以解釋這個日趨復雜的世界……這些年我聽到別人說我是一個先鋒作家就很傷感,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啊,只是我眼里的現實與他們眼里的現實不一樣。我們是“現代性”的孩子。我寫的就是現實,我從未離開現實半步,我呈現現實的方法是由現代性孕育的那些點、線、面,不是什么高難度的級數、波函數。有時我覺得這些方法就像使用微信添加朋友一樣,當屬于不言而喻的常識。
十二、所謂新現實,我把它又稱之為知識社會。它大致有四個特征:一個知識生產呈指數級增長的塊莖結構,一個人可能真正獲得主體性(自由)的個人時刻,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戲劇性的現代性景觀,一個“技術奇點”隨時可能爆發(fā)的前夜。我曾論述過這四個特征,這里不復贅述。知識力是國族最核心的競爭力。小說也不例外,知識在文本中是極端重要的。比如,它讓蝴蝶成為蝴蝶,罪犯成為罪犯。知識讓細節(jié)真實可信,你不能讓一個手持漢陽造的士兵擊斃一公里外的敵人;比如知識給出語言的活力,擺脫文藝腔等,讓它豐乳翹臀。形容一種老奸巨滑的笑容,說他“笑得像一個 2”,這遠比平鋪直敘說他“笑得意味深長”來得精確生動;比如各種學科知識提供的理解世界的不同維度,能極大豐富寫作者的魂靈,開闊其視野。知識提供了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觀念、視角與經驗(小說家是對他們的概括),一個可以信賴、值得尊重的知識結構;比如知識提供的各種公理定律,能指導小說的文本結構,隱喻人物內心,測量人與人的關系……尤其是人文學科里的各種知識,懂得越多越好。今天的寫作者至少要精通其中一門。當然知識有很多問題,許多知識都是被苦心孤詣統(tǒng)一整理后的“技術現象或程序”,以及工具理性蔓延至社會領域所導致“生命本真”的喪失等等,這些可視為新現實的陰影進入小說文本。前幾天布魯姆過世,看到他說過的一句話,“關懷人類,而不只是取悅讀者……作品里起碼得有這么一些生命質素”,當時在微信朋友圈里寫了一段話:“寫了20年,最近這幾年才漸漸明白了,什么是生命質素,或者說,是我在《人間值得》里說的作為‘人的長嗥,不僅僅是對現有牢籠籓籬的打破撕扯,跨越躍起,建筑構架(追尋自由的歷程),更重要的是從諸多思潮觀念等中抽身后退,盡可能擺脫迷宮奇觀與大江大河的誘惑,回到人之本性(第一性),再往前行,重新與此時代結合,確認自我屬性,人之邊界,事與物的各種維度,及命運的澎湃賦格。”當然,寫《人間值得》時我沒想這么多;寫完后,這些字就在腦中‘涌現了,是凱文·凱利在《失控》一書中描述的涌現。
十三、對初習寫作者說幾條建議。未必有用。
1.讀文學期刊。用當年高考的氣力來讀。讀到滾瓜爛熟處,精微奧義自然顯現。他們的好,你看得見;他們的不足,你也能大致看見。看見之后,若還有想寫的沖動,那就開始瘋狂敲擊鍵盤吧。
2.先改寫經典。取其主旨、框架、人物關系、沖突之核,置入當下語境。各種改法。“所有的未來都包含在過去之中,是對過去的一種意味深長的闡釋”,而要真正理解這種闡釋,必須使用當下語境以及各種技術。你要懂得一臺蘋果手機究竟意味著什么,以及有些年輕人為什么為了獲得它不惜去賣腎。(只是追逐虛榮么?)
3.找到小說要講的那個核,一句話能拎出來的,哪怕就是你此刻戴著的那塊表(或任何一人一物一個瞬間),繞著它跳舞吧,至于跳倫巴還是慢三,沒那么重要。如果你能圍繞著這塊表寫上十萬字,你及格了;你若能寫上五十萬字,你就在牛掰的邊緣。
4.這個核最好是二律背反層面的沖突。通俗地講,忠孝難兩全,哈姆雷特的生存還是毀滅,我們貪戀手機提供的便利性又被手機此媒介控制,等等。
5.現實到此為止。在此刻度上,再前邁一步。
【責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