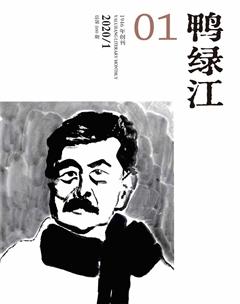走向崩解的自反性寫作
《池魚屋》是青年作家索耳近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整部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的主觀視角,以意識流的方式敘述了她與另一位具有共同經歷的女性的遭遇,而所謂的共同經歷則是她們與同一位男性發生過性關系。這部小說仍舊延續和發展了索耳強烈的個人化寫作風格,由此同索耳其他的小說包括《所有的鯨魚都在海面以下》《南方偵探》《飛鐵首乘紀聞》以及新近創作的小說《鄉村博物館》《非親非故》《皮套女演員之死》等共同構成了其在形式層面上的作者標志。
《池魚屋》這篇小說的女主人公楊惠純是一個性工作者。小說從她的主觀敘述出發,講述了她一天之中的經歷。她懷揣著一封信,準備把它寄給自己喜歡的一位男性,這位男性曾經作為她的客戶與她發生過多次性關系。在她去寄信的過程中,她偶遇了同樣接待過這位男性的另一位性工作者龐小蒙,龐小蒙還同這個男人生下了一個孩子。小說以一種含蓄而簡練的方式呈現了楊惠純對龐小蒙尤其是對她的孩子的復雜而微妙的情感變化。男孩彬彬成為他的爸爸之外又一位將兩位素不相識的女性維系在一起的中間物。彬彬的天真爛漫、單純無邪始終在喚起楊惠純身上美好的情愫,也在不斷升華她和龐小蒙之間的關系。
但是這篇小說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形式的層面上,作者索耳并沒有給予這些情感以顯要的位置,也沒有賦予其清晰的輪廓,相反,索耳始終以含蓄的筆法和高度抽象敘述使得這些情感隱而不彰,因而在巨大的情感潛流之上是極其有限的外在表達。由此看來,只有通過對小說形式內涵的分析才能抵達其幽微的意義深處。
首先,這部小說以高度凝練、簡潔、白描式的語言風格塑造了鮮明的、基礎性的文體特征。如下面這一段描繪女主人公同另一位女性初次相遇的場景:
“她在等車,等了有十來分鐘,跟其他人一塊在等。其他人上車了,又有另外一批人走過來。除了她,還有一個女人,一直站在原地。女人穿著卡其色棉襖,灰色牛仔褲,黑色皮靴。本來她沒注意這個女人的,但是后來她發現女人有點面熟,至少見過一兩面。肯定不是自己那片單元的,不然她就能準確叫出女人的名字。”
人物間的對話發展到后來甚至直接省略了說話者主體:
“傅秋來住的地方,在郊區,又窮又破,保證你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是嗎,比我們住的那小區還破?破得多!你見了他,就跟他說,讓他搬回來住,你們倆住一塊,多好,一塊兒養彬彬。真的嗎,你說他會愿意嗎?有什么愿不愿意的,自己的孩子,難道還不管了?他見了彬彬肯定會嚇一跳。為什么?他肯定會以為是我隨便找個孩子騙他來的。他要是敢這么想,這么說,咱倆就把他家房子給燒了。”
通過“有意義”的省略,人物之間急速、短促、快節奏的應答對話模式被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同時人物內心急切、焦灼的心理狀態也得以展示。
除此之外,作者通過蒙太奇式的省略和剪輯的手法構造句子與句子之間的拼貼,在場景的轉化、畫面的銜接過渡之處,作者創造出了通過斷裂來進行接合、通過空白來制造意義的張力結構,如在下面這一段敘述中:
“起風了。斜的雨滴,以輕盈的姿態鉆進傘底。褐色的公路在爬升。另一個方向上,車輛駛過留下的殘光散裂成千萬縷,褶皺,然后筆直向前逃逸,生成一個多彩的線性世界。一切都在變慢、變快、再變慢、再變快。公交車駛過來,變慢,停止,啟動,加速離開。”
蒙太奇的敘事不僅體現在場景的描繪中,還體現在人物心理的轉折、跳躍、突奔之處:
“孩子們的年紀從一歲到五歲不等,但彼此相處得很愉快。和諧社會,天真的熱烈的直率的氣泡從心底冒出。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童真會傳染。”
作者在此處描寫的是女主人公見到孩子們的心理活動,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結構同人物的意識結構達成了一致。在連續的意識之流中并不存在有規律性的情感的強弱變化、思想的漸次更替,毋寧說意識之流是一種朝向任何方向逃逸的散發和奔涌,故而超越了邏輯因果的規約,而作者正是在敘述的突然中止和起始中達成與意識結構的同構。
然而在這部小說中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作者在利用大量的省略、空白、斷裂、跳躍創造出文本節制凝縮的文體特征的同時又出其不意地加入一段繁復冗長的描寫,作者似乎有意識地對自己的文體風格進行戲謔式的解構,例如下面這一段描寫:
“從那一瞬間開始。西斯廷圣母。圣母的婚禮。坐著的圣母。卡爾代利諾的圣母。金絲雀圣母。帶金鶯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園中的圣母。福利尼奧的圣母。椅中圣母。阿爾巴圣母。一群圣母和圣子的黏合體。從草坪滾到山上,從山上跳到云端,從云端墜入大海,從海面潛入海溝。”
在這一段描述中,作者雖然同樣通過省略句子之間的結構性詞匯形成非邏輯化的句法形式,但是他同時通過羅列和堆砌意象制造出過剩、冗余的表述。作者在此以一種游戲和荒誕的態度完成對自我風格的自反性、解構性指涉,形成了文本的復雜多樣、歧義多元的面貌。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所追求的是異質之美與審美共存”(索耳:《我所追求的是異質之美與審美共存》)。小說在一種明晰統一的風格追求之中又通過異質性元素的介入去除文本形態的單一化和整飭性,在確立一種風格樣貌的同時又突兀地植入另類的描寫實現對這一風格完整性的消解,從而整個文本形成了通過局部讓整體走向崩解、通過對立讓統一朝向分裂的辯證敘事。
作者對于文本風格的塑造并不僅僅體現在語言風格上,亦即以最低限度的修飾完成對事物的概括和描述,以跳躍和突兀的蒙太奇手法組接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還體現在敘事層面上,通過有意的省略和留白造成敘事的斷裂和結構性空白,從而形成了召喚性的接受效果。這突出表現在對人物行為以及心理的描寫當中,小說幾乎對人物做出的某種行為或者生發的某種心理沒做解釋性的說明,而僅僅是呈現這種行為和心理本身。這也就意味著小說并不試圖讓讀者去理解人物以及小說的情節,它所力圖實現的是制造理解的難度同時擴充意義的層次性和豐富性。這樣的手法在小說中隨處可見:
“兩個影子。兩個影子在心里凸現。一對戀人在爭吵,女人扇了男人一耳光,男人把女人打倒在地上。三個月!楊惠純喊道。什么?龐小蒙沒聽清,回過了臉。我說——半年!楊惠純說。什么半年?”
“楊惠純看向龐小蒙,她睜大了眼睛,對方也看過來,對方的眼里隱藏著栗色的深淵。楊惠純非常難過,她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楊惠純趁機把手放在龐小蒙的手上,剛一接觸,她們馬上收回手去。楊惠純覺得龐小蒙心里有一點微小的憤怒,因為自己也是。她有些失望。”
在第一段當中,楊惠純為什么在腦海當中會浮現這種畫面,這一畫面有什么意義?楊惠純又為何突然說出“三個月”?又為何改口成“半年”?在第二段當中,楊惠純為什么會感到“非常難過”?“栗色的深淵”又代表什么?第三段的描寫更加具有代表性,楊惠純把手放在龐小蒙手上暗示著什么?又為何“剛一接觸”就又“馬上收回手去”?她們對彼此的憤怒和失望又是來自何處?
作者執著于一種“平面化”的寫作或者也可以稱之為是“單向度”的寫作。這種寫作將人物的行為以及心理本身作為書寫的對象甚至是全部的對象,而不對行為、心理所產生的原因進行解釋和說明。讓行為和心理本身成為小說的主體,省略行為和心理背后的深層次的動因,將人物在環境中的綿延作為獨立自足的陳述客體,有意克制通過潛在——表象、深度——表面這——立體的心理學模式將人物放置于生成—反應的因果機制當中,從而讓人物的行為和心理在一個單維的平面上自動地發生。這種敘述方式是小說的視角被嚴格限定在女主人公楊惠純身上所必然要采取的策略。整篇小說都是楊惠純的自我言說,是她自己行為和心理活動的自動化呈現,她的行為和心理活動所產生的原因對于她自己而言已經完全被了解而無須再有意識地敘述出來,而只有在面對一個外在的他者之時,這種行為和心理活動的原因才需要加以呈現。小說在這個層面上隔絕了自我(女主人公楊惠純)與他者之間的聯系,小說沒有設置一個對其進行傾訴和敘述的他者。這是一個完全自我和封閉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只有楊惠純本人在自說自話,這是一種比主觀敘述更加自我也更加嚴格的限制性敘述。而這其實也是作者對于創作和閱讀關系的一種思考,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將讀者視為潛在的進行文本閱讀的主體,視為是文本生產和流通當中的最后一環。換言之,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拒絕預設一個對文本進行閱讀的讀者,從而通過文本與讀者進行對話,通過穩定明晰的文本意義尋求與讀者的共鳴,作者反而在制造理解的難度從而與讀者之間形成緊張、沖突甚至對抗的局面。
索耳有另外一篇短篇小說,題目為“殺死觀眾”,這一題目似乎暗中表達出了索耳對于作者與讀者之間關系的理解。所謂“殺死觀眾”當然不是其表面意義所傳達出的對觀眾進行身體層面的清除和消滅,而是喻示著作者以一種同觀眾相隔絕的方式進行創作。這不僅意味著小說通過主人公的自說自話進行敘述,放棄了與行為和心理相關的解釋項的必要呈現,還意味著小說通過意義的崩解拒絕了讀者對小說進行單一化、本質性解讀的嘗試。傳統的小說讀者試圖在小說中建構一套穩定明晰的解讀模式,而在《池魚屋》這篇小說中作者通過自反式的寫作讓意義本身在小說中被耗散,使得對小說的文本意義進行建構的意圖走向崩解。就這篇小說而言,它既缺乏嚴格閉合的敘事結構從而將其置于開放和未完成的動態序列中,同時又在形式層面上掏空了統一的風格特征,筆法上的簡練、抽象同冗沉、繁復的描寫相互解構,由此徹底失去了對小說進行中心化解讀和建構的可能性。作者索耳似乎以戲謔的方式完成一場后現代式的游戲,他通過自身的游移、漂浮、變幻、奔突在一個巨大的文本疆域中信馬由韁。索耳拒絕被困縛于一個固定的點而是始終在各個方位之間來回擾襲,這同時也是他進行創作之時的文本哲學。
通過索耳的這篇《池魚屋》,我們可以窺見一個努力構建自己話語、風格以及意義體系的小說創作者。他在艱難地嘗試著用簡省、平白、樸素的語言完成解構與建構的浩大工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小說在形式和內蘊上的內在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也成為索耳帶有個人色彩的風格化標識,但與此同時,如何突破這種風格化的作者標識對他的規約,持續地在創作中發展自我,也是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張登峰(1991-),男,湖北黃岡人,南開大學文藝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