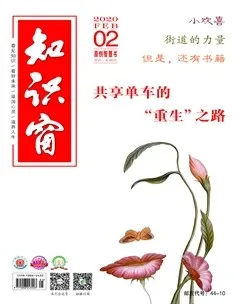一顆叫作葉培健星的小行星
胡征和
75歲的葉培健已經在航天深空探測領域整整奮斗了53年,為之作出了杰出貢獻,這位繞月探測工程衛星系統總指揮兼總設計師被授予了“人民科學家” 國家榮譽稱號。
2004年,我國月球探測計劃邁開了第一步——繞月探測工程正式啟動,這是繼美國、俄羅斯等國家開啟之后第五個月球探測計劃。面對一個全新的領域,葉培健院士帶領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研制團隊用了三年時間,在沒有任何經驗、數據參考的一張探月白紙上,先后攻克了月食問題、軌道設計等一系列技術難題。2007年,我國第一顆月球探測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十三天后進入月球環繞軌道展開科學探測,嫦娥工程的第一步——“繞月”順利完成。
第一步成功邁出,讓葉培健和他的團隊信心倍增,更有了不懈前行的動力。接下來,2010年和2013年,“嫦娥二號”與“嫦娥三號”相繼成功發射,前者獲得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精確的全月圖,后者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將航天器送到月球,并實現落月的國家。而2019年1月登月的“嫦娥四號”更是意義非凡,它首次實現了人類在月球背面的軟著陸。這次,葉培健格外激動,因為他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航天實力。從此以后,別人不能再說中國人只會跟著干了。
1945年1月,葉培健出生在江蘇省泰興市的一個軍人家庭,填寫大學志愿時接受了父親“我們國家需要強大空軍”的思想。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航天部衛星總裝廠,從此與航空航天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我國的航天技術還比較落后,為了掌握先進技術,1978年國門剛剛打開之際,葉培健就前赴瑞士納沙太爾大學微技術研究所攻讀博士。在那里,葉培健以努力刻苦而出名。當地一家報紙曾寫過他的專訪,問他:“為什么要這么努力?”他說:“國家派我出來學習,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我應該努力,為國家做些事情。”臨近畢業,他從來沒有想過留在富裕之國,他說:“我這個人民族自尊心很強,在國內干,是為自己國家干的,在人家那兒干,錢掙到了,但那是替別人干的,就這么一個簡單的想法。”1985年,獲得博士學位后,葉培健回國了。
在回國后的工作中,因為葉培健“知道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所以他總是敢為人先,勇于創新。他參與中國資源二號衛星設計,實現了星地一體化設計;他是第一個實踐把電測與總體分開的人;他是第一個提出在衛星進入發射場前,要進行整星可靠性增長試驗的人。特別是“嫦娥四號”著陸月球背面的創舉,更是他敢于挑重擔的結果。“嫦娥四號”原本屬于“嫦娥三號”的備份星,“嫦娥三號”執行任務成功后,作為備份星的“嫦娥四號”再落在月球正面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葉培健便建議落在月球的背面。可當時有專家認為沒有必要冒險,還是落在正面更保險。葉培健據理力爭:“搞科學探測,就不應該怕失敗,就要敢挑重擔,每一步都要有創新。”正是這樣的堅持,才迎來了探月史上的世界第一次。
2017年1月,為表彰葉培健在空間科學技術領域的卓越貢獻,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國際小行星中心將編號“456677”的小行星命名為“葉培健星”。
“嫦娥四號”在月球背面著陸后,葉培健又給自己加了擔子:“要把‘嫦娥五號做好,要把火星做好,同時把小行星的工程立項做好。”可面對葉培健的執著,很多人表示了不理解,甚至持懷疑態度,去月球干什么?為什么要探測火星?這能帶來多少GDP?
葉培健聽到這樣的疑問,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心平氣和并鄭重其事地予以解疑:“我認為宇宙就是海洋,不要以為今天看起來沒有用處,未來的太空權益,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去爭取。因為別人占下來了,你再想去,就去不了了。另外,很多科學的探索價值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越來越明朗的,不是說今天干什么,馬上GDP就增加多少。過去誰知道海洋里有石油,海洋里面還有那么多礦藏,更何況我們知道宇宙中的月亮、小行星上有很多資源可用,所以我們眼光要放得更長遠一點。”
原來,月球就是太空中的“釣魚島”,形象的比喻、理直氣壯的條分縷析,強調了探月工程既是國之重器,又與人民的生活分不開。葉培健的憂患意識與高瞻遠矚的眼界,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