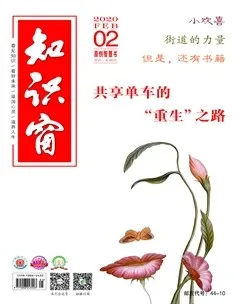梅花不急
許冬林
梅花開得遲。梅花不急。
出門回家,我路過一棵臘梅,正開花的臘梅。梅樹的葉子幾乎凋盡,只余一樹的臘梅花冷冷淡淡地開在嶙峋的枝干上,開得漫不經心。
迎著那冷香,我走近折了一枝。回家后,我將梅枝插進淡綠色的細頸瓷瓶里。一下午,梅枝在書房里,幽幽地吐著香,像是低聲部的吟唱,又帶著點敘事長詩的味道,婉轉,樸素。
冬天,在這不緊不烈的梅花香里,就此算是真正地開場了。
記得我少年時,外婆家的后院有一棵臘梅樹。臘梅樹是大舅栽種的,他愛養花,薔薇、大麗菊、美人蕉、君子蘭……實在是多。那時的我一去外婆家,就愛去那些花邊草邊轉悠。但對于臘梅,我心里哂笑大舅的審美。臘梅樹看起來實在是貌不驚人,完全不像能演繹一段傳奇的角色。
外婆家的后院,春天里,桃花、杏花鬧哄哄地開著,氣場盛氣逼人,狗都安靜得不嚷了。我那時常常仰面在樹下,等花瓣落到我臉上來,而臘梅樹呢,只是在長葉子,葉子俗常得很,惹不起人的興致。夏天,籬笆旁的木槿枝上眨巴眨巴地開起紫紅色的花來。臘梅呢,葉子倒是和木槿的葉子長得一樣厚,可依舊寒門模樣,片花不著。秋天,桂樹終于開花了,桂花的香充盈得一個村子都清甜起來,很有些五谷豐登的意味。
我聞著空氣里滿溢的桂香,心想:臘梅啊,你怎么辦呢!就這樣什么都不交代嗎?
臘梅樹依舊緘默著,靜靜地立在后院,人家長葉子,它也長葉子,人家落葉子,它也落葉子。它如何知道,一個小女孩已經在逼視它,逼視它生長的意義,懷疑它存在的價值。
可是,臘梅不急。它依舊安然走著自己的時令。
不記得是在哪一陣冷風里,我忽然聞到了花香。好奇地尋到后院,我看見落光葉子的臘梅樹上,有黃色的花朵打開,三朵、兩朵、三朵,像是各開各的,又像是呼應著開。更多的是花蕾,一粒粒的,像攥緊的小拳頭。
梅花到底還是開了!
我站在臘梅樹下,聞著冷香,覺得這香味沉實。若能把花香拿到秤盤上稱稱,梅花的香一定比桃花、杏花的香要重。
實在,梅花擔得起這傳說!
梅花的傳說,是一段用低聲部在民間吟唱的傳說,初聽平淡,細思感懷。
有些人的人生,其實就是一段梅花的傳說。
它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遭遇過漠視,遭到過嘲笑,遭受過排擠。就像我對待外婆家后院的那棵臘梅,我無視過它的存在,哂笑它不會開花,我甚至建議舅舅砍掉它,好讓芍藥、海棠們喧嘩地開。
但是,梅花沒有抱怨,它依舊靜靜地生長,篤定地伸展枝干。它只有一個信念:我要生長,生長,生長——長高,長粗,長得根脈深深扎進寬廣的土地,長得枝葉可以漲滿一座院子……
直到長得所有的花都開過了,長得所有的葉都凋盡了,它才長舒一口氣,開了。
頂風冒雪,寂靜盛開。一朵花一盞雪,一樹花一樹雪,即使開得肝膽欲裂,也是寂靜盛開。
苦難太深長了,所以,當最后一展芳華獨自綻放的那一刻,它是靜穆的。
苦難太深長了,所以,已經習慣低調,已經懂得從容,已經能穩穩地沉住氣。最后,當天地將一年的光陰交給它來壓軸收梢時,它已無意嘩眾取寵,無意顯擺炫耀。
樓下的梅花,依舊在漫不經心地盛開,漫不經心地零落。進出小區,我常常會路過它,我默然走過,覺得自己心上也開著一枝冷梅。我心上的這枝梅,也沒有委屈,沒有抱怨……只有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