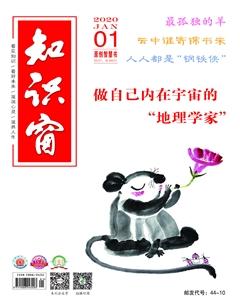時光靜好,知心無紋
薛峰

有三個清淡的人,令我尊敬。
第一位是張中行先生,已過世五年多了。在北京大學燕園,曾經住著四位老先生——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張中行,人稱“未名四老”,如今他們都離開了人世。據說,張中行先生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平靜地離去。季羨林稱張中行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抵是指他的學識修養、為人品格和等身著作了。
張中行先生一生清貧,85歲的時候才分到一套三居室,屋里擺設極為簡陋,除了兩書柜書之外,幾乎別無他物。老人為自己的住所起了個雅號,叫“都市柴門”。他的書房里書卷氣襲人,桌上攤著文房四寶和片片稿紙,書櫥內列著古玩,以石頭居多。他曾說,希望做點學問,看點書,寫點書,安安穩穩地過適然恬淡的生活。
第二位是陸文夫。
陸文夫,著名作家,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一舉成名。他的小說常寫閭巷中的凡人小事,深蘊著時代和歷史的內涵,清雋秀逸,含蓄幽深,淳樸自然,展現了濃郁的地方色彩。
有一年秋天,劉心武和陸文夫坐車前往蘇北采風,途中車堵在一處鄉村路口,剛剛下過一場雨,路旁一片泥濘。陸文夫從容地走下車,來到一個簡易的粥棚,提了提褲腳,然后踩著泥濘在裂痕斑斑的農家大板凳上坐下來。他要了一碗清粥,慢慢悠悠地喝著,喝了幾口后,沖不遠處坐在車上的劉心武微笑著豎起大拇指——那一幕讓來自北京的劉心武心里一震,難以忘懷。多年以后,劉心武著文說:“在那一碗鄉村農家清薄寡淡的米粥里,我看見了陸文夫淡泊的品性和清潔的風骨。”
第三位是林清玄。
林清玄是臺灣作家中最高產、獲得各類文學獎項最多的一位,出版過一百多部著作。他的作品大多以“品味生活中的真滋味”為主題,教人以一顆從容有情的心,活在當下,品嘗生命中甜的幸福、咸的離別和淡淡的生活平常,在柴米油鹽的平庸生活中品味人生的真諦。
而這,正是清淡的真諦。
有一次,在接受某刊記者采訪當天,林清玄穿著白色的西式襯衣,套著中式的黑色背心,頗具仙風道骨之感。年近六旬的他,目光睿智,語速舒緩,妙語連珠,常常穿插著幽默風趣的調侃,讓人覺得可敬又可親。
林清玄的文字之所以清淡,缺少那種熱烈與張揚,可能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小時候,他必須按父親的要求到樹林里去掃落葉,日復一日,辛苦異常。一天,父親開玩笑地說:“你為什么不把明天的葉子搖落下來一起掃呢?”林清玄歡天喜地地去搖樹,滿懷希望地想偷懶,但第二天,又是滿地的黃葉堆積。搖壞了幾十棵樹后,有一天,他豁然開朗,滿心歡喜:“今天掃完今天的落葉,明天的樹葉不會在今天掉下來,不要為明天煩惱,要努力地活在今天這一刻。”
于是,他看清了,也看淡了……
因此,讀林清玄的散文,我感受到猶如一道清泉,在這浮華人世里滌蕩心塵,開啟心智。
心不起不落,心安即清明。保持精神的敏銳度,在寂靜的生活角度,感受四季流轉的美感,享受內在的富足和安詳,涵養一顆水晶之心,澄澈自己,也清涼別人,能恒于孤寂而又免于孤寂,使心如秋月柔白,如碧潭清澈,如行云流水般流暢自在,那是大安心。就像林清玄說的:“以清凈心看世界,以歡喜心過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軟心除掛礙。”
時光靜好,知心無紋。在這有限的時光里,且吟且行,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