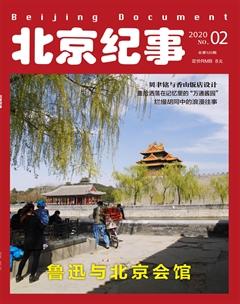榆錢兒飯的味道
張德虎


老榆樹綠得打眼,老枝新杈上,滿滿墜著一簇簇的榆錢兒

改良榆錢兒飯清新綠色的自然之味
桃紅柳綠春三月,嘗過了柳芽兒,品過了香椿,嚼過了薺菜,一張口就能吐出整個春天。回味之余卻仍不滿足,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榆錢兒飯
清明回鄉,在墳前一陣揮鍬,弄得滿臉土,一身汗。“瞧你弄這模樣兒!一邊兒歇著喘口氣去。”母親說著,一把搶過我手中的鐵鍬,健步上前,攘臂培土。母親動作麻利,老當益壯。我這個壯勞力,被淘汰出局,灰溜溜退居二線。只得在“后方”觀戰助威,也就樂得扭脖子抻腰,讓緊繃的筋肉松弛下來。腦袋還沒晃悠一圈兒,瞥見墳圈子外兩棵老榆樹綠得打眼,老枝新杈上,滿滿墜著一簇簇的榆錢兒。看著樹上的,想著鍋里的。劉紹棠用文字煮出的“榆錢兒飯”甘美可口,讓人垂涎三尺。而今,如此“尤物”就在眼前隨微風婀娜,若只遠觀而未有所獲,豈不辜負了這不期而遇又盼之良久的邂逅?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絕不能放過這次舌尖與榆錢兒飯的約會。
對榆錢兒飯思慕的種子,是劉紹棠散文《榆錢兒飯》種下的。“九成榆錢兒攪和一成玉米面,上屜鍋里蒸,水一開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夠火候兒。然后,盛進碗里,把切碎的碧綠白嫩的青蔥,泡上隔年的老腌湯,拌在榆錢兒飯里;吃著很順口,也能哄飽肚皮。”紹棠先生筆墨烹出的榆錢兒飯,色味俱佳,文堪下酒。勾起了饞蟲,也勾起了遐思。奈何看到文章時已是暮春時節,花謝花飛。榆錢兒也年老色衰,由嫩綠變慘白。一陣旋風起,如落滿地紙錢。把遐思吹成了祭奠。此刻,邂逅年華豆蔻的榆錢兒,如何能不動心?
“傻愣著什么呢?大功告成,班師回朝。”“媽,做頓榆錢兒飯吃吧。”我只當沒聽見母親的集結號。父親調笑道:“怎么著,爺們兒,饞了?”“您吃過嗎?”“敢情,打小那會兒,缺米少面的,開春榆錢兒飯可真沒少吃。”父親說著伸胳膊張手,握住眼前的榆樹枝,自上而下一捋,再張開時,已是滿手榆錢兒。“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捋完了,我給你們做。”母親笑著說。說干就干,一家人各自為戰,三下五除二,不多久,就有了滿滿兩袋子戰利品。
晚上一進家門,我就鉆進廚房。洗凈榆錢兒,備好玉米面。“棒子面少了!”母親站在門口望著我說。“這可是黃金配比!有書為證,劉紹棠說九成榆錢兒,一成玉米面。”母親只笑笑道:“多擱點兒棒子面吧,擱少了粘。”聽取了老廚意見,榆錢兒、玉米面五五開。榆錢兒混合著玉米面好似金中嵌玉,拌勻了上鍋蒸。水一開,滾幾滾。關火出鍋,大功告成。掀開鍋蓋,蒸汽朦朧,淡黃色的榆錢兒飯巨星大腕兒般地亮相了。盛進碗里,配上下午從二姑家菜園里現摘的羊角細蔥調成的料汁,再添一勺辣椒紅油,送一勺入口,榆錢兒的甜、料汁的咸、青蔥的鮮、紅油的辣,層次分明地刺激著味蕾。玉米面粗糲的口感把榆錢兒的軟糯烘托到了極致,把春天咬到了嘴里。我一連干掉兩碗,大祭了五臟廟,還意猶未盡!玉米面從不沾唇的姐姐,狼吞虎咽三碗后大呼“明兒個,還吃榆錢兒飯!”母親在眾人接連不斷的飽嗝聲中,遙想當年,“痛”說家史,苦訴童年……
改良榆錢兒飯清新綠色的自然之味,讓人著迷。在雞鴨魚肉滿口,山珍海味塞腸的富足時代,清粥小菜的寡味,便成了至味。劉紹棠筆下九成榆錢兒,一成玉米面,泡著隔年老腌湯的榆錢兒飯。自然樸質外,恐怕只能哄飽肚皮,味道并不太佳,卻仍然讓人著迷,是那碗榆錢兒飯里以苦為樂,苦中作樂的辛酸,還有沁潤著對生活飽滿憧憬的味道。
桃紅柳綠春三月,紅男綠女們陶醉在春光里;青黃不接春三月,丫姑和紹棠,一個騎在樹上,一個坐在樹下,乞求老榆樹救命。
一樹榆錢兒,兩種味道。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