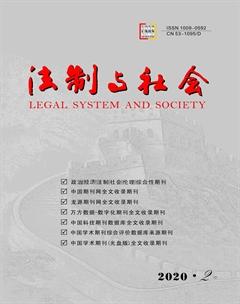醉酒駕駛行為出罪問題探討
關鍵詞 醉酒駕駛 病理性醉酒 刑事責任
作者簡介:祁婷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中圖分類號:D9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141
最高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其中有關醉酒駕駛的量刑幅度,載明 “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這是最高院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醉駕的出罪事由,但是該規定不夠具體細致,只是大體上的把握,指導司法實踐實用性不強,也忽略了罪刑法配置不當等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某一基層法院受理一起危險駕駛案件,案情如下:被告人酒后駕駛小型轎車途徑中環高架行駛到路面處,被設卡檢查民警攔下,民警發現被告人有酒駕嫌疑,遂當場對其進行呼吸式酒精測試結果為88mg/100ml。經鑒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為99mg/100ml,屬醉酒駕駛機動車。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但在法院審理期間,辯護人提出,被告人有病理性醉酒病史,應不負刑事責任。
對于病理性醉酒是否是危險駕駛罪的出罪事由,《刑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并無明確規定。但在法律適用以及刑法理論上,一般都是將病理性醉酒人納入精神病人范疇,認為其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如果一概而論,又是否合理?本文將從域外法的規定、及我國立法的不足等角度加以分析,完善病理性醉酒的出罪路徑。
二、病理性醉酒
(一)從醫學角度分類
醉酒分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病理性醉酒,又稱為特發性酒中毒,是指少量飲酒后,出現異常的極度興奮,并伴有攻擊和暴力等特征,在飲酒時或者稍后即出現了沖動、激越等攻擊行為,從而可能對他人或者自己造成傷害。發病可能出現斷片、幻覺、錯覺等,并伴有意識障礙,持續時間不長,以深睡狀態結束。
病理性醉酒伴有后續性遺忘,對自己的發病及伴隨的狀態行為,在之后一般不能完全記起或者只能回憶起小部分。一般無復發性可能,醉酒者也會在發病之后拒絕再飲,因而患者一般只會發病一次。病理性醉酒現象極為少見,可能與自身的個體素質或者大腦不耐受酒精有關,這種不耐受一般是由原有腦損害如外傷后遺癥、腦動脈硬化等引起。現代醫學和司法精神病學認為,病理性醉酒屬于精神病范疇,是短暫性精神障礙癥的一種。
(二)從法學角度分類
一種是少量飲酒后身體即刻發生異常反應而引發急性酒精中毒,一種是放任自己陷入醉酒的狀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別將前者定義為“無故意、無過失的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將后者定義為“故意、過失的醉酒”和“自愿醉酒”。
三、域外法的規定及我國立法的不足
(一)病理性醉酒刑事責任在英美法系中的規定
英美法系中法醫學鑒定有著非常嚴格的程序,舉證責任歸行為人,即病理性醉酒人需要證明自己當時處于發病狀態,否則應負刑事責任,屬行為正常人。并且規定,行為人若處于明知狀態,卻利用發病進行犯罪,仍然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即“被告因為醉酒而使自己行為不能自主,不應當作為辯護理由”“被告人如果是因為醉酒使自己的理解力受到損害,才無法正常預見自己的行為后果,這是不可原諒的”。病理性醉酒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是“非自愿”,美國刑法中明確規定,如果病態性的狀態系行為人主動引起,不構成出罪的理由,如果是在“非自愿”狀態下引起的醉態,即可以作為正當辯護的理由。這里的“非自愿”狀態即指病理性醉酒。
(二)病理性醉酒刑事責任在大陸法系中的規定
大陸法系針對病理性醉酒的立法模式分為總則和分則二種。
總則模式,如《瑞士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奧地利刑法典》等,在總則中專門設置條款,對于即關于心神喪失、耗弱等人犯罪,原因自由行為可作為其減免刑罰條款的適用。大陸法系多數國家都采用這種立法模式。
分則模式,即在分則中成立一個獨立的罪名,其中包含所有類型的原因自由行為。比如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德國,總則中沒有明確規定醉酒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只是明確了無責任能力和限制責任能力的規定,同樣適用于醉酒人。將醉酒等犯罪的刑事責任設置專門條文規定在刑法分則中。德國刑法認為病理性醉酒一般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但是如果故意制造醉態,是為了在無責任能力下去實施犯罪,這種行為是需要承擔責任的,應按照故意犯罪處罰。如果基于過失制造醉態,則應當以過失犯罪處。這實則跟美國刑法中的“非自愿”醉態有類似之處。
(三)我國關于病理性醉酒的相關規定
對于病理性醉酒的刑事責任,我國立法沒有明確,病理性醉酒人是否構成精神病及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及依據,均沒有明確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操作性差,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其次,我國立法沒有針對不同的特殊醉酒類型去規定不同的刑事處理方式,對病理性醉酒一般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及其他例外情況,僅將同類型犯罪的問題普遍化簡單化處理,缺乏理論依據。另外,我國沒有引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我國也未針對不同的醉酒犯罪類型規定具體和特殊的刑事制裁方式,刑法僅采取單一的刑事制裁方式,沒有區分病理性醉酒的特殊情況,沒有確立特殊預防機制,因而刑罰的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功能難以實現。另外關于病理性醉酒的鑒定問題,也可能發生鑒定失誤等問題,這主要是由于鑒定方法、材料以及人水平等諸多因素影響,且鑒定都是在發病之后進行的,對病理性醉酒鑒定難度大, 容易出現失誤的問題, 我國并無配套措施予以規避。
四、病理性醉酒的刑事責任分析
(一)不承擔刑事責任
病理性醉酒屬于暫時性精神病,依據主客觀相統一的歸責原則,病理性醉酒人是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不符合犯罪構成的主體要件,且行使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時,作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而言,其主觀上不可能是故意或過失,且不具備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如果對病理性醉酒行為人實施刑事處罰,就是僅針對客觀危害結果,即客觀歸罪,無法達到刑罰的目的。
(二)承擔刑事責任的例外
如果病理性醉酒人明知自己曾經發過病,卻故意再次飲酒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針對這種情形,我們引入“原因自由之行為”,可控的原因行為,即故意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應負刑事責任能力。以表面上,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時處于無責任能力狀態,其實行為人有飲酒的故意以及借酒實施犯罪的故意,行為人醉酒前擁有犯罪故意和具備的責任能力,并在此犯罪故意支配下實施醉酒狀態中的危害行為,即是其犯罪的責任能力要件和主觀要件。筆者認為,故意讓自己再次發病,并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并對其危害結果除以刑罰。但是若行為人是因為客觀原因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復發病理性醉酒而實施危害行為,即有過病理性醉酒病史的人,由于不能預見等原因再次飲酒,并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則不應當負刑事責任。
針對本案第一節提出的案例,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四年前曾因酒后毆打妻子,但醒后對發作過程完全不能回憶,后去鑒定,醫院做出了傾向于病理性醉酒的結論。如果法院不認可此結論,被告人理應負刑事責任無疑。但如果認可結論,對于此種復發病理性醉酒,被告人明知自己有病理性醉酒的病史,行為人依然飲酒,借醉酒實施危險駕駛行為,仍應追究刑事責任,除非被告人能舉證自己是基于客觀原因而復發病理性醉酒,從而對刑事責任進行阻卻。
五、完善病理性醉酒的立法構想
(一)完善關于病理性醉酒的立法規定
出臺關于病理性醉酒刑事責任的立法規定,比如在危險駕駛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加以明確規定,使司法實踐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避免引起分歧、過于籠統等問題存在,減少爭議,上訴和申訴等問題。
(二)引入原因自由行為
應明確規定因病理性醉酒實施了危害社會行為的,一般不應負刑事責任,同時規定應負刑事責任的一些特定情形,比如“病理性醉酒人實屬首次飲酒或因無法抗拒、不能預見等原因而使自己陷入病理性醉酒狀態,從而有社會危害行為的,不承擔刑事責任;故意或者過失使自己陷入病理性醉酒狀態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應當負刑事責任。”
(三)嚴格限定病理性醉酒的司法鑒定程序
因為病理性醉酒歸屬于精神病范疇,必須經過嚴格的司法鑒定程序,除了要不斷完善鑒定水平, 盡力避免鑒定失誤的發生,立法上還應當嚴格規定鑒定程序,指定由省一級以上的醫院進行鑒定,當事人還應當擁有申請重復鑒定的權利,因為鑒定結論直接關系到被告人是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必須審慎對之,還應結合具體案情加以研判。
(四)增加制裁方式
應強制戒酒或限制其飲酒,對于酒后因自己的危害行為造成了國家、社會或他人造成損失,應賠償相應的損失,還可以處以行政處罰、比如罰金刑等。
六、結語
醉駕所導致的社會危害比較嚴重,已經成為了現階段比較常見的一種社會問題,對人的生命安全造成無法挽回的侵害。因此,我國對于醉酒駕使的行為已經給予了一定的明確,這也是我國不斷完善的體現,但是對于出罪問題也同樣應當予以重視,除了明確但書條款中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更應當甄別其它沒有明文規定的出罪情形,并配以相應的法律規定,真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以便社會和諧風氣的塑造。
參考文獻:
[1]趙博譽.醉酒犯罪刑事責任依據和立法完善路徑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8.
[2]郭奕.醉酒人犯罪刑事責任研究[D].海南大學,2016.
[3]劉蘭.關于醉酒駕駛入刑的思考[J].法制與經濟(中旬刊),2013(8) : 16-17.
[4]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
[5]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6]高明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