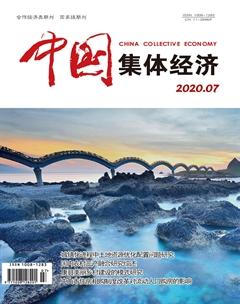生態補償的商品化發展進程梳理
王立
摘要:生態補償在傳統保護危機之后出現,生態補償定價機制受到了生態系統服務市場、“污染者付費原則”和生態系統服務付款、“管家收入原則”的影響,隨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環境保護主義的發展,生態補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最終實現商品化。
關鍵詞:生態補償;污染者付費;管家收入原則
一、生態系統服務方法
(一)傳統保護的危機
盡管人類在保護稀有物種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但傳統的保護方法無法扭轉或穩定全球經濟的代謝模式,其特點是對自然資本存量、生態補償和生物多樣性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保護運動未能對經濟和社會政治的變革驅動因素采取行動,且大多數環境運動長期不愿意與經濟學相聯系而造成的,這也是許多當前環境問題的根源。
例如,在當前的領土規劃方法中,可以看到將經濟學和生態保護分離為兩個單獨的政策領域。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本體論立場,認為人類與環境分離,自然保護作為經濟發展的讓步。在這種背景下,生態補償提供了一個從“保護與發展”的邏輯轉向“保護促發展”的邏輯轉變的機會。從生態系統服務方法來看,生態系統的保護是長期經濟可持續性的必要先決條件。
(二)生態補償方法的出現
生態補償方法將生態系統描述為給人類社會提供多樣化商品和服務的自然資本存量。生態補償除了包含木材、纖維和原材料等傳統商品外,也包含了大自然的非市場利益,但此時的非市場利益的價值既沒有反映在市場交易中,也沒有反映在公共支付中,在經濟核算和決策中也往往被忽視。生態補償的出現表明了可以克服傳統經濟的生態盲目性和實現永久經濟增長的不可能性。
(三)國際政策議程中的生態補償
20世紀90年代,生態補償方法的擴展超越了理論界,1992年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部分認可生態補償方法從理論轉向實踐。隨后,生態補償逐步有了識別、分類和評估的框架和方法。繼2005年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出版后,生態補償被納入國際環境政策議程。該議程包括開發生態系統和生態系統服務的標準化分類,這些舉措促進了環境商品市場和生態補償計劃的支付。
二、公共政策和市場中的生態系統服務
生態補償定價機制的擴展遵循兩種主要方法:一是“庇古解決方案”,在公共干預通過稅收和補貼糾正“市場失靈”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20世紀80年代起第二種方法是遵循“科森解決方案”,即在生態補償可以自由出售和購買的市場中,通過私人交易對市場失靈的進行糾正。這些糾正市場失靈的方法已通過兩個主要機制實施:生態補償市場和生態補償支付。因此,作為前者基礎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得到了后者的“管家收入原則”的補充。
(一)生態系統服務市場和“污染者付費原則”
“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基礎是責任倫理原則,根據這種原則,造成環境損害的經濟主體應承擔其創造的負外部性的經濟成本。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污染者付費原則已納入法律之中。在歐洲,它被列入1986年“歐洲單一法案”(第174條)、“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第130.2條)和“歐洲憲法條約”(第233.2條)。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也于1972年通過了污染者付費原則,并在1992年可持續發展里約首腦會議宣言(第16條)中予以考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用于實施污染者付費原則的主要工具是所謂的生態補償市場(MES)。例如,199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促進了二氧化硫的上限和交易機制。新市場遵循了這些經驗,例如英國的排放交易系統,2003年在美國建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以及同年在澳大利亞建立的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計劃。第一個國際排放交易計劃(ETS)于1997年在歐洲建立。當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生效時,ETS擴展到其他國家,在2010年創造了1420億美元的市場。
(二)生態系統服務付款和“管家收入原則”
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的是負面的環境外部性,“管家收入原則”處理的則是積極的外部性。生態補償(PES)被定義為至少一個提供者和一個受益者之間的條件和自愿交易。其基本原理是生態補償的受益者應該補償維護或保護使他們受益的生態系統服務的管理者。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推動了對采取措施防止土壤侵蝕的農民的支付,并且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了類似的機制來保護農田免受城市擴張。哥斯達黎加是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環境服務支付計劃的國家,它通過一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建立的計劃,每公頃提供45美元給業主,作為支持該計劃的補償。
三、市場保護主義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商品化
(一)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環境保護主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政策嵌入的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被定義為政治——經濟實踐理論,它提出通過以強大的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為特征的制度框架解放個人創業技能,可以最好地促進人類福祉。新自由主義包括政治經濟實踐,如私有化、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將市場估值擴大到以前不受商業影響的領域。
這些政治經濟實踐也在環境科學、政策和保護領域展開。一些學者認為,以貨幣形式重視生態補償的倡導體現在市場環境保護主義的邏輯中,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也是如此。市場環境保護主義可被視為一種旨在調和經濟增長、分配效率和環境保護的環境治理方法。市場環境保護工具集的基本要素包括:為具有公共品質特征的生態補償建立明確的產權,對環境外部性進行評估,以及使用基于市場的保護工具。估值、財產分配和基于市場的保護工具的邏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科斯和哈丁的制度分析基礎之上,科斯和哈丁已經適應了自20世紀80年代初在芝加哥學派影響下推行的私有化政策。
19世紀末以來生態補償已經涉及自然商品化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后商品前沿已經擴展到全新的生態補償類型,其中包括調節服務,如碳封存和流域調節,這些服務傳統上在市場范圍之外運作。
(二)生態補償的商品化
商品化的概念是指將市場貿易擴展到以前沒有上市的領域。它涉及商品和服務的概念和操作處理,因此,生態補償的商品化是指將新的生態補償納入定價系統和市場關系。生態補償的商品化通過四個主要階段進行:經濟框架、貨幣化、撥款和商業化。然而這些階段有時會在時間上重疊,并不總是必然伴隨的。
第一階段,包括生態系統功能作為生態補償的話語經濟框架,從生態補償的人類中心解釋開始,并繼續應用20世紀60年代的生態補償概念。
第二階段,發生在生態補償中嵌入的使用價值通過貨幣化或定價表示為交換價值時。這一過程在經濟理論中的概念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但更直接地與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外部性概念的起源有關。雖然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將貨幣價值附加到生態系統上,但環境科學家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對這項工作給予了關注,將估價框架進行系統化。
第三階段,包括生態補償的占用,并通過特定生態補償產權的正規化或產生此類服務的土地來運作。這一階段通過該私有化,以前在公開可用的制度或公共財產制度中的生態系統已經變成了私有財產。這個“自然”私有化周期的直接理論根源在于科斯和哈丁的研究。前者對明確的產權的辯護得到后者的支持,即公共池塘資源的私有化(或者國家的占用)作為避免過度開發的方式。
商品化過程的最后階段包括生態補償的商業化,即為生態補償的銷售和交換創建體制結構。與其他市場一樣,MES和PES涉及一種或多種服務的定義,這些服務隨后成為受貿易影響的商品。因此,MES和PES向新的生態系統功能的延伸涉及自然商品化的過程。
與常識相悖的是,商品化過程不一定是單向的或不可逆轉的,正如貝克所指出的那樣,“物品從商品狀態一再進出”。在特定時間點,由特定社會或一群人共享的一套規范、慣例和正式規則決定,對市場范圍的限制,即由現有的體制結構決定。通過利用制度,社會不僅決定商品化的內容,還決定什么去商品化。從歷史上看,可以隨著特定形式的商品化失敗或社會爭議來了解商品化過程。因此,商品化可以被視為有爭議和短暫的。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主導方向仍是商品化,而這種趨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加劇。
參考文獻:
[1]李珂.我國環境經濟學研究綜述[J].生產力研究,2017(11).
[2]李碧潔.國內外生態補償研究綜述[J].世界農業,2013(02).
[3]袁偉彥.生態補償問題國外研究進展綜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
*基金項目:西藏自治區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項目“基于碳匯的環喜馬拉雅生態區生態補償機制研究”(項目編號SK2017-06);西藏大學2017年度科研培育基金項目“基于碳匯的環喜馬拉雅生態區生態補償機制研究”(項目編號:ZDCZJH17-04)。
(作者單位:西藏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