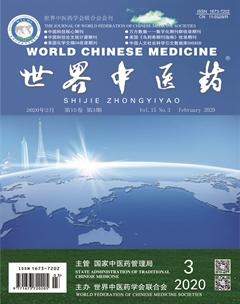從濕毒挾風論治炎癥風暴引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程演進
彭博 王世長 高彤彤
摘要 濕毒、風邪是本次COVID-19的主要病理因素,其產生和流行也具有顯著的自然、體質特征。在多種誘因的共同作用下,濕毒挾風邪致病具有傳播迅速、毒性熾烈、病情纏綿、易于傳變等特點,并與誘發輕型、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型轉化的炎癥風暴的產生密切相關。本文研究COVID-19的相關文獻和病例報告,從“天人合一”理論出發,分析COVID-19爆發流行的自然、體質因素,從濕毒挾風的病理性質和傳變規律論述炎癥風暴在COVID-19病程演進過程中的病理變化,提出以清熱宣肺、解毒辟穢、健脾除濕、疏風通絡為主的COVID-19治則。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濕毒;風邪;炎癥風暴
Abstract Dampness toxin and wind are the main pathological factor of novel coronavious pneumonica(NCP),its generation and spread also have significant natural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multiple incentives,the etiology of dampness toxin complicated by wi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spread,intense toxicity,lingering illness,and easy transmission.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inflammatory storm that induce the conversion of light and ordinary patients to severe and critically severe ones. The paper studi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 reports of NCP,and analyzed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factors of the outbreak of NC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storm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NCP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mpness toxin complicated by wind′s pathological properties and transmission laws. The mainly treatment principle for NCP was proposed which is clearing heat and purging lung,removing toxicity and dispelling filth,invigorating spleen for eliminating dampness,dispelling wind and dredging collateral.
Key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Dampness-toxin;Wind pathogen;Inflammatory storm
中圖分類號:R242;R256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0.03.003
2019年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陸續出現了大量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進入2020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疫情快速蔓延至全國其他3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截至2月20日24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5 465例,現有疑似病例5 206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606 037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120 302人[1]。目前,針對COVID-19尚無用于預防和治療的特效藥物,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派遣3支國家中醫醫療隊前赴疫情防控救治一線,截至2月17日,中醫藥參與救治的確診病例共60 107例,占比85.20%,湖北以外地區中醫藥參與救治病例的治愈出院數和癥狀改善者占到87%,凸顯了中醫藥防治急性傳染性疾病的優勢。
COVID-19患者多數以發熱、咳嗽等呼吸系統異常表現為首發癥狀,部分患者出現咽痛、腹瀉等癥狀,病情嚴重者可出現呼吸困難、低氧血癥,并迅速發展至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或膿毒癥(Sepsis),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危殆生命。研究人員通過臨床觀察發現,炎癥風暴已成為COVID-19輕癥患者病情迅速發展的重要節點,中醫藥在調節機體免疫功能中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臨床經驗,在阻斷輕型、普通型COVID-19患者向重型、危重型的轉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擬淺析COVID-19的病因、病機,論述中醫藥在調節細胞因子等免疫功能過程中的作用機理,討論COVID-19病程演進過程中的病機變化及防治思路。
1 中醫學對急性傳染性疾病的認識
迄今為止,COVID-19已在我國境內大范圍流行,世界多國也發現輸入性病例,而早在先秦時期我國便對急性傳染性疾病有了一定的認識,《呂氏春秋·季春紀》云:“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論述了傳染性疾病的季節性特征,《素問·刺法論》云:“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將傳染性疾病分為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并描述了疫病的癥狀特點,闡釋了人體對疫病的易感性,并提出了“避其毒氣”以保身全形。此后多以疫病代指現代的急性傳染性疾病,并將傳染性強、致死率高的疾病稱為“厲”或“疬”。
東漢末年,適逢大規模的戰亂、干旱等災害,瘟疫大范圍流行,張仲景由此著以《傷寒雜病論》傳世。同時代的曹植在《說疫氣》敘:“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記述了疫病流行時社會的悲慘狀態并強調了疫病強烈的傳染性,此后的歷代醫家對疫病的病因、治法均有闡述。
至明末清初,以吳又可等人為代表的溫病四大家強調了不同于內傷雜病,疫病的發病原因是特殊的疫氣侵襲人體,如《溫疫論》云:“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疫氣的不同,引發的癥狀、流行性也有所差異。對于疫病的傳播途徑,葉桂的《溫熱論》開篇提出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吳又可則更為完善的指出多種傳播途徑:“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至此,以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為特點的溫病學派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
己亥歲末大規模流行的COVID-19,潛伏期1~14 d不等,發病患者多以發熱、干咳、乏力為首發癥狀,部分患者有咽痛、腹瀉等癥狀,輕型、普通型患者或僅表現為低熱、乏力及呼吸道癥狀,重型患者發病1周后可出現呼吸困難、低氧血癥,病情進一步加重可進展為ARDS、膿毒癥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編印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明確提出了濕、熱、毒、虛、瘀為COVID-19的主要病理性質,并將其病機概括為:疫毒外侵,肺經受邪,正氣虧虛[2]。《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受先天稟賦、自然環境、致病因子等多種因素影響,疫病的流行更與多種自然因素有關。
2 從“天人合一”觀論COVID-19發病的體質、自然因素
“天人合一”是中醫學和古代哲學的重要思想,人與天地相參、與四時相副,陰陽的消長、四時的更替對人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體的發病與自然的異常變化更是息息相關。從體質因素而言,荊楚之士大多快人快語,率性而為,剛強易怒[3],肝木偏盛,多易乘克脾土,影響樞機。飲食方面以水產為本,魚饌為主,雖不及川蜀菜肴熱辣,但仍然偏于辣、燥[4],在情志、飲食等因素影響下易形成風木偏盛、脾土不及的體質特點。
《溫疫論》云:“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指出了疫毒來源的特殊性,并受到年運、節氣的影響呈現不同程度的毒性和傳播趨勢。厥陰風木司天,少陰相火在泉,己亥年運氣候整體風熱偏盛,耗傷氣陰,乘克脾土,脾運不足[5]。結合湖北省氣象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湖北省氣溫較常年整體升高,境內降雨量較歷年減少,但在6月降雨增多且出現極端降雨情況,至7月雖有多次暴雨天氣,但全月的降雨量整體較常年偏少5成,而在己亥歲末太陽寒水主氣時氣溫整體轉暖,冬行春令,又迎來多次大范圍雨雪天氣,降水異常偏多1.8倍,排歷史同期第1位[6],助長了濕毒邪氣的蒸騰而起。
武漢地處長江、漢江交匯之所,有“百湖之城”的美稱,水文資源豐富,正所謂“江河湖泊并存,因水而生,得水而興。”長年以來,武漢暴雨和洪澇災害頻發,濕濁之氣彌漫,而武漢又是“四大火爐”之一,歷年來長夏天氣炎熱,火熱之氣蒸騰水源,己亥歲終太陽寒水主氣,少陽相火客氣,天氣雖然轉冷但較歷年仍然氣溫偏高,濕毒之邪旋即而起。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提出:“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這也被認為是引發本次COVID-19傳播的自然環境因素。
3 炎癥風暴:COVID-19病情轉歸的信號
目前,湖北地區COVID-19的病死率為3.42%(截至2月20日),ARDS和膿毒癥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周琪介紹了部分患者出現了炎癥風暴(Cytokine Storm),被認為是輕型、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型進展的重要節點,也是重型、危重型患者引發ARDS和膿毒癥的主要原因。現代醫學研究表明,ARDS和膿毒癥的產生與自身的免疫調節功能異常引發的細胞因子的過度反應有關,病毒刺激免疫細胞釋放大量的細胞因子,當免疫反應超出機體代償能力時出現過度的炎性反應,引起廣泛組織細胞損傷[7]。中醫藥在調節機體免疫功能中具有顯著的優勢,對于免疫功能異常引發的腎小球腎炎、類風濕關節炎等疾病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
細胞因子(Cytokine,CK)是單核細胞、T細胞、B細胞等細胞受到免疫原、絲裂原或其它因子刺激產生的可溶性低分子量蛋白質,具有調節固有免疫應答和適應性免疫應答等功能。人體內不同的細胞能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干擾素、腫瘤壞死因子等,通過自分泌、旁分泌和內分泌的方式發揮作用。病毒在突破口腔、鼻腔黏膜免疫屏障后,多種免疫細胞發揮吸附、吞噬、裂解功能,細胞因子則負責在細胞之間傳遞信息,充當“免疫系統的信使”,而新型冠狀病毒致病性較強,具有較強的繁殖能力,且目前尚無特效藥物能遏止新型冠狀病毒的繁殖、傳播。潛伏期和發病初期,侵入人體的新型冠狀病毒誘導細胞因子水平升高,促進機體免疫細胞清除入侵的新型冠狀病毒,如果在一定時間內病情沒有得到良好的控制,機體免疫功能失衡,引起多種細胞因子在組織、器官中異常升高,形成細胞因子過度反應的炎癥風暴,最終會造成組織器官嚴重的病理損傷或功能衰竭。
COVID-19患者起病初期的胸部CT檢查呈雙肺多發小斑片影,隨著病情的發展新型冠狀病毒進一步損傷肺泡細胞并大量增殖,超過機體免疫系統的代償能力,釋放大量的細胞因子形成炎癥風暴,損傷呼吸道上皮細胞、肺泡毛細血管等多種細胞,大量的滲出物充斥肺組織,肺組織呈實質性改變,引發患者以呼吸窘迫、青紫、嚴重缺氧為主要特征的ARDS。炎癥風暴還能導致肝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研究發現在肝衰竭發生過程中依次觀察到肝組織免疫損傷、缺血缺氧性損傷和內毒素血癥3種病理變化,其中免疫損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8]。IL-6具有介導炎性反應和應激反應的作用,能進一步誘導系膜細胞分泌其它炎性細胞因子,增強細胞因子相互之間的作用,沉積于腎小球系膜,促使腎臟纖維化發展,加重腎臟損害[9]。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建議對機體炎性反應過度激活狀態的患者予以短期糖皮質激素、血漿置換治療和中藥方劑治療[10]。結合COVID-19的病理性質,中醫學認為疏風祛邪、抑制濕毒在機體內的浸潤彌漫能阻止患者從輕型、普通型向重型、危重型轉化;對于出現呼吸急促、手足厥冷甚則神昏、煩躁的患者應予清熱解毒、化濕涼營之品;對以高熱厥逆、神昏譫語、手足逆冷、呼吸窘迫為主要臨床表現的重型患者予以回陽固脫、開竅醒神等療法,必要時予以有創呼吸通氣或體外膜肺氧合(ECMO)。
4 從濕毒、風邪論述COVID-19炎癥風暴誘發ARDS和膿毒癥機理
日前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明確提出了濕、熱、毒、虛、瘀為COVID-19的主要病理性質,但關于COVID-19各類型分期的病機演變規律仍然引起了研究人員的廣泛討論。濕毒為患得到了中醫學界較為廣泛的認可,仝小林教授[11]、南征教授[12]分別分析了武漢、吉林地區發病患者的臨床表現認為COVID-19的起病初期以寒濕疫毒為主;陳瑞等人總結武漢地區52例患者初期病機多兼雜風熱[13];周仲瑛教授團隊分析南京地區42例患者病機以濕邪為主,兼有熱證或寒證[14];劉清泉教授認為COVID-19患者發病初期以濕邪為主,多伴有熱象[15]。
結合發病人群的流行病學特征和不同類型患者的臨床表現及舌脈資料[16],本文認為:濕毒挾風是本次COVID-19的主要病理性質,患者體質、氣候和地域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寒熱偏盛,但隨著病情的進一步發展濕毒化熱、生瘀、入營、燔血、彌漫三焦,引發難以救逆的危殆重癥。本次COVID-19具有疫毒熾烈、易于傳變、纏綿難愈的特點,病位以上焦、中焦為主。
4.1 濕毒侵肺,困遏脾陽,擾動營血,彌漫三焦——COVID-19的核心病機
中醫理論認為疫病的傳播多從口鼻而入,正氣的充盈與否決定了疫氣中病的強弱,正邪的消長關系決定了疾病進展的趨勢,而疫毒的性質決定了主要的臨床癥狀。COVID-19患者多以發熱、乏力為首發癥狀,或伴有腹瀉,察舌多見舌質暗紅、苔黃厚膩,部分患者熱勢不高,由此初步判斷濕毒是COVID-19的主要致病因素。疫毒之邪與濕相合使疫病更纏綿難愈,也為病情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變數。
不同于六淫致病,濕毒疫氣熾盛、毒性更強,中傷人體引發的癥狀也更為兇險,雖然經由口鼻而入,但濕毒疫氣不易流戀肌表皮毛,大多直中上焦肺葉,郁痹肺脈、困阻脾陽,衛氣不能敷布,氣機升降失調,濕毒郁而發熱,這也是很多患者發病初期肺衛癥狀不明顯的原因。濕毒疫雖然具有極強的毒性和傳播能力,但仍有顯著的濕邪致病的特點。濕為陰邪,其性重濁黏滯,易襲陰位,易傷陽氣,阻遏氣機,留滯經絡。《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于濕,首如裹。”說明了濕邪困阻,清陽不能上達于頭面,穢濁之邪不能下降,出現口涎黏膩,眼眵垢膩,如油裹面,頭腦昏沉,困頓乏力;肺為華蓋,濕毒疫氣熾烈、重著,最易中傷肺葉,郁阻上焦則胸陽不展、肺氣郁痹,因而可見咳嗽、胸脘痞悶;心與肺同處上焦,雖然有心包護衛,但感邪深重易于傳變,發病后期的患者能出現心功能受損;肺絡受邪,不能宣發肅降,肺與大腸相表里,大腸傳導功能失司,發為泄瀉、腹痛;脾為太陰濕土之臟,喜燥惡濕,《六因條辨·卷下》曰:“夫濕乃重濁之邪,其傷人也最廣……中則中其內……脾陰也,濕土也。”濕邪侵襲最易傷脾,己亥中運歲土不及,脾陽、脾氣較往年更弱,如濕毒困頓脾胃,升降失司,清氣不升,濁陰不降,清濁相混,可見惡心、痞悶;“傷于濕者,下先受之”這與濕性趨下的性質有關,易于流滯于肢體肌肉,表現為肢體的沉重、乏力。
濕毒為病纏綿難愈,病程遷延濕毒郁久化熱、生瘀,灼傷肺葉肺不納氣宗氣不生,耗竭脾胃陽氣化源不能,正氣虧耗陰津不攝。濕熱毒邪熾盛,彌漫三焦,肺納氣不能,心神明無主,脾化生無源,肝熱毒浸潤,腎開闔無常,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動輒喘甚,神昏譫語,肢冷汗出,口唇青紫,甚則內閉外脫之癥,幾可危及生命[17]。
4.2 濕毒挾風,竄行三焦,襲擾臟腑——COVID-19傳變的載體
大多數患者發病初期以發熱、咳嗽、乏力為主,衛表癥狀并不顯著,這與濕毒挾風侵襲肌表后迅速傳變有關。己亥歲風木偏盛,風邪與濕毒相合使COVID-19癥狀變化復雜多端。風邪為六淫之首,在多種外感疾病中極為重要,《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厥陰司天為風化,在泉為酸化。”風為陽邪,其性開泄,易侵陽位,風邪侵襲人體能使腠理開張,易于侵襲人體的頭面、肌表、肺衛;風善行而數變,或由口鼻、或由肌湊侵襲人體,發無定時,起病迅速,癥無定處,病情急驟,變化迅速,易于傳變,而與風邪相合的邪氣也兼具風性特點。《素問·風論》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風邪侵襲人體不獨自起病,往往與寒、濕、燥、熱等邪氣相兼為病,因此說風為百病之長。風邪的病理特性也印證了COVID-19的快速傳播、肺衛起病、傳變無常、夾濕熱毒邪的特征。
風邪與熱相合,起病初期患者發熱明顯,兼有咽痛口干;或與寒相合,癥見發熱惡寒,頭身疼痛。風邪引濕毒疫氣流竄臟腑經絡,使以熾烈、重著、黏滯為性的濕毒疫氣迅速傳變周身,藥物不能速達,針刺不能周全,病情更加遷延難愈。在此過程中,濕毒彌漫周身,內蘊三焦,燔灼營血,亡陽竭陰,患者病情迅速惡化。而輕型、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型的轉化過程伴隨著炎性反應因子的不斷升高,并引發炎癥風暴導致ARDS和膿毒癥。臨床中因ARDS和膿毒癥死亡的感染患者發病初期中醫辨證分型多為風寒、風熱、風燥之邪侵襲人體,入里化熱,肺內邪熱壅盛,化瘀生毒,濕濁毒瘀邪氣走竄三焦致肺氣衰敗、精氣耗竭,進而出現全身的器官功能衰竭引發患者死亡。在COVID-19中,風邪引動濕毒熱邪流竄,易于侵犯機體的多處組織器官,引發組織器官功能的減退或衰竭,表現出全身嚴重的炎性反應。人體中細胞因子種類繁多,不同的細胞因子形成的細胞因子網絡所引發的炎癥風暴也呈現不同的病理特點,這與風邪的善行數變性質極為相似。治療輕型、普通型患者時,在清熱宣肺、解毒辟穢、健脾除濕的基礎上給予疏風通絡的藥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濕毒的傳變;對于出現呼吸困難、神昏譫語等一系列危象的重型、危重型患者應及時予涼營開竅、回陽固脫的藥物,待病情稍緩后再行清熱宣肺、解毒辟穢、健脾除濕、疏風通絡之法。
4.3 營衛不周,衛外不固,失于內守——COVID-19病情發展的內在因素
本次COVID-19患者發病的潛伏期不等,且有統計數據顯示老年患者比例較大并容易發展至重型、危重型,這多與人體正氣的強弱有關,《溫疫論》有言:“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營衛營運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病熱。”說明了人體的正氣影響著發病、轉歸、預后過程。對于正氣本虛,年老多病的患者,往往發病不久便疫毒內陷,引發呼吸喘促、心胸憋悶,疫毒進一步耗氣、傷陰、動血而發為呼吸窘迫、神智昏聵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表現,這與現代醫學研究中病毒的感染程度超過了免疫系統的代償能力時大量的細胞因子引發的炎癥風暴相類似。年輕的患者正氣無明顯的虧耗,發病初期正氣鼓舞,維持了相對平穩的癥狀,但濕毒疫氣熾烈且纏綿難愈,日漸傷津、耗氣、燔灼營血、毒漫三焦,最終引發了相同的癥狀,而由于年輕的患者自身免疫系統功能完善,產生的各類細胞因子能引發更加劇烈炎癥風暴,因此臨床可見高熱、呼吸急促窘迫等癥。
細胞因子是調節機體免疫功能的低分子量蛋白質,細胞因子分泌“不足”“過多”都能對機體免疫功能造成巨大的損傷。衛氣是人體內能抵御外邪、護衛機體的一類精微物質,《靈樞·禁服》有言:“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衛氣失常是疾病的發病基礎,醫者在驅邪外出的同時應調節衛氣的循行節律,使其不得逆行、傾移。《靈樞·營衛生會》曰:“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以傳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氣、衛氣均由人食五谷釀化而成,有研究表明,人體攝入食物能引起細胞因子變化進而發揮調節免疫系統的作用,這與中醫藥理論具有相似之處[18]。前文已述,濕毒疫氣中傷人體除了表現出呼吸系統的異常外,對脾胃功能也有巨大的影響,在治療中扶助正氣、健脾除濕尤為重要,對于熱毒浸入營血、充斥三焦的重型、危重型患者,應臨證辨其順逆,或酌情少予行氣之品,避免補益藥物助長疫毒氣焰。
5 結語
從武漢爆發流行的COVID-19以濕毒挾風為主要病理因素,發病初期感邪不深,以發熱、干咳、乏力等輕癥為主。而濕毒疫氣毒性熾烈、病性纏綿,易于深中臟腑,加之風性善行數變,使濕毒流竄臟腑經絡,病情遷延正氣虧耗,濕毒內蘊臟腑郁而化熱、生瘀,燔灼營血彌漫三焦,引起炎癥風暴,誘發ARDS和膿毒癥等多種臨床危重病癥導致患者死亡。治療中不能忽視濕毒、風邪的傳變規律,特別是在輕型、普通型階段即應予以清熱宣肺、解毒辟穢、健脾除濕、疏風通絡之品,觀其陰陽偏盛予以糾正,避免濕毒疫氣的進一步傳變。對于已經轉為重型、危重型的患者給予糖皮質激素抑制免疫系統的過度激化或血漿置換療法降低血液中的細胞因子水平,同時給予中藥涼營開竅、解毒辟穢、回陽固脫,待病情稍緩后再行清熱宣肺、解毒辟穢、健脾除濕、疏風通絡。
中醫藥在防治急性傳染性疾病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疫情初起的扶正、辟穢預防性療法到感邪初期的驅邪外出避免傳變均體現了成熟的理論思路和臨床經驗。目前,雖然疫情的傳播得到了較好的防控,但隨著年運的變化、節氣的變更、病性的轉變,COVID-19也將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和臨床表現。中醫藥治療COVID-19仍需立足于起病的濕毒挾風的病理特征,結合人群傳變規律及陰陽偏盛,針對性的予以辨證治療,更早的介入,更多的參與,在COVID-19防治過程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截至2月20日24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況[EB/OL].(2020-02-21)[2020-02-21].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2/ac1e98495cb04d36b0d0a4e1e7fab-545.shtml.
[2]王琦,谷曉紅,劉清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20:4.
[3]馮惠茹.武漢方言中的武漢人性格[J].報刊薈萃,2017,29(10):75.
[4]熊正安.武漢飲食文化地域特色淺析[J].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學報,2006,20(3):13-14.
[5]顧植山.五運六氣看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J/OL].世界中醫藥:1-6[2020-02-2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29.R.20200222.2028.004.html.
[6]湖北省氣象局.2020年1月湖北省氣候影響評價[EB/OL].(2020-02-02)[2020-02-21].http://hb.cma.gov.cn/xxgk_29519/tjsj_29533/202002/t20200202_1411911.html.
[7]張艷麗,蔣澄宇.細胞因子風暴: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中的主宰生命之手[J].生命科學,2015,27(5):554-557.
[8]陳智,朱海紅,楊英.細胞因子風暴與肝衰竭[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4,30(10):981-983.
[9]朱俊利.百令膠囊對慢性腎功能衰竭透析患者營養狀況、炎性細胞因子水平的影響[J].新中醫,2019,51(8):154-156.
[10]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EB/OL].(2020-02-19)[2020-02-21].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8334a8326dd94d329df351d7da8ae-fc2/files/b218cfeb1bc54639af227f922bf6b817.pdf.
[11]仝小林,李修洋,趙林華,等.從“寒濕疫”角度探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中醫藥防治策略[J/OL].中醫雜志:1-6[2020-02-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17.2034.006.html.
[12]南征,王檀,仕麗,等.吉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治思路與方法[J].吉林中醫藥,2020,40(2):141-144.
[13]陳瑞,羅亞萍,徐勛華,等.基于武漢地區52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證治初探及典型病案分析[J/OL].中醫雜志:1-4[2020-02-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20.1443.002.html.
[14]張俠,李柳,戴廣川,等.南京地區42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臨床特征及中醫證候初探[J/OL].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5[2020-02-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247.r.20200219.0801.002.html.
[15]劉清泉,夏文廣,安長青,等.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作用的思考[J/OL].中醫雜志:1-2[2020-02-2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15.1057.002.html.
[16]李筱,馮敖梓,馬文,呂軍,徐安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證候學的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J/OL].世界中醫藥:1-10[2020-03-0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29.r.20200302.1415.008.html.
[17]駱長永,王雙,李雁.從“毒、瘀、虛”論治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探析[J].中國中醫急癥,2017,26(5):823-826.
[18]夏菲菲.中醫衛氣與西醫免疫的比較研究[D].青島:青島大學,2019.
(2020-02-25收稿 責任編輯: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