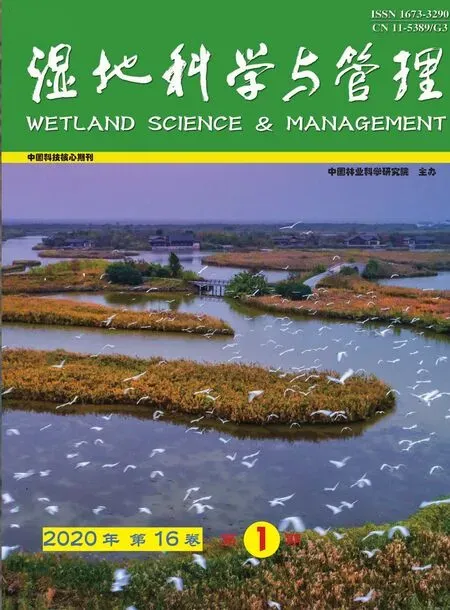甘肅鹽池灣黑頸鶴繁殖分布格局
色擁軍 竇志剛 楊巨才 王煜民 達布西力特 馬志兵 王博馳
(1 鹽池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甘肅 酒泉 736399;2 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北京 100083)
黑頸鶴(Grus nigricollis)是一種生活在高原的大型涉禽,隸屬于鶴型目鶴科鶴屬,為國家Ⅰ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被IUCN評定為易危。其分布區僅限于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在青藏高原繁殖,在云貴高原和雅魯藏布江中游及印度等地越冬(竇亮等, 2013)。鹽池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黑頸鶴已知的緯度最高的繁殖地(舒美林, 2017),自2013年以來我們就一直致力于監控鹽池灣黑頸鶴的數量,但對黑頸鶴在黨河流域的繁殖分布情況一直缺乏了解。開展鹽池灣黑頸鶴繁殖分布格局研究對于黑頸鶴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甘肅鹽池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祁連山西段高山地帶,青藏高原北緣,地處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東南部 ( 圖 1),位于 38°26′~ 39°52′ N、95°21′~ 97°10′ E,東西長約 152 km,保護區總面積136萬hm2(寶力德等, 2009)。最高海拔5 493 m,最低海拔2 600 m,氣候屬高寒干旱荒漠大陸性氣候類型。鹽池灣自然保護區地形地貌復雜多變,包括高山草原、冰川凍土、高原荒漠、河流濕地等,其中黨河濕地是鹽池灣自然保護區面積最大的濕地,是黑頸鶴繁衍生息的主要場所。鹽池灣保護區的地形地貌復雜,除黑頸鶴外,還有諸如灰鶴(Grus grus)、蓑羽鶴(Grus virgo)等35種國家Ⅰ、Ⅱ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55種有益或者有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
1.2 研究方法
1.2.1 調查方法從2013至今,對鹽池灣黑頸鶴的數量進行實時監控。2019年4月20日到2019年5月20日調查黨河濕地內牧民的分布情況,并采用觀察法對黑頸鶴鳥巢的數量、地理緯度進行了記錄。

圖1 鹽池灣黑頸鶴研究區域Fig.1 The research area of Black-necked Crane in Yanchiwan

圖2 2019年春季鹽池灣的黑頸鶴鳥巢Fig.2 The nests of Black-necked Crane in Yanchiwan in spring of 2019

圖3 黑頸鶴的巢址分布格局Fig.3 The nests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lack-necked Crane
1.2.2 數據分析運用ArcGIS 對黑頸鶴的巢址位置進行標注及數據分析,運用Origin對黑頸鶴相關數據進行做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鹽池灣黑頸鶴的繁殖分布
調查鹽池灣黑頸鶴鳥巢的地理緯度與黨河兩岸的牧民人口,共記錄黑頸鶴鳥巢35處(圖2)和牧民214人。最近鄰分析結果顯示,黑頸鶴鳥巢在黨河流域呈隨機分布,大部分的黑頸鶴巢址分布在黨河濕地東北側,共計25處,而在黨河濕地西南側僅有10處。記錄的35處黑頸鶴巢址中有25處分布在黨河濕地的下游地區,僅有10處分布在黨河濕地的上游地區(圖3)。黨河濕地東北側的雕爾力吉村牧民共計93人,黨河濕地西南側的烏蘭布勒格村有7人,南寧郭勒村114人,共計121。在黨河兩岸,牧民的數量分布與黑頸鶴的繁殖分布呈明顯的負相關(圖4)。

圖4 牧民數與黑頸鶴數量間的關系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herder and the quantity of Black-necked Crane
在調查中發現,黑頸鶴鳥巢散布在黨河濕地周圍的各村落中,其中南寧郭勒村1處,烏蘭布勒格村4處,雕爾力吉村30處,但僅位于扎丹灣子的7號、8號和10號巢分布在牧民聚居點附近,其它鳥巢都遠離聚居點,這體現出了黑頸鶴對人類干擾的回避。
2.2 黑頸鶴巢址選擇的趨同性
黑頸鶴的巢址選擇具異質性,但在海拔選擇上卻表現出顯著的趨同性,在已記錄的35處黑頸鶴鳥巢中,海拔最高為3 212 m,最低為3 068 m,平均海拔為3 112 m,最大差值不超過144 m,共有29處鳥巢分布在海拔3 100~3 140 m,占所有鳥巢的82.9%(圖5)。Han等(2017)的黑頸鶴模型預測結果顯示,黑頸鶴更加傾向在海拔2 800 m以上的地區繁殖,這與我們的調查結果相吻合。我們推斷,海拔很可能是影響黑頸鶴繁殖的主要因素。相比于其他鶴類,影響黑頸鶴繁殖的主要因素顯然與其他鳥類不同,大多數鶴類,如白頭鶴(Grus monacha),巢址水域面積、水深以及巢址植被覆蓋率是影響其繁殖的重要因素(Jiao et al,2014)。在羅布泊洼地等低海拔地區(海拔790 m)也有報導稱有黑頸鶴分布,但并沒有調查表明黑頸鶴在羅布泊繁殖,在繁殖季節出現在該地的黑頸鶴很有可能是阿爾山和昆侖山的擴張種群,或者是個別迷鳥(馬鳴等, 2011)。黑頸鶴主要集中于鹽池灣海拔3 100~3 140 m,可能是黑頸鶴對棲息地、食物資源、人類干擾等各種因素的綜合選擇。

圖5 鳥巢的海拔分布Fig.5 The altitude distribution of nests
2.3 黑頸鶴卵的孵化及數量變化
在35處黑頸鶴的巢址中,有34處巢的鶴卵都順利孵化,僅35號巢的幼鳥被天敵捕食。在秋季的統計中,觀察到30只羽翼豐滿的幼鶴,在黑頸鶴成年個體數比2018年減少10只的情況下,黑頸鶴幼年個體數卻比2018年增長7只,幼鶴數量的增長可能受益于2019年黨河濕地的限制放牧。2019年鹽池灣黑頸鶴亞成體個體僅40只,較2018年減少了12只,亞成體數量的減少可能是黑頸鶴擴散或者遷徙模式發生改變的結果,并不能說明棲息地環境惡化,尤其對于遷徙距離較遠,且壽命較長的物種更是如此。Campioni等(2019)對猛鹱(Calonectris borealis)的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猛鹱亞成體個體的遷徙模式會不斷調整,在哺乳動物中擴散行為更加明顯,而且擴散總是由雄性亞成體個體來完成。Daniel等(2003)對美國弗吉尼亞州黑熊(Ursus americanus)的研究發現,1~2歲的雄性個體有著強烈的外遷傾向。因此,鹽池灣黑頸鶴亞成體個體數量減少,歸因于其擴散或遷徙模式的改變是較為合理的。從2013年至今,鹽池灣黑頸鶴的數量有波動,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尤其以非繁殖個體較為明顯。鹽池灣自然保護區黑頸鶴種群數量穩定向好(圖6)。

圖6 鹽池灣黑頸鶴的數量變化Fig.6 The population variation of Black-necked Crane in Yanchiwan
3 討論
黨河濕地是甘肅鹽池灣自然保護區內集河流濕地、湖泊濕地和高山草甸濕地為一體的綜合性濕地(王煜明等, 2011),我們發現共計35處黑頸鶴鳥巢分布在黨河濕地,黑頸鶴鳥巢主要集中分布在黨河濕地下游,濕地兩側鳥巢數量差異大,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3.1 人類干擾
黨河濕地的草場繁盛,春季很多牧民會在濕地放牧,這時正是黑頸鶴的繁殖季節。黑頸鶴在筑巢期間對牲畜放牧尤為敏感(蔣政權等,2017),牛羊的踩踏會破壞黑頸鶴巢址及卵,家畜動物狗也會給黑頸鶴的繁殖帶來嚴重干擾。2012年竇亮等(2013)在四川若爾蓋自然保護區的調查發現,牦牛距黑頸鶴最近的距離2~3 m,并觀察到牦牛有頂撞黑頸鶴的行為,在黨河濕地也有類似現象。黨河濕地的牧民會用鐵絲柵欄將自己的草場圈起來,黑頸鶴有可能會卡在柵欄內造成死亡(王煜明等, 2011)。黨河濕地西南側牧民數量比東北側多,黑頸鶴在西南側筑巢將會受到更多的干擾,所以大部分的黑頸鶴巢址分布于黨河濕地東北側。放牧對其它鶴科動物的繁殖也有明顯影響,蒙古國烏爾茲河流域繁殖的白枕鶴(Grus vipio)也會選擇在放牧強度較低的地方筑巢,并且在沒有牲畜干擾的白枕鶴繁殖成功率更高(Bradter et al, 2005)。另外,黨河濕地南側有一條和黨河并行的公路,汽車的噪音可能會影響到黑頸鶴的繁殖,所以黑頸鶴大多將鳥巢搭建在距離公路較遠的黨河濕地東北側。
3.2 地形地貌
繁殖期間的黑頸鶴對棲息地的選擇、分布與食物的豐富程度有很大的關系(鄺粉良等, 2010)。黨河下游的濕地面積廣闊,北側山麓交錯,這給黑頸鶴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庇護所。黨河流域水生動物資源匱乏,黨河濕地下游更加寬廣的水體可能給黑頸鶴提供更加豐富的食物來源,所以大部分黑頸鶴鳥巢分布在黨河濕地下游以北的廣闊區域。
3.3 種內競爭和物種適應性
黑頸鶴到達繁殖地的時間有差異(竇亮等,2013),最先到達的黑頸鶴先占據黨河東北側最好的棲息地,隨著黑頸鶴繁殖數量的不斷增加,激烈的種內競爭使得黨河東北側的棲息地無法再容納更多的黑頸鶴,因此,10對黑頸鶴個體選擇在黨河濕地的西南側繁殖。以往的研究表明,鶴類尤其是丹頂鶴對火燒地較為敏感(吳長申等, 1999),丹頂鶴筑巢于火燒地,說明丹頂鶴繁殖具有一定的適應性(鄒紅菲等, 2003),能夠適應突然改變的環境。繁殖于黨河濕地西南側的10對黑頸鶴個體也可能適應了干擾較為嚴重的環境。
4 黑頸鶴保護建議
(1)減少放牧干擾。在鹽池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狗、牲畜和人是黑頸鶴最大的干擾因素(Zhang et al, 2017),牛羊會踩踏黑頸鶴的巢址及卵,牧民家散養的狗和野狗會偷食濕地內的鶴卵和幼鶴(Farrington et al, 2013),因此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動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黑頸鶴筑巢及孵化期間,限制牧民放牧的范圍和時間,在核心區嚴禁放牧。調節好牧場的季節性利用(竇亮等, 2013),對牧民在濕地內隨意設立柵欄的行為也應予以限制。
(2)減少噪聲干擾。杜絕濕地周圍的施工活動,同時也不允許車輛在黑頸鶴筑巢期靠近岸邊(Wu et al, 2009),以防止噪音對黑頸鶴的繁殖產生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