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分科史
張小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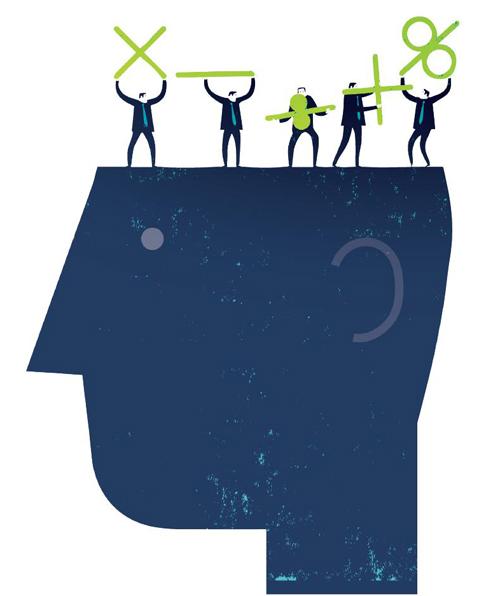
在理科生的眼里,學文科的處在鄙視鏈的最底端;在學文的人眼里,理科生提供了一大波兩性之間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的爛尾故事素材,但是……“理工科宅男”似乎還是要比“文傻”好聽得多。
文科是怎么從一開始的高級學問,淪落到鄙視鏈條底端的?
文理分家:一個多世紀前
本來,世界上所有的學問沒有分類,更沒有“理工科”這樣的概念。但隨著人類知識和科技的進步,自然科學逐漸從一團混沌的學問里分離出來,不再居于人文學問的包裹之中。
這個跡象從一個多世紀以前就開始了。工業革命的到來讓自然科學不斷發展。1830年代,“科學家”一詞被發明了,用來和“藝術家”區分。
這個詞的發明者,當然是一群科學家們。他們開始宣示自己的專業領域跟那些傳統的文學文化,也就是文科,有所不同,而當時,占主流的文科文化并沒有對這一崛起的自然科學領域予以足夠重視。
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期,包括歷史、文學、語言學和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在社會上都是占上風的。在牛津和劍橋這樣的學校,學科的領域主要由古典文學、數學和神學組成。
增加知識水平確實意味著需要增加專業化培訓,但專業化的教育并不一定會成為學科之間溝通的阻礙。
然而,到了1847年,耶魯大學打破傳統,組建專門的應用化學學院。它成為耶魯的科學學院,在1861年被命名為謝菲爾德科學院。這所學院里的三年制課程主要集中在化學、工程和獨立研究領域,它在美國提供最優秀的自然科學教育。這所學院里的學生無論學習還是生活都是跟耶魯的其他學生分開的,這兩個群體之間也不怎么來往。
人文科學教育給人帶來成功的老道理在這里受到了挑戰。這一時期,美國的自然科學開始和人文科學分割開,并“上升”到和文科平起平坐的局面。
從那以后,關于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生有沒有必要上文科課程的問題,一直都處于爭論之中。隨著科技越來越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科技從道德、美學、政治等領域中分割出去,在許多人眼里看來,這給這個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這種割裂同時造成文科生和理科生在知識上的貧瘠——就盯著眼前這點事兒,其他領域一無所知。
人文和自然科學逐漸陷入相互隔絕的狀態。比如,物理學與哲學的良性溝通,在20世紀下半葉開始隔絕。而在此之前,許多物理學家本身非常注重哲學方面的思考,比如,麥斯威爾和玻爾茲曼,在他們的研究中,哲學方面的思維活動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法國馬賽大學的物理學家卡洛·羅威利曾說,20世紀上半葉的科學家太厲害了,愛因斯坦和海森堡和迪拉克等人提出相對論和量子論,并做了所有牽涉哲學思考上的思維工作。于是20世紀的下半葉,物理學就變成了應用前人精彩絕倫的理論——當你想要應用這些理論的時候,只是應用而已,你無須再進行那些關乎哲學的思維上的活動。
后來,經濟學也不跟文科一起混了
從人文社科中脫離出來的學科還包括經濟學。
從亞里士多德到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再到20世紀中期那些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們,他們都認為除非商業活動和商業思想植根于人文,否則一個社會不會長久興盛,而一個受過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才能創造財富。
自由貿易的支持者,都傾向于把亞當·斯密稱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學家。但斯密就像他之前那些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一樣,是一位倫理學者和歷史學家——他最開始是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授邏輯學和倫理學。
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看不見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了道德體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將社會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見的手”,而是呼吁倫理道德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民眾、特別是有權勢的人物來創造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文條件。然而在他死后的兩百多年里,道德倫理作為經濟學本身的人文屬性,逐漸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當作影響其“科學性”的絆腳石——經濟學中的“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總在不斷角力。
20世紀的經濟學家仍舊被人文所影響,比方說如雷貫耳的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也學習古典文學和歷史。
南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Jacob Soll認為,過去50年中經濟學最大的變革不單是從一個學科轉變成一門更加量化的科學,而且商科也完全從人文學中分割出來。經濟學教育不再讓學生把人看成一個個由宗教、文化和社會因素塑造成的道德主體,而是把人看成單一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即便行為心理學對這種理論提出挑戰,人不是總那么理性的,但它給出的心理學解釋中也沒有深入涉及歷史和文化背景。對于人的消費行為,難道真的有一個整齊劃一的、拋開各自人文背景的購物習慣嗎?
文理科經歷過互相看不順眼的時期
英國學者查爾斯·帕希·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講,首次深刻提出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歧和沖突,并指出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文化,一方是文學知識分子,一方是科學家,猶以物理學家最有代表性。
斯諾說:由于教育背景、知識背景、歷史傳統、哲學傾向和工作方式的諸多不同,兩個文化群體即科學家群體和人文學者群體之間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相安無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擊,導致了“文學知識分子嘲笑科學家沒讀過莎士比亞、科學家嘲笑文學知識分子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文化危機。
這兩種文化的分歧和沖突已經成為整個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
斯諾認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是我們對專業化教育的過分推崇和我們的社會模式固定下來的傾向。我們總是希望一個人能很快地在某個領域達到深入的境界,而且認為專業化教育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捷徑。我們也總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我們現存的社會模式永久不變,力圖使它固定下來,按這個模式發展下去,而這卻是一種保守僵化的傾向。”
近代科學發展建立在對自然界進行分門別類研究和每門科學內部的獨立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正如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科學的興起把人推入一條專門化訓練的隧道,人越在知識方面有所進展,就越看不清整體世界,也看不清自己。
由這種專業化教育帶來的文理分科可不止是在中國有。實際上,英國的教育體制也曾在這方面被抨擊,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的學校教育讓學生在一個相對小的年齡就限制了他們所學的學科數目。在很多學者看來,增加知識水平確實意味著需要增加專業化培訓,但專業化的教育并不一定會成為學科之間溝通的阻礙。
不過,理工科在科技大躍進的年代,掌握的力量越來越大,比如他們成功地掌握了可以把地球炸掉,跟所有文科生同歸于盡的能力。文科的弱勢,越發明顯了。
中國的文理分科之路
中國的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當時傳統的私塾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知識和教育的需求了,然而新式學堂要怎么辦,也是個問題。
20世紀初,清朝政府派人出國考察,效仿法國和德國的教育模式,實行了“文實分科”,也是最早的文理分科。所謂“文科”包括歷史、文學、外語、地理等等,“實科”包括算學、物理、博物等等。當然,當時的文科生也和現在一樣要學實科的知識,實科亦然。
清政府針對分科在《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實科析》中是這樣解釋的:“至中學之宗旨,年齒已長,趣向已分,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儲治國安民之用,或令其精研藝術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文科與實科分焉。”說白了就是學了這么多年,想報國就學點實用的,沒興趣就好好搞搞文化,培養下一代。
看似安排得妥帖,操作起來卻有很大的差距,社會上對于“文實分科”的爭議也一直很大,包括分科會使學生的普通學識欠缺,從而違背了中學宗旨,而且很容易造成學生“選擇不慎,貽誤終生”的局面。
教育家蔡元培就中學分科提出過反對意見,他認為當時教育條件、學生素質都是文科重于實科,對實科的發展不利,而文科的學生在科學方面的缺乏也讓他們無法適應新時代。對于大學分科,蔡先生并不反對,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就是這樣做的。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民國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中學文理分科,實行通識教育。
1922年,中學教育從過去的四年變成了和現在一樣的六年,學生需要在高中選擇是普普通通讀書,還是學點技術方便就業,有點類似現在的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經歷了幾次反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高中最終還是取消了文理分科。
新中國成立后,人才的缺乏成了一個大問題,于是在高等教育中引進蘇聯的“專業化”模式。
蘇聯在大清洗和二戰期間損失了大批知識分子,而對展開科技競賽的各國來說,各類專業人才都是戰略資源。比如美國,在二戰中就從歐洲引進了大批科學家和工程師。為了快速培養專門人才,蘇聯采取了文理分科教育,從中學時代開始,就把學生分為文理科,以便提高培養效率。
中國對蘇聯模式的學習,最早是50年代對高校進行大合并,將同類專業院校合并為專業學院,設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使教育體制適應計劃經濟,為工業化培養人才。
雖然此時高中并沒有實行具體的文理分科,但大學的專業細化得很嚴重,實行文理分校,科類單一,行業性非常強。不同以往,工業化的社會讓理科生變成了香餑餑。
中學文理分科是在“文革”結束后,高考恢復后為了培養不同類別的人才,才再次分文理科考試,高中教育為了迎合高考,自然也變成了文理分科。
跟新中國剛剛建立時期相同的背景是,國家的現代化更需要科技類的專門人才,所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成了當時的流行語,中學的文理科,一度成為“成績不好”和“成績好”的標志。
在那之后,世界又迎來了互聯網大爆發,人文學科在創造財富的能力上無法與理工科相比,在一般人眼中地位越來越低,也是自然的了。何況人文學科既不能為星辰大海造航母,又不能“you can you up”,嘲笑理工科“然后就沒有然后了”,也不過是維護一點自尊罷了。
心愛的東西
/黎貝卡
太宰治寫過一句話:“我本想這個冬日就去死的。可正月里有人送了我一套鼠灰色細條紋的麻質和服作為新年禮物,是適合夏天穿的和服。那我還是先活到夏天吧。”
有時候,毫無道理的東西能幫我們度過糟糕的日子。心愛的物品之于我們的意義,已經無法用理性的價值來衡量。
如果給我的心愛小物排個榜單,第一位是一張被單。
和價格沒有關系,那是奶奶在我很小的時候親手縫的。
人生最遺憾的事之一是沒有陪伴奶奶度過最后的日子。但直到現在,無論我搬多少次家,無論多少次斷舍離,都會帶著她留給我的幾件東西:一枚戒指,一張被單,一些零錢。
那張紫色葡萄圖案的被單,因為蓋上去太舒服,尤其是夏天,自帶涼意,一度成為我和弟弟妹妹們每次夏夜睡覺的必爭之物。后來我贏了,以睡不好為由,徹底把它占為己有。
這些年我一直把這張被單帶在身邊。它是我出行時行李箱的必備,直到前幾年,每次出差我都帶著它,在陌生的異鄉,裹著它度過了很多個難以安睡的晚上。這幾年我不帶它了,因為用得太多,它開始有點磨破了,不舍得再用。
前不久夢到爺爺奶奶,他們剛裝修完房子,有一個巨大的客房,我建議讓我的司機住過去既可以陪他們聊天又可以接送他們。他們很開心。我也很開心。
醒來想起他們已經離開我很久了,而我再也沒有機會對他們好了。
十年前,我忙著沒心沒肺地工作和談戀愛,總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很多機會可以陪他們,不用著急,最終卻連他們最后一面都沒見上。
那天早晨我在被窩里哭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