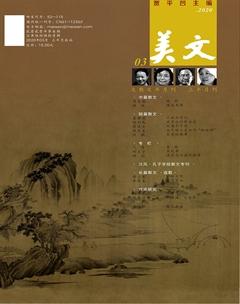小城辦學(xué)記
龔靜染
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四川給他的朋友鐘山寫(xiě)了一封信。信中寫(xiě)到:“吾開(kāi)春欲回北大,但不知路上便利否?”很明顯這封信在提前問(wèn)路,因?yàn)樗械娇箲?zhàn)勝利后,各路人馬紛紛返回,大后方呈現(xiàn)一片寂寥,氣場(chǎng)已散,自己的事業(yè)已難有作為。此時(shí)的熊十力顯得很茫然,所以他在信的最后又補(bǔ)了一句:“世局不復(fù)了,我仍不知安居處。”
熊十力于1947年仲春去了重慶,后又到武漢,4月抵達(dá)北京,結(jié)束了他在小城五通橋的一段短短的歷程。這一年他63歲。
有人說(shuō),在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哲學(xué)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xué)思想家,是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國(guó)學(xué)大師。當(dāng)然,熊十力到五通橋不為他事,也是奔著哲學(xué)而來(lái)。熊十力一生有個(gè)夙愿,就是想創(chuàng)辦一個(gè)民間性質(zhì)的“哲學(xué)研究所”。
早在1931年,他就曾向北大校長(zhǎng)蔡元培先生提起辦學(xué)之事,但沒(méi)有結(jié)果。1939年,他與馬一浮到樂(lè)山烏尤寺搞“復(fù)性書(shū)院”,這個(gè)書(shū)院就有點(diǎn)哲學(xué)研究所的意思,但由于兩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結(jié)果是不歡而散。1946年的時(shí)候,蔣介石聽(tīng)說(shuō)熊十力有辦哲學(xué)研究所的愿望,便令陶希圣打電話(huà)給湖北省主席萬(wàn)耀煌,送一百萬(wàn)元給熊十力辦研究所,但被熊當(dāng)場(chǎng)婉謝。這年六月,徐復(fù)觀(guān)將熊十力《讀經(jīng)示要》呈送蔣介石,蔣感嘆其才學(xué),令何應(yīng)欽撥款法幣二百萬(wàn)元資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絕。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復(fù)觀(guān)、陶希圣:“弟稟氣實(shí)不厚,少壯己多病,兄自昔所親見(jiàn)也。……今市中與公園咫尺,每往一次,腰部漲痛。此等衰象,確甚險(xiǎn)也。生命力已虧也,中醫(yī)所云元陽(yáng)不足也。弟因此決不辦研究所。……研究所事,千萬(wàn)無(wú)復(fù)談。吾生已六十有二,雖不敢日甚高年,而數(shù)目則已不可不謂之大,不能不自愛(ài)護(hù)也。”
很顯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體差、年紀(jì)大為由謝絕了這件事。但實(shí)際上,此時(shí)的他已經(jīng)做好去四川的準(zhǔn)備,黃海化學(xué)工業(yè)社的孫學(xué)悟先生主動(dòng)請(qǐng)他到五通橋,邀其主持黃海化學(xué)工業(yè)社的哲學(xué)研究部。“清溪前橫,峨眉在望,
是絕好的學(xué)園。”(孫學(xué)悟語(yǔ)),而這一次他是慨然應(yīng)允。
為什么他會(huì)做如此選擇呢?其實(shí)熊十力是明白人,他不愿接受蔣介石的錢(qián)是他從根本上認(rèn)為:“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十力語(yǔ)要》)所以他在給徐復(fù)觀(guān)的信中再度寫(xiě)道:
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資講學(xué),而士林唾棄。如今士類(lèi),知識(shí)品節(jié)兩不敗者無(wú)幾。知識(shí)之?dāng)。礁∶粍?wù)潛修也,品節(jié)之?dāng)。教摌s而不甘枯淡也。舉世趨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當(dāng)局如為國(guó)家培元?dú)猓詈萌挝易园财渌亍N宜麨椋槐赜僧?dāng)局以財(cái)力扶持。
孫學(xué)悟與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們重新聯(lián)系上是在1945年2月,經(jīng)馬一浮的學(xué)生王星賢牽上線(xiàn)的。結(jié)果兩人是相談甚歡,一拍即合,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橋。在熊十力看來(lái),此事正合了他“純是民間意味,則講學(xué)有效,而利在國(guó)族矣”的意愿。
其實(shí),孫學(xué)悟請(qǐng)來(lái)熊十力也不純粹為了友情或個(gè)人喜好。黃海化學(xué)工業(yè)研究社“二十五年,歷經(jīng)國(guó)難,辛苦萬(wàn)端。賴(lài)同人堅(jiān)忍不拔,潛心學(xué)術(shù),多所發(fā)明,于國(guó)內(nèi)化學(xué)工業(yè)深有協(xié)贊。復(fù)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礎(chǔ)漸趨穩(wěn)固。學(xué)悟竊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學(xué)之研究實(shí)不容緩”。(孫學(xué)悟《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緣起》)當(dāng)然,這件事跟黃海創(chuàng)始人范旭東也有很大的關(guān)系,1945年范旭東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認(rèn)為科技進(jìn)步是民族的富強(qiáng)之道,西洋科學(xué)有今日之發(fā)達(dá)并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個(gè)問(wèn)題,那就是中國(guó)哲學(xué)思想是否儲(chǔ)有發(fā)生科學(xué)之潛力?作為實(shí)業(yè)家的范旭東在把久大、永利等企業(yè)做大之后,想到的還是哲學(xué)問(wèn)題。孫學(xué)悟認(rèn)為,“哲學(xué)為科學(xué)之源,猶水之于魚(yú)、空氣之于飛鳥(niǎo)。”于是,范旭東的去世成為了一個(gè)契機(jī),對(duì)他的追思內(nèi)化為了進(jìn)行哲學(xué)研究的動(dòng)力,“今旭東先生長(zhǎng)去矣,余念此事不可復(fù)緩。爰函商諸友與旭公同志事、共肝膽者,擬于社內(nèi)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
當(dāng)時(shí)的“黃海”不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國(guó)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國(guó)科學(xué)界的一面思想旗幟,他們主張“工業(yè)的基礎(chǔ)在科學(xué),科學(xué)的基礎(chǔ)在哲學(xué)”。孫學(xué)悟就曾說(shuō)過(guò):“發(fā)展科學(xué)的要素至多,可歸納為二:一為哲學(xué)思想;一為歷史背景。哲學(xué)思想為創(chuàng)造科學(xué)精神的源泉;歷史乃自信力所依據(jù);此二者吾人認(rèn)為是培植中國(guó)科學(xué)的命根。……中國(guó)民族,本來(lái)有哲學(xué)思想的,為什么現(xiàn)代科學(xué)不產(chǎn)生于中國(guó)?這個(gè)問(wèn)題何等重要!如其放過(guò)它,我們又何能談發(fā)展中國(guó)科學(xué)?更還有甚么工業(yè)建設(shè)可言?盲人瞎馬,空費(fèi)周章,令人不勝惶悚。這是在黃海二十年最苦心憂(yōu)慮,而亟待為國(guó)家民族竭盡心力追求的一目標(biāo)。”(孫學(xué)悟《二十年試驗(yàn)室》)
其實(shí),孫學(xué)悟?qū)φ軐W(xué)的思考早已有之,他不僅是個(gè)杰出的科學(xué)家,而且對(duì)文史哲經(jīng)有很深的鉆研。孫學(xué)悟作為黃海化學(xué)社的領(lǐng)頭人,在一個(gè)搞化工的學(xué)術(shù)研究機(jī)構(gòu)創(chuàng)設(shè)哲學(xué)部,這是中國(guó)科技與哲學(xué)相結(jié)合之思想發(fā)軔,就是現(xiàn)在看來(lái),仍是中國(guó)科技界的一大盛舉。這個(gè)哲學(xué)部雖然只是黃海下的一個(gè)部門(mén),但它將承擔(dān)的卻是“置科學(xué)于生生不已大道,更以?xún)艋釃?guó)思想于科學(xué)熔爐”(孫學(xué)悟《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緣起》)的重任。
1946年8月望日(15日)這天,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正式開(kāi)講,熊十力演講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講詞,這篇講詞后來(lái)發(fā)表在了一些雜志上,又題《中國(guó)哲學(xué)與西洋科學(xué)》。熊十力在文中系統(tǒng)闡述了哲學(xué)與科學(xué)的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夫科學(xué)思想,源出哲學(xué)。科學(xué)發(fā)達(dá),哲學(xué)為其根荄”,他辦哲學(xué)研究所的愿望在五通橋這個(gè)小小的地方得到了
暫時(shí)的滿(mǎn)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這篇已成為名篇中的文章結(jié)尾,他不無(wú)深情地寫(xiě)道:
余與穎川(孫學(xué)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戰(zhàn)八年間,余嘗籌設(shè)中國(guó)哲學(xué)研究所,而世方忽視此事,經(jīng)費(fèi)無(wú)可籌集。今穎川與同社諸公紀(jì)念范旭東先生,有哲學(xué)部之創(chuàng)舉,不鄙固陋,猥約主講。余頗冀償夙愿。雖學(xué)款亦甚枯窘,然陸續(xù)增益,將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團(tuán)體可以支持永久,百世無(wú)替。余雖衰暮,猶愿與穎川及諸君子戮力此間,庶幾培得二三善種子貽之來(lái)世,旭東先生之精神其有所托矣。
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以后,專(zhuān)門(mén)制定了簡(jiǎn)章,分“學(xué)則”和“組織”兩部分。“學(xué)則”中又分教學(xué)宗旨和課程設(shè)置,其中教學(xué)宗旨規(guī)定為甲乙丙三條:“上追孔子內(nèi)圣外王之規(guī)”“遵守王陽(yáng)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顧亭林行已有恥之訓(xùn)”,并“以茲三義恭敬奉持,無(wú)敢失墜。原多士共勉之”(《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簡(jiǎn)章》)。哲學(xué)研究部的主課為中國(guó)哲學(xué)、西洋哲學(xué)、印度哲學(xué),兼治社會(huì)科學(xué)、史學(xué)、文學(xué)。要求學(xué)者須精研中外哲學(xué)大典,歷史以中國(guó)歷史為主,文學(xué)則不限于中國(guó),外國(guó)文學(xué)也要求廣泛閱讀。
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還制定了一個(gè)完整的組織機(jī)構(gòu)。設(shè)有主任、副主任,又設(shè)主講一人,研究員和兼任研究員若干。兼任研究員不駐部、不支薪,原黃海化學(xué)社的研究員也可兼任哲學(xué)部,但不兼薪。設(shè)總務(wù)長(zhǎng)一人,事務(wù)員三人,分辦會(huì)計(jì)、庶務(wù)、文書(shū)等事項(xiàng),但創(chuàng)業(yè)之初均由研究員兼任。在學(xué)員方面,不定額地招收研究生,“其資格以大學(xué)文、理、法等科卒業(yè)者為限。研究生之征集,得用考試與介紹二法。研究生修業(yè)期以三年為限。”研究生給一定津貼,待遇跟一般大學(xué)研究生相當(dāng),但鼓勵(lì)自給自足。哲學(xué)研究部也招收“特別生”,可以不受學(xué)業(yè)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實(shí)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僅如此,還設(shè)有學(xué)問(wèn)部,“凡好學(xué)之士,不拘年齡,不限資格”,都可以入學(xué)問(wèn)部,只是膳食自理。從這個(gè)組織機(jī)構(gòu)就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這個(gè)哲學(xué)研究所確系民間性質(zhì),沒(méi)有官方的任何贊助,雖然得到一些黃海化學(xué)社支持的常年經(jīng)費(fèi),但“黃海”本身就是民間團(tuán)體,且“學(xué)款亦甚枯窘”,還需要另行募集。好在正因?yàn)槭敲耖g組織,學(xué)術(shù)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導(dǎo),而里面的師生更多是不圖名利、甘于吃苦勤學(xué)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來(lái)到五通橋后,他的一些學(xué)生、朋友也追隨至此,有些是他請(qǐng)來(lái)的,有些是從其他地方轉(zhuǎn)過(guò)來(lái)的,也有慕名而至的。
當(dāng)時(shí)馬一浮有兩個(gè)學(xué)生,一個(gè)叫王準(zhǔn)(字伯尹),一個(gè)叫王培德(字星賢),可以說(shuō)是一生追隨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當(dāng)年他們除了跟馬一浮學(xué)習(xí)以外,還負(fù)責(zé)在樂(lè)山烏尤寺“復(fù)性書(shū)院”的事務(wù)、書(shū)記、繕校等工作,馬一浮的論述多由兩人記錄保存。1945年“復(fù)性書(shū)院”由樂(lè)山東歸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賢則到了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工作,其實(shí)這兩人當(dāng)年也是熊十力的學(xué)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為他整理有《王準(zhǔn)記語(yǔ)》,王星賢曾協(xié)助他匯編《十力語(yǔ)要》卷三、卷四等,這些都是在五通橋期間做的事。1946年的農(nóng)歷十月六日,馬一浮在杭州給兩人寫(xiě)過(guò)一首《秋日有懷·寄星賢伯尹五通橋》的詩(shī)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橋畔小西湖,幾處高陵望舊都。
九月已過(guò)猶少菊,江東雖好莫思鱸。
游船目送雙飛燕,世路繩穿九曲珠。
卻憶峨眉霜抱月,一天煙靄入看無(wú)。
當(dāng)年馬一浮與熊十力在樂(lè)山烏尤寺辦復(fù)性書(shū)院的時(shí)候有過(guò)不諧,最后是各奔東西。但馬一浮在這首詩(shī)的最后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為問(wèn)訊”,可見(jiàn)他不計(jì)前嫌,早已經(jīng)解開(kāi)了心中的疙瘩。王星賢后來(lái)?yè)?dān)任
黃海化學(xué)研究社的秘書(shū),一直跟隨到遷回北京,并負(fù)責(zé)參與了1951年黃海社的財(cái)產(chǎn)移交中國(guó)科學(xué)院的工作。
在學(xué)生心中,熊十力是個(gè)怪人。他的學(xué)生曹慕樊就是這樣評(píng)價(jià)他:“熊先生通脫不拘,喜怒無(wú)常,他與人處,幾乎人最后皆有反感。”(《曹慕樊先生講學(xué)記錄》)他回憶有一次黃海化學(xué)社在五通橋舉行慶典活動(dòng),請(qǐng)熊十力講話(huà),本來(lái)無(wú)非是說(shuō)幾句應(yīng)景的話(huà)的,但他一上臺(tái)就開(kāi)始大罵政府當(dāng)局,而且越罵越起勁,讓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連他的學(xué)生都深感他的言語(yǔ)放浪不羈,粗野之至。
當(dāng)年曹慕樊收到熊十力的信后,不顧待遇菲薄,辭去教職來(lái)到了五通橋,跟隨熊先生學(xué)習(xí)佛學(xué)及宋明理學(xué),后來(lái)《十力語(yǔ)要》中收入的《曹慕樊記語(yǔ)》就是曹慕樊當(dāng)年為他記錄整理的文字。他們?yōu)槭裁匆活櫼磺凶冯S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學(xué),二也是慕其人,雖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實(shí)擺脫一切世俗,蟬蛻塵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觀(guān)之”。
廢名與熊十力是同鄉(xiāng),當(dāng)年兩人曾經(jīng)住在一起討論學(xué)問(wèn),但常常是爭(zhēng)得耳紅面赤,時(shí)不時(shí)還要老拳相向,但隔一兩天又完好如初,談笑風(fēng)生。周作人就記下過(guò)這樣的事情:“……大聲爭(zhēng)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jiàn)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jiàn)廢名又來(lái),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wèn)題矣。”(周作人《懷廢名》)后來(lái)熊十力到了五通橋,與廢名幾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開(kāi)信,總見(jiàn)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獨(dú)特,如嬰兒之笑不設(shè)防。這兩人是見(jiàn)不得來(lái)離不得,但爭(zhēng)論之后很快又光風(fēng)霽月,在旁人看來(lái)熊十力就是個(gè)不通人情世故的人,這大概也是熊十力獨(dú)特人格。
任繼愈對(duì)熊十力講課的記憶深刻:“熊先生講起來(lái)如長(zhǎng)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shí),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tīng)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shí),或者認(rèn)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tīng)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聲振堂宇。”(任繼愈《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xué)》)
熊十力在五通橋的時(shí)候,也有不少朋友、學(xué)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當(dāng)時(shí)唐君毅正好在華西大學(xué)教書(shū),成都到五通橋可以走岷江順舟而下,兩日可到。師生見(jiàn)面自然高興,但熊十力每次見(jiàn)面都不談其他,只談學(xué)問(wèn),他激情似火,氣氛熾烈,直到讓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后不久又想再回去聆聽(tīng)他的“瘋言狂語(yǔ)”。后來(lái)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認(rèn)“熊先生一生孤懷,亦唯永念之而已”。
從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橋一共待了大半年時(shí)間。1947年2月后他去了重慶梁漱溟處,“十力先生自五通橋來(lái)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記),但他這一走,意味著他們之前謀劃了近一年的黃海化學(xué)社附設(shè)哲學(xué)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后,王星賢稍作盤(pán)桓去了北京中華書(shū)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從此以后,熊十力的哲學(xué)研究所夢(mèng)想煙消云散。
熊十力離開(kāi)五通橋既有經(jīng)濟(jì)的原因,也有環(huán)境的原因。
黃海化學(xué)社作為一個(gè)民間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除了最早范旭東給的一部分啟動(dòng)資金,其他資金來(lái)源都靠民間籌措。但在抗戰(zhàn)期間,“公司川西各廠(chǎng)創(chuàng)建先后六年,乃內(nèi)困于交通之阻礙,外扼于越緬之激變,加以物價(jià)飛騰,材料奇缺,全局幾瀕傾覆。”“公司各部皆在極度困難中掙扎,尤以新立之財(cái)務(wù)部及運(yùn)輸部為最。”(《永利企業(yè)檔案》)這些記載都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企業(yè)的困境。
工廠(chǎng)的情況如斯,“黃海”也絕無(wú)寬裕的可能。但“黃海”除了自力更生以外(如給外面的一些企業(yè)提供技術(shù)支持,收取一定費(fèi)用等),還在努力籌措資金。當(dāng)年范旭東
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黃海是一個(gè)孤兒,大家應(yīng)當(dāng)拿守孤的心情來(lái)?yè)嵊⒆訉?lái)有好處,那將是國(guó)家之福。”(范旭東1939年2月《黃海》卷首語(yǔ))所以,他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曾在美國(guó)借成了一筆巨款,用以實(shí)現(xiàn)他的“十廠(chǎng)建設(shè)計(jì)劃”,但他沒(méi)有忘記“黃海”,撥給了400萬(wàn)法幣用來(lái)補(bǔ)充儀器和書(shū)籍,又送“黃海”里的多名研究人員赴國(guó)外留學(xué)深造。這個(gè)時(shí)間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這難得的時(shí)機(jī),熊十力主持的黃海化學(xué)社哲學(xué)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錢(qián)剛領(lǐng)到不久,幣值便急遽跌落,不到兩年時(shí)間,這些錢(qián)已形同廢紙。
實(shí)際上在建立哲學(xué)研究部的時(shí)候,當(dāng)慣了窮社長(zhǎng)的孫學(xué)悟自然會(huì)把錢(qián)捏得緊緊的,在理事會(huì)的簡(jiǎn)章中就明確寫(xiě)到:“哲研部為發(fā)展研究工作購(gòu)書(shū)或印書(shū)等事需要重款,不能僅恃社款撥給時(shí),本會(huì)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經(jīng)費(fèi)除由本社按月?lián)馨l(fā)正款外,應(yīng)更籌募基金。”(1946年8月《黃海化學(xué)社哲學(xué)研究部理事會(huì)簡(jiǎn)章》)所謂正款,無(wú)非是人員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錢(qián)則是卡得很?chē)?yán),連筆墨信箋之類(lèi)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滿(mǎn)足,這也讓熊十力感到萬(wàn)分“枯窘”,做事頗為掣肘。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復(fù)了,我仍不知安居處”,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正處在抗戰(zhàn)結(jié)束不久,國(guó)內(nèi)形勢(shì)紛亂復(fù)雜,流亡大后方的各路人馬回到曾經(jīng)失去的土地上,所有西遷的企業(yè)、單位都紛紛復(fù)原,仿佛一夜之間,那種焦灼、緊張、艱苦的抗戰(zhàn)氣場(chǎng)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現(xiàn),而大地依然滿(mǎn)目瘡痍,百?gòu)U待興。當(dāng)時(shí)范旭東在天津等地被日本人搶占的企業(yè)已經(jīng)收復(fù),“抗戰(zhàn)多年國(guó)力疲憊萬(wàn)分……同人困于久戰(zhàn),亟欲爭(zhēng)取時(shí)間,提前促進(jìn)。”(《永利企業(yè)檔案》)復(fù)原大幕一經(jīng)拉開(kāi),同黃海化學(xué)社一起西遷到五通橋的永利川廠(chǎng)開(kāi)始了分批回到天津,而永利川廠(chǎng)實(shí)為黃海化學(xué)社的母體,黃海化學(xué)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個(gè)化學(xué)研究室,后來(lái)是“信歐美先進(jìn)諸國(guó)之成規(guī),作有系統(tǒng)之研究”才專(zhuān)門(mén)設(shè)置。永利一走,“黃海”也勢(shì)必離開(kāi),事實(shí)上從1938年就遷到五通橋的“黃海”已經(jīng)醞釀遷回北方。
1947年春天,孫學(xué)悟到上海參加黃海化學(xué)社董事會(huì),專(zhuān)門(mén)討論了復(fù)原問(wèn)題,決定新社址初選在青島,后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橋作為分社。直到1951年,撤銷(xiāo)了青島研究室,結(jié)束五通橋分社,在北京設(shè)立總社,但最后的結(jié)果是并入中科院,以黃海化學(xué)社為基礎(chǔ)成立化學(xué)研究所。在這一過(guò)程中機(jī)構(gòu)和人員都動(dòng)蕩不安,可以想象熊十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也是難以靜心做學(xué)問(wèn)的。
離開(kāi)五通橋后,各方都在爭(zhēng)取他,但他最后的人生軌跡還是并入了解放運(yùn)動(dòng)的滾滾洪流中。而改朝換代中的人們關(guān)注的已經(jīng)不是什么學(xué)問(wèn)了,對(duì)于他的舊學(xué)更是無(wú)人問(wèn)津,這已經(jīng)注定了他日漸寂寥的命運(yùn)。
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不忘創(chuàng)辦哲學(xué)研究所的事情。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學(xué),與校長(zhǎng)胡適交流時(shí)建議在北大設(shè)哲學(xué)研究所,但沒(méi)有得到回應(yīng);1948年2月,他遠(yuǎn)赴杭州講課,期間專(zhuān)門(mén)談過(guò)在浙江大學(xué)建立哲學(xué)研究所一事,但當(dāng)時(shí)的校長(zhǎng)竺可楨考慮到資金、時(shí)局等問(wèn)題,也無(wú)回應(yīng);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懇切建議:“復(fù)興中國(guó)文化,提振學(xué)術(shù)空氣,恢復(fù)民間講學(xué)。”“政府必須規(guī)設(shè)中國(guó)哲學(xué)研究所,培養(yǎng)舊學(xué)人材。”他甚至有些悲愴地寫(xiě)道:“中國(guó)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愛(ài)惜。清季迄民國(guó),凡固有學(xué)術(shù),廢絕已久。”當(dāng)然,他的這些奔走呼告皆付諸流水,事實(shí)是直到最后熊十力也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這一夢(mèng)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