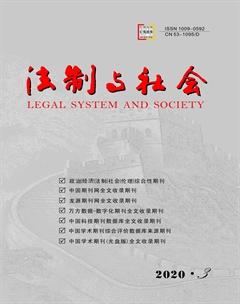論電子游戲玩法的可專利性
關(guān)鍵詞 電子游戲玩法 商業(yè)方法 可專利性
基金項目:淮陰師范學院2020屆優(yōu)秀畢業(yè)論文(設(shè)計)培育對象項目。
作者簡介:陳官民,淮陰師范學院法政學院2016級學生。
中圖分類號:D92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3.119
傳統(tǒng)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之中,電子游戲玩法作為智力活動亦或計算機軟件的一種,盡管對于電子游戲的開發(fā)與傳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一直都缺乏具體的保護方法。近年來,電子游戲抄襲侵權(quán)案件紛至沓來,使得電子游戲玩法如何保護成為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話題。
本文將結(jié)合美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商業(yè)方法可專利性判斷標準的審查標準,探索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將電子游戲玩法納入專利法保護范疇的可行性。
一、電子游戲玩法專利保護的必要性
在電子游戲同質(zhì)化嚴重的今天,卻難以對電子游戲玩法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屬性進行歸類。同為智力活動,商業(yè)方法的專利化路徑對于電子游戲玩法有著參考價值。既然商業(yè)方法,因其能夠與各種互聯(lián)網(wǎng)、計算機系統(tǒng)相關(guān)聯(lián),而逐漸取得相應(yīng)專利。那么,電子游戲玩法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問題上無疑可以參照商業(yè)方法的專利化路徑,取得自己的專利地位。且由于電子游戲玩法與智力活動規(guī)則的密切聯(lián)系,以致電子游戲玩法在專利授權(quán)問題上始終難以為公眾廣泛接受。
長期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因尚無準確定義,在同類案件審理中,法院判決意見亦難有定論,導(dǎo)致電子游戲玩法保護困難。考慮到電子游戲更新?lián)Q代非常快速,長保護周期并不利于電子游戲產(chǎn)業(yè)健康發(fā)展,所以有著較短保護周期的專利權(quán),在價值上也成為了電子游戲玩法保護的最優(yōu)解。故本文將主要研討,參照商業(yè)方法可專利性判斷標準,電子游戲玩法在可專利性命題上可成立的原因。
二、電子游戲玩法可專利性的美國經(jīng)驗
美國司法實踐提出商業(yè)方法的可專利性標準是以“實際應(yīng)用性”為主導(dǎo)的。推此及彼,電子游戲玩法在美國法視角下可專利性判斷的第一步也可考慮其是否經(jīng)受得起“實際應(yīng)用性”的檢證。在早期游戲廠商的專利申請中,不乏各類將具體的游戲玩法與游戲設(shè)備的具體鍵位捆綁在一起申請專利的案例。這種策略無疑降低了電子游戲玩法純“智力活動”特征,而使其在形式上具有了被美國專利法中對可專利客體的四種類型(新的和有用的程序、機器、產(chǎn)品或物質(zhì)成分)囊括其中的可能。但近年來,隨著電子游戲產(chǎn)業(yè)的飛速發(fā)展,電子游戲產(chǎn)業(yè)呈現(xiàn)出設(shè)備制造商與游戲內(nèi)容開發(fā)商分離的格局。
因而,這類單純的游戲內(nèi)容開發(fā)廠商客觀上不再能夠?qū)⑵溟_發(fā)的電子游戲玩法與特定的硬件設(shè)備相關(guān)聯(lián),使其符合傳統(tǒng)可專利客體要求以取得相應(yīng)專利。商業(yè)方法可專利的路徑則能為此問題提供一個有益思路。隨著商業(yè)方法可專利性判斷標準的研究逐漸深入,商業(yè)方法的可專利性已經(jīng)為大量的司法判例確定。早期的司法判例中,與電子游戲玩法最為接近的為1972年美國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的Gottschalk v. Benson一案。該案涉及一種“將二進制編碼的十進制數(shù)字(binary-coded decimal/BCD)轉(zhuǎn)換為純粹二進制數(shù)字的方法。”這一商業(yè)方法與電子游戲玩法相近之處在于兩個方面:首先,該商業(yè)方法與電子游戲玩法相同,也依賴于在電子計算機上具體呈現(xiàn)實際效果;其次,該方法與電子游戲玩法一樣,當其實際運用于一種程序之后,在任何普通計算機上都可以實現(xiàn)運行。所以該商業(yè)方法可專利與否的核心問題與電子游戲玩法可專利與否的核心問題有其一致性,即前文中所說的,一種“智力活動”的結(jié)果,當其不需要特定設(shè)備時,是否能夠單獨申請專利。而在該案中,針對這一問題,美國最高法院確立了一項判斷可專利與否的線索,即“只要存在著轉(zhuǎn)換特定客體為不同的事物或狀況這一事實”,即使一項“智力活動”創(chuàng)設(shè)的方法并不依賴特定的設(shè)備,依然是可專利的客體。將商業(yè)方法與電子游戲玩法進行橫向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既然在這一線索下,日常生活中將原材料再加工的物理程序可被認為是符合“轉(zhuǎn)換特定客體為不同事物”。那么,電子游戲開發(fā)商也是將游戲開發(fā)引擎中的素材轉(zhuǎn)換為了各種交互方法,而這些交互方法便共同構(gòu)成了電子游戲玩法。
由此可見,使電子游戲玩法符合“轉(zhuǎn)換特定客體為不同事物”這一可專利性判斷標準是存在可能性的。所以電子游戲玩法在這一路徑上存在成為可專利客體的機會。
隨著司法實踐的發(fā)展,在類似的案件中,美國法院對商業(yè)方法可專利性的判斷標準也愈發(fā)寬松。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在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INC.一案中發(fā)展出了“申請是否屬于可專利客體的問題,不應(yīng)當關(guān)注申請是否屬于專利法所規(guī)定的四個可專利客體范疇,而應(yīng)當關(guān)注申請客體的實質(zhì)特征,特別是申請客體的實際效用。”這一判斷原則。相應(yīng)的,這一原則對于電子游戲玩法也應(yīng)當具有可適用性。比如在同樣適用這一原則判斷商業(yè)方法是否可專利的Arrhythmia Research Technology Inc v. Corazonnix Corp.一案中,巡回上訴法院認為方法實現(xiàn)了將病人心臟情況客觀反映的實際應(yīng)用結(jié)果,所以是可專利的客體。我們將這一方法與電子游戲《PUBG》作比較,該游戲開創(chuàng)了一種在一張開放沙盤中,近百名玩家經(jīng)歷跳傘進入游戲場地、收集散落在場地各處的裝備武裝自己、根據(jù)游戲刷新安全區(qū)的節(jié)奏不斷移動、擊敗上述行為過程中遭遇的其他玩家,并由最終幸存玩家取得單局游戲勝利的游戲方式。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系列電子游戲玩法與此類商業(yè)方法大相徑庭,都是將人的某些行為通過不特定的輸入設(shè)備經(jīng)過一系列的程序后由輸出設(shè)備呈現(xiàn)最終圖像化的結(jié)果,借此來實現(xiàn)某種實際作用。State Street案涉方法在醫(yī)療領(lǐng)域有其獨特價值,而《PUBG》創(chuàng)設(shè)的該種游戲方法也確實解決了電子游戲中大量玩家處于同一沙盤中如何游戲的難題。可因受限于電子游戲玩法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定義不明,該玩法最終被廣泛抄襲。如果我們在電子游戲玩法的保護問題上適當?shù)匾蒙虡I(yè)方法可專利性的判斷標準,會對電子游戲玩法的保護有重大而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