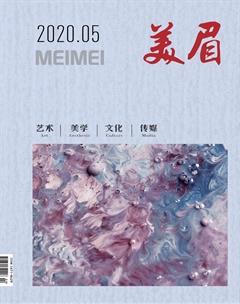“無”中生有:談“手工耿”個展的有效性

主辦:西戲
地點(diǎn):西戲·XIXILIVE
地址:杭州市濱江區(qū)西興路2333號星瀾大廈4幢301室
展期:8月2日-8月30日
在消費(fèi)時代的社會發(fā)展中,我們常常針對事物的價值來討論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對“價值”的評判也和資本流動和消費(fèi)增長捆綁在了一起。進(jìn)入消費(fèi)4.0時代,快消“產(chǎn)品”充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存在即可消費(fèi)的思想往往讓我們慢慢形成一種價值速成的慣性。那些不被資本青睞的事物,會被貼上無“用”的標(biāo)簽進(jìn)入被忽視的貨架,形同虛設(shè)。在這里,沒法被消費(fèi)的創(chuàng)造力內(nèi)容就是其中之一。

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看,事物價值的高低往往與其勞動時間成正比。但在消費(fèi)社會的發(fā)展中,我們在價值觀上出現(xiàn)了某種評判性偏差。無法被資本經(jīng)營,毫無使用價值的東西挑戰(zhàn)了價值的本質(zhì)定義。要想產(chǎn)生經(jīng)濟(jì)效益和資本增長,包括藝術(shù)在內(nèi)的商品仿佛都要迎合新的價值觀,藝術(shù)本身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價值危機(jī),新的價值定義直接向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核心發(fā)起挑戰(zhàn)。無法產(chǎn)生商業(yè)使用價值的藝術(shù)是否還能生存?或許我們需要從當(dāng)代藝術(shù)之外的現(xiàn)象來反思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新形態(tài)。

“手工耿”案例的出現(xiàn)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直接的路徑去思考藝術(shù)的問題、價值的問題和社會經(jīng)濟(jì)邏輯的問題。他的發(fā)明是荒誕無用的,這種大膽的創(chuàng)造從使用價值上看,完全是“廢物”化的個人表達(dá)。但在當(dāng)下,他的發(fā)明卻在如此幽默的情境下以“廢物”的角色向大家提供了人們對創(chuàng)造力缺失時代的某種補(bǔ)償。誰也沒有想到,一位在精神上自娛自樂,在夢想上“自給自足”的人,卻描繪了某種創(chuàng)造力的形狀,填補(bǔ)了行尸走肉般,在社會大鏈條下生活的人們對想象力的欲望。在某種意義上看,手工耿從屏幕中走出來,進(jìn)入到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語境中,實(shí)在帶著一種“無”中生有的意味。

手工耿個展以“廢物工廠”的概念提供給了觀者兩個維度。其一,它是一個荒誕的劇場,是由觀眾對手工耿“無用之功”的經(jīng)驗(yàn)與演繹聯(lián)合呈現(xiàn)的一場戲,在人們不斷沉浸在其個人的夢想趣味中時,是否可以感受到一位當(dāng)下社會的“矯正”者,通過荒誕詼諧的發(fā)明,對當(dāng)下自我無趣、枯發(fā)想象力沉重現(xiàn)實(shí)的化解。其次,它是對每一個觀者,尤其是當(dāng)代藝術(shù)領(lǐng)域從業(yè)者的一次操演式追問(performative inquiry),追問它作為一場“無用”價值操演的有效性,尤其是在當(dāng)代文化與展示的上下文語境中,何以做到真正“有用”。這種有用是對于觀者的,也是對于藝術(shù)家自我的。



手工耿的創(chuàng)作邏輯來源于他個人對于有效性的假象,即“麻煩”。雖然這些麻煩在現(xiàn)實(shí)之中幾乎沒有成立的理由。但對這些麻煩的構(gòu)想正是我們對生活所丟失的某種想象。另一方面,在這些“麻煩”背后,一種極其荒誕的趣味,也同時投射出某種社會之中情感、倫理和生活現(xiàn)實(shí)。如,“童年三件套”不銹鋼版的撥浪鼓、紙飛機(jī)和大風(fēng)車,被戲稱為“武器三件套”、“毀童年三件套”;“硬核母親節(jié)禮物:鐵掃把”長約一米八,重十斤左右,因而媽媽“不會因?yàn)榇虻揭话氡哿硕鴮擂螔吲d”。這種無厘頭的詼諧成立的條件是在地的相似的時間與人情經(jīng)驗(yàn)。這是手工耿作為一個發(fā)明家的“此地”屬性。是“麻煩”讓我們用幽默來反思社會現(xiàn)實(shí)的個人情感。手工耿不是愛迪生,也不是安迪·沃霍爾,他是一個“此時此地”中國社會生活形態(tài)下急需的一個個案。在此基礎(chǔ)上,手工耿的玩法并不是跳到所謂消費(fèi)社會的反面來與之對抗。與其相反,他通過高度消費(fèi)化的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介,不斷讓自己的發(fā)聲變得“有效”。“短視頻”和“高人氣”分別對應(yīng)“審美經(jīng)驗(yàn)”與“群體共情”兩個層面。他的短視頻以放蕩不羈的視覺形象、平靜的場景敘述和硬核的演繹再加工了發(fā)明作品本身。在短視頻媒介上,他對多感官材料的獨(dú)特的處理(或者說,藝術(shù)的處理)在幾十秒的時間內(nèi)對觀者的感受力形成極大的刺激,生成共享的快感與愉悅。同樣的發(fā)明,量產(chǎn)不能賺錢,而以短視頻再創(chuàng)作發(fā)明為他帶來了商業(yè)收益,共情的歡樂依托于此,這是近幾年,在這片土地上,大眾文化的一個特色的景觀和印記。人們在對它視頻作品消費(fèi)的同時,獲得了自我認(rèn)同的補(bǔ)償。無用的東西本身成為了一種被消費(fèi)的欲望,收割著人們的關(guān)注力,制造了荒誕景觀,反映其背后社會創(chuàng)造力匱乏的現(xiàn)實(shí)境遇。

從手工耿的創(chuàng)作邏輯上看,他作品的核心特點(diǎn)是“無用”。“無用”與“創(chuàng)造”之間是有沖突的。這種矛盾的化解同時依賴于手工耿獨(dú)特的創(chuàng)造力以及觀者群體的共情。對手工耿與他的觀眾來說,“無用”的參照系是不一致的:“地震應(yīng)急吃面神器”解決吃泡面時地震“泡面灑出來及影響口感”的問題,它來自于手工耿的工地生活中頻繁地在卡車上吃泡面的經(jīng)驗(yàn),是實(shí)用的;而對觀眾來說,這是一種生造的荒誕,是幽默的。兩者的“無用”參考系錯位源自他們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角色的差異。有趣的是,觀眾的“無用”判斷刺激了他們的快感與愉悅,以支持手工耿的“無用創(chuàng)造”作為對功利的消費(fèi)資本化社會的抵抗,而手工耿繼續(xù)創(chuàng)造,繼續(xù)引發(fā)群體共情,即錯位生成了第一個小閉環(huán)。選擇“無用”的抵抗被轉(zhuǎn)化為一種“娛樂”,這是第一重灰色幽默。這樣的“無用創(chuàng)造”小閉環(huán)再度輸入手工耿“無用”的個展中,使觀眾唯有用“文化消費(fèi)”的方式才能與他們選擇的“無用”建立一種親密,這是第二重灰色幽默。在這里,與觀眾所理解的歡樂的“無用創(chuàng)造”一致,“文化消費(fèi)”需保持某種有趣、美好和積極。這可能是對不自覺的社會抵抗第二度的消解,即消費(fèi)關(guān)系引生了一個大閉環(huán)。“無用”的灰色幽默閉環(huán),是娛樂消費(fèi)時代下,手工耿個展與手工耿“無用創(chuàng)造”共享的一組特殊的社會坐標(biāo)系(social referential grid)。

在這個坐標(biāo)之下,他的“有效”目標(biāo)再度指向了資本化社會形態(tài)。這讓我們回憶起上世紀(jì)50年代,著名藝術(shù)家安迪·沃霍爾的“藝術(shù)工廠”。這位著名的波普藝術(shù)家,用資本化邏輯去打造一個藝術(shù)帝國,用藝術(shù)進(jìn)入商業(yè)邏輯來生產(chǎn)大眾的藝術(shù)想象。在這里,手工耿的“廢物工廠”是另外一套邏輯。但最終的目的似乎同樣指向喚醒大眾對創(chuàng)造性生活的重新期望。這正是“無用”的灰色幽默閉環(huán)中必須保持有趣、美好和積極的文化消費(fèi),是一場“無用的”而“美妙的”劇場。手工耿的創(chuàng)作展示是個人化的、樂觀式的表達(dá),其有效性則在于以一場關(guān)于“生產(chǎn)”與“動能”的沉浸展示,邀請觀眾成為演員,體驗(yàn)與演繹手工耿的硬核生產(chǎn)與動力結(jié)局。以手工耿創(chuàng)造力為核心的“無用”戲劇,化解“廢物”與“工廠”之間天然的沖突,點(diǎn)燃人們的靈感與熱情,使自我調(diào)侃的“廢物”啟動對生活自主能動的重新把控。這也是一種“工廠”的角色,一種反工業(yè)4.0時代所特有的情態(tài)。
在這個方向上,許多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們在自我專業(yè)訓(xùn)練的背景和資本運(yùn)作的加持之下,往往未能走到一個合理價值體現(xiàn)的最終終點(diǎn),反而一位非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愛好者,提供給大眾的反思問題來的更加有效。這對于陷入生命力疲乏的國內(nèi)當(dāng)代藝術(shù)現(xiàn)狀,不得不說,是某種無中生有式的刺激。手工耿的出現(xiàn),勢必真實(shí)地觸及到了當(dāng)下最為熱門的當(dāng)代藝術(shù)討論的話題,而面對之前很多不痛不癢的討論,它顯得格外直接、真實(shí)、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