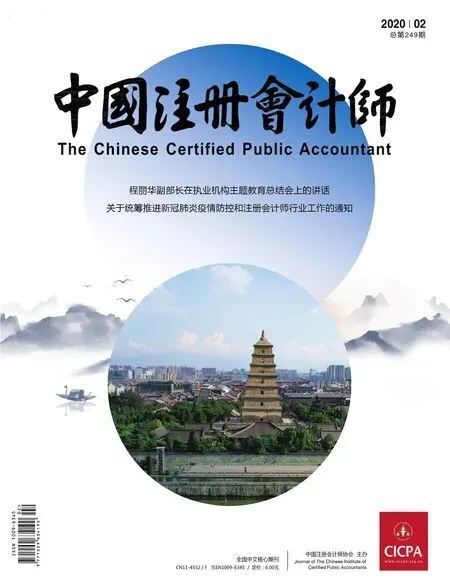庫存股制度下股票回購市場效應的實證研究
賀恩遠
一、引言
股票回購指上市公司使用自有資金從市場上回購本公司股票的行為,是上市公司優化治理結構、穩定股價的重要手段。股票回購起源于美國,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政府為鼓勵企業投資,限制上市公司以現金形式發放股利,上市公司開始采用股票回購的形式回報投資者。2000年,美國證監會(SEC)制定10b5-1規則后,上市公司回購股票開始蓬勃發展。2018年度,美國上市公司回購了7979億美元的股票,同期現金分紅4563億美元,股票回購已經遠超現金分紅,成為股東回報的主要來源。
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回購歷史則較短,1992年原國家體改委發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1994年《公司法》正式施行,兩個立法對股票回購的要求是“原則禁止,例外允許”。2005年,出于便利股權分置改革和提振股市的需要,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回購社會公眾股份管理辦法(試行)》,同年《公司法》修改通過,對涉及股票回購的條文進行修訂。2008年10月,證監會發布《關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股份的補充規定》,對報批程序進行簡化,股票回購在A股市場開始興起。
2018年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公司法》有關公司股票回購的規定進行了修改,增加了股票回購的兩種情形(將股份用于轉換上市公司發行的可轉債和上市公司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所必需),簡化了回購決策程序,提高了回購股份比例上限(公司合計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百分之十),延長了公司持有所回購股票的期限(允許公司在特定情況下持有本公司股票不超過3年)。自此,我國上市公司正式建立庫存股制度。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綜述
股票回購對股價的影響已被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廣泛的研究。Vermaelen(1981)采用事件研究法對美國上市公司1962年至1977年要約回購事件和1970年至1978年公開市場回購數據進行研究,發現要約回購和公開市場回購在公告前一日和公告當日都存在顯著為正的收益,股票回購存在正的公告效應,異常收益率隨回購溢價率的提高而增大,但在公告之前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Lkenberry、Lakonishok和Vermaelen(1995)基于1980年至1990年公開市場回購數據,發現上市公司股票回購的短期效應并不顯著,回購后3年內存在高達8.65%的超常收益,長期效應較為顯著;同時還發現回購比例越大、公司規模越小,回購公告效應越大。Stephens和Weisbach(1998)基于1981年至1990年公開市場回購數據,發現在事件前后3天窗口期內存在2.69%的超常收益。Jagannathan和Stephens(2003)基于1986年至1996年市場回購數據,對回購頻次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回購公告效應進行了對比,發現不經常回購的公司產生的公告效應平均高達3.36%,高于經常回購和頻繁回購的公司。Erik lie(2004)的研究發現進行回購的上市公司相較于未進行回購的上市公司,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經營業績有顯著的提高。Gustavo Grullon和Roni Miehaely(2004)研究發現總資產、市凈率與股價表現負相關,回購規模與股價表現正相關。
(二)國內文獻綜述
國內對股票回購的研究文獻較少,主要集中在回購動機、回購的市場效應以及回購對公司經營的影響。韓冰(2000)通過研究我國早期回購案例發現,回購動機多是為了改變所有權結構。徐國棟和遲銘奎(2003)發現,回購公告日和實施日股票均表現出顯著的正收益,回購后公司ROE和EPS均顯著提高。梁麗珍(2006)研究了公告效應的影響因素,發現收入增長率、回購比例與異常收益正相關,公司規模、PB、資本支出和ROE與異常收益負相關。馬明(2009)研究指出證券市場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問題和信息泄露問題,股票回購向市場傳遞了公司股價被低估的信號。李業彬(2016年)發現A股市場不同類型的股票回購存在不同的公告效應,以購回離職員工所持限制性股票為目的的股票回購不存在公告效應,以消除公司股價低估為目的的股票回購存在顯著的正向公告效應,公告日前存在股價累計超額收益顯著為負的區間。林兆祺(2017年)研究了2011年至2017年3月我國A股市場股票回購事件,實證結果表明股票回購的宣告會導致超常收益,超常收益的大小與宣告前股價表現負相關,且國有企業股票回購公告后超常收益率相對較高。
(三)本文研究的突破點
2018年10月26日發布的《公司法》修正案,允許上市公司在出于特定目的回購本公司股票的情況下,即:將股份用于員工持股計劃或者股權激勵,將股份用于轉換上市公司發行的可轉換為股票的公司債券等上市公司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所必需的情形,可以持有不超過三年,即建立了上市公司庫存股制度。而在此之前,上市公司回購的擬用于股權激勵的股票須在六個月內轉讓或者注銷,用于穩定股價而回購的股票應當自完成之日起十日內注銷。制度的變化預計將對股票回購的市場效應產生不同的影響,而目前尚沒有文獻對此進行專門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嚴格的樣本篩選,構建了上市公司回購股票并持有的組(以下稱為“持有組”),通過事件分析法研究回購方案公告前后股票異常收益情況。同時作為對比,篩選2011年至2018年6月已完成的上市公司回購股票并注銷的案例做為注銷組(以下稱為“注銷組”),通過對比的方法研究庫存股制度的市場效應。最后通過回歸分析的方法量化不同解釋變量對異常收益的影響,對比研究庫存股制度下解釋變量對異常收益作用的變化情況。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所采用的上市公司股票回購數據均來自于Wind資訊,并通過手動查詢的方式對數據一一核實。其中,持有組為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間公告并開始實施股票回購的公司。并按照以下原則對樣本進行了篩選:(1)剔除金融公司樣本;(2)剔除定向回購樣本;(3)剔除僅公告了回購方案而未開始實施回購的樣本;(4)剔除多次進行回購的公司;(5)對于2018年11月之前已經宣告并實施的回購,在2018年11月之后繼續實施第二期的,為避免前次回購對股價的影響,將其剔除。

表1 解釋變量的經濟意義及取值方法
注銷組樣本為2011年至2018年6月間完成回購并注銷股票的公司,其篩選原則與上述(1)至(3)相同,但對于進行多次回購的公司,只保留第一次回購研究樣本。
篩選后,持有組共獲得有效樣本119個,注銷組獲得有效樣本93個。
(二)事件研究方法與步驟
事件研究法是研究特定事件對公司股價波動影響的常用方法,假設在投資者是理性的情況下,上市公司股票價格會迅速對事件的發生作出反應。
1.事件日、窗口期、估計期
上市公司公告股票回購方案是上市公司第一次向市場公開回購信息,因此本文將上市公司公告回購方案當天作為事件日(t=0)。窗口期設定為(-15,40),即事件日前15個交易日至事件日后40個交易日。本文將估計期長度確定為250個交易日,因此計算正常收益率的估計期為(-265,-15)。
2.異常收益率
正常收益率是基于估計期數據計算的股票的期望收益,采用市場模型來計算。該模型基于CAPM模型,假設股票收益率與市場組合收益率有線性關系:

式中,Ri,t和Rm,t表示t日股票i和市場組合的收益率。基于估計期股票收益率和市場組合收益率數據,通過上述模型估計出樣本公司的和。
對于在滬市、深市主板、中小板、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分別以上證綜指(000001)、深證成指(399001)、中小板指(399005)和創業板指(399006)的收益率作為市場組合收益率。
收益率的計算采用取自然對數的方式,即:
Return=Ln(Pt/ Pt-1)
計算正常收益率的基本模型為:

異常收益率的計算公式如下:

平均異常收益率(AR)計算公式如下:

累計異常收益率(CAR)計算公式如下:

3.異常收益顯著性檢驗
統計檢驗的目的在于確定窗口期內股票異常波動的顯著性水平,本文以標準化殘差法(Standardized Residual Method)進行檢驗,此辦法由Patell(1976)首先提出,是對傳統t值檢驗法的改進。計算公式為:

表2 持有組平均異常收益率及累計異常收益率

式中:

(三)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設定
為考察股票回購信息公告后,股價異常波動的影響因素,本文結合國內外研究結果,認為股票回購方案公告后異常收益的大小可能與回購比例、盈利能力、規模大小、股權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市場估值等多個因素有關,并設定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予以檢驗。各解釋變量的含義及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

四、研究結果
(一)股票回購引致的市場反應
持有組和注銷組窗口期內AR和CAR值以及顯著性檢驗結果分別見表2和表3所示。由于數據較多,這里僅列出具有顯著性的檢驗結果。
由表2和表3可見,持有組和注銷組在事件日當天均有顯著的異常正收益,均在1%顯著性水平以上,說明股票回購信息對提振股票價格有顯著作用。(-15,-1)內未出現股票異常收益顯著為正的情形,可以推斷在公告日前沒有發生明顯的信息泄露。
持有組(-15,-1)內僅有4個交易日出現股票異常收益顯著為負的情形,置信水平為90%;而注銷組(-15,-1)內存在9個交易日股票異常收益顯著為負的情形,其中有4個交易日在1%顯著性水平以上。同時,持有組CAR(-15,-1)為-0.0235,股價平均異常收益為-2.32%;注銷組CAR(-15,-1)為-0.0678,股價平均異常收益為-6.56%,均在1%顯著性水平以上。說明回購信息公告前,存在著股價異常下跌的情形;但是在庫存股制度下,股票異常下跌的幅度明顯小于回購并注銷的組合。
股票回購公告后,持有組在t=1日即出現股價回調,在連續五個交易日內CAR(0,4)值為0.0142,股價平均累計上漲幅度為1.43%。注銷組在t=1日繼續取得正的異常收益,在t=2日股票價格開始出現回調,CAR(0,4)值為0.0312,股價平均累計上漲3.17%。說明在原回購制度下,我國上市公司公告股票回購消息后市場反應更為激烈,而在庫存股制度下,由于所回購的股票繼續為公司持有,后續可能還會在市場上流通,所以投資者對股價走勢的判斷更為謹慎,多空爭奪更為激烈。后續隨著股票回購方案的實施,股票不斷出現正的或負的異常收益,在(0,40)內,持有組平均累計上漲3.76%,注銷組平均累計上漲5.29%。圖1為(-15,40)窗口期內CAR走勢情況,兩組在窗口期內走勢較為相似。圖2為(0,40)窗口期內CAR走勢情況,在回購方案公告后,注銷組CAR高于持有組水平。

表3 注銷組平均異常收益率及累計異常收益率
(二)多元回歸模型檢驗結果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
表4和表5分別對兩組樣本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公告日前持有組CAR(-40,-1)的平均值明顯小于注銷組,說明公告股票回購方案前,注銷組股票下跌幅度更大。兩組樣本數據中,資產負債率、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回購比例均值和中位數均較為接近。兩組樣本公司總資產規模中位數接近,但持有組總資產的平均數小于注銷組,是因為持有組公司數量較多。從股東性質來看,持有組平均值小于注銷組,說明持有組中非國有企業比重更大。持有組市凈率平均數和中位數均低于注銷組,說明持有組中公司估值水平更低。而持有組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數和中位數均低于注銷組,顯示出持有組公司盈利能力低于注銷組。
2.模型檢驗
首先通過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檢驗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表6中DEB和LnSize的相關系數為0.71,大于0.70,存在相關性。但通過檢驗模型中方差膨脹因子VIF,變量之間VIF值最高為2.69,最低為1.07。通常認為VIF小于10時,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持有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7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70,同時變量之間VIF值最高為2.10,最低為1.22,因此注銷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通過BP(Breush-Pagan)檢驗法對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注銷組Prob.Chi2值為0.6368,因此接受隨機擾動項方差是同方差的原假設,模型不存在異方差。而持有組Prob.Chi2值為0.0370,因此拒絕隨機擾動項方差是同方差的原假設,該模型存在異方差。
3.回歸結果

圖1 (-15,40)窗口期內CAR走勢情況

圖2 (0,40)窗口期內CAR走勢情況

表4 持有組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5 注銷組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由于持有組模型存在異方差,因此不能直接采用OLS法進行估計,為此本文采用了懷特標準誤法對持有組模型進行修正。表8是回歸統計結果。
由上述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持有組回歸的R2小于注銷組,說明解釋變量對持有組股票異常收益的解釋能力弱于注銷組,也就是說在庫存股制度下對股價波動的影響因素更多。持有組和注銷組F值分別為1.3830和2.3673,分別在10%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說明解釋變量對CAR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在持有組回歸結果中只有CAR(-40,-1)一個解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在注銷組回歸結果中只有市凈率一個解釋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此,將模型中P值較大的解釋變量刪除,重新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所示。
由上表可見,將解釋能力不顯著的變量從模型中刪除后,持有組和注銷組模型中Adj_R2值均有所提高,說明模型擬合程度提高;同時F值顯著性水平也有所提高,分別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上。
4.回歸結果分析
(1)與注銷組相比,持有組解釋變量擬合程度降低,說明我國建立上市公司庫存股制度后,上市公司公告股票回購方案后40個交易日內,股價波動影響因素增多。從模型回歸結果來看,公告前股價走勢對公告后股票異常波動有影響,在持有組中,回歸系數為正,顯著性水平在5%以上,公告前股價走勢與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正相關。而在注銷組中,回歸系數為負,公告前股價走勢與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負相關。回歸結果說明,庫存股制度實施后上市公司回購自身股票的動機更為復雜。2018年11月以來,上市公司公告的回購方案中多數并未明確具體用途,只是籠統地說明將來用于股權激勵或員工持股,或者將股份用于轉換上市公司發行的可轉債,或者注銷。由于上市公司回購股票后可以持有不超過3年,因此上市公司可以在3年內擇機確定具體用途。上市公司持有庫存股用途的增多,使得回購方案公告后向市場傳達的并非完全是股價低估的信號,因而回購方案公告前公司股價走勢與回購后股票異常收益正相關。

表6 持有組各變量相關系數

表7 注銷組各變量相關系數

表8 回歸統計結果
在注銷組中,公告的回購方案主要集中在2015至2018年上半年,占比超過樣本的三分之二。這一時期正值我國A股市場由牛市轉為熊市的時期,上市公司推出的股票回購方案中明確說明回購完成后將于10日內注銷。因而給市場傳達的更多的是公司股價低估的信號,使得回購方案公告前股價越是超跌,公告后股價反彈幅度越大。
(2)在持有組中資產負債率、股權集中度和實際控制人性質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在注銷組中,將這三個解釋變量從模型中刪除后,模型解釋能力反而提高了,說明這三個解釋變量對股票異常收益未有顯著影響。
(3)資產總額在兩個模型中回歸系數均為負數,說明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越大,回購信息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越小。信息經濟學認為,公司規模越大,獲得的關注可能越小,也就越有可能被低估。Vermaelen(1981)、Comment和Jarrell(1991)等人研究也發現,規模較小的公司更傾向于獲得更大的股票回購公告效應。本文的研究結果支持這一結論。在注銷組中,資產規模這一解釋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而在持有組中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庫存股制度下,資產規模對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影響的顯著性下降。
(4)在持有組中市凈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對股票回購方案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沒有顯著影響,將其從模型中刪除后,模型解釋能力反而提高。而在注銷組中,市凈率與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呈顯著的負相關,在1%顯著性水平上。同時,股票異常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呈正相關。說明在注銷組中,市場估值更低、盈利能力更好的股票,回購方案公告后異常收益越高。這也進一步說明了,上市公司持有庫存股的用途增多后,回購方案向市場傳達的并非完全是股價低估的信號。

表9 變量調整后回歸統計結果
(5)回購比例在持有組中,與股票異常收益正相關,在10%顯著性水平上;在注銷組中也與股票異常收益正相關,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進一步說明,在注銷組中,回購方案向市場傳遞的更多是股價低估的信號,市場更多的是關注公司估值是否低估,而不僅是回購股票的數量。而在持有組中,由于上市公司回購方案傳遞的信號更加復雜,市場的正向反應更多的是基于股票回購后流通股減少、每股盈利增加,因此在庫存股制度下,回購比例對回購方案公告后股價異常收益的影響力提高。
五、結論
結合已有研究結果,本文通過對比研究的方法,對上市公司在庫存股制度建立后公告股票回購方案的市場效應進行研究,得到以下重要結論:
《公司法》修改后,實施股票回購的上市公司數量大幅增加,回購方案公告前15個交易日股價平均異常收益為-2.32%,遠低于公司法修改前的-6.56%。主要是因為公司法修改前,上市公司出于穩定股價的目的而進行的股票回購,需要在回購完成后10日內注銷,因此回購公告向市場傳遞的更多是公司股價低估。而在庫存股制度下,上市公司在回購完成后,可以持有不超過三年,后續可用于股權激勵、員工持股以及轉換上市公司發行的可轉債,市場上流通股的減少是暫時性的,因此回購方案向市場傳遞的信號更加復雜,并非完全是股價低估的信號。
基于上述原因,雖然在回購方案公告當日,上市公司股價均表現出顯著的正收益,但在公司法修改之前,回購方案公告后40個交易日內股價上漲幅度更大,說明在庫存股制度下,股票回購公告的市場效應降低。
通過多元回歸分析得出,庫存股制度下股票回購方案公告后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增多,公告后股價的走勢并非是對公告前股票異常下跌的修正。上市公司規模與股票回購的公告效應負相關,但影響力的顯著性降低。庫存股制度實施前,市凈率、凈資產收益率分別與回購公告后股票異常收益成負相關、正相關關系,回購比例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庫存股制度實施后,市凈率、凈資產收益率對異常收益不再具有解釋能力,回購比例的影響更加顯著。表明在庫存股制度下,股票回購公告后市場的正向波動并非是對盈利能力強、低估值公司股價的修復,更多的是基于股票回購后流通股減少、每股盈利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