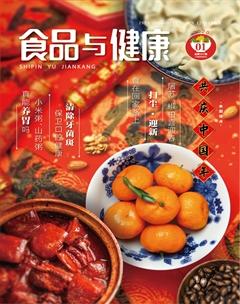阿司匹林,“百年靈藥”的前世今生
譚昭麟

阿司匹林(Aspirin),又稱乙酰水楊酸,是醫藥史上的三大經典藥物之一,自1897年合成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應用歷史。這種毫不起眼的白色小藥片最開始只是解熱鎮痛的感冒藥。但隨著在臨床上的不斷應用,人們發現它還可以治療風濕痛,預防心血管疾病、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風的發病風險,甚至對靜脈血栓、腸癌、肺癌、乳腺癌、白內障、偏頭痛、不孕癥、皰疹、阿爾茲海默癥均有防治作用,其累計銷量已達幾十萬億片。至今,人們還在不斷發現它的新功能。關于阿司匹林,每年都有超過2500篇文獻發表。可以說,阿司匹林不僅是一款成功的商業產品,也是一種“靈藥”。
那么,阿司匹林是怎樣問世的呢?它又如何從一種普通感冒藥變成家庭必備的救命藥呢?故事還要從一株我們最為熟悉的植物說起……
“出身”柳樹
柳樹,這種讓無數文人墨客不吝筆墨描摹、歌詠的植物竟然還可以治病?沒錯,它的體內含有一種可以消炎鎮痛的物質,阿司匹林的前體——水楊酸。柳樹用于治病始于何時?我國民間早有“榆樹救荒,柳樹祛病”的說法。距今3500年前的古埃及《埃伯斯紙草書》中明確提到,柳樹可以治療咳嗽、消炎止痛。1000年后,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指出,柳樹皮可以用來退燒和減輕分娩的疼痛。說明古人早已在觀察自然、探索自然的過程中,認識到了柳樹的醫用價值。
可惜的是,隨著中世紀的降臨,西方隨即陷入了黑暗和愚昧之中。柳樹用于治病的藥方同幾千年積累下來的醫學知識一起消失了。18世紀,它在西方重見天日,一位名叫愛德華·斯通的英國牧師的靈光一現。
1758年的一個夏天,愛德華·斯通牧師跟往常一樣,在家鄉一條名叫“考門”的小溪邊散步。溪水兩岸綠柳成蔭,景色宜人,讓斯通牧師感覺非常愜意。或許是因為無聊,或許是出于純粹的好奇心,斯通牧師掰下一塊柳樹皮,放進嘴里咀嚼起來——一股苦澀而又熟悉的味道立刻彌散開來。斯通牧師想了好一會兒,才想起來這味道跟金雞納樹皮——當時用于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幾乎完全一樣。
當時的英國瘧疾肆虐,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克倫威爾正是死于這種疾病。雖然,當時人們已經找到了對抗瘧疾的特效藥金雞納樹皮,但其價格昂貴,常常供不應求。西班牙壟斷了這種只生長在中美洲的珍貴藥材的貿易。
擅長思考的斯通牧師突發奇想:既然柳樹皮的味道跟金雞納樹皮的味道一模一樣,那么柳樹皮可不可以用來代替金雞納樹皮治療瘧疾?想到這里,激動的斯通牧師馬上掏出小刀,開始削取柳樹上的樹皮。最終,他抱著一大捆樹皮來到了一座磨坊里,要求磨坊主把樹皮烘干。磨坊主并沒有拒絕牧師的古怪請求,他把自己用來烘焙面包的烤爐借給牧師使用。于是,斯通牧師用一座磨坊的面包烤爐,得到了約1磅重的柳樹皮粉末。
接下來,斯通牧師開始到處尋找瘧疾患者并給他們服用自己的新藥。經過長達5年的實驗和觀察之后,斯通牧師發現:柳樹皮可以治愈大部分瘧疾患者。1763年,斯通牧師向英國皇家學會寫信,正式公布了自己的重大發現。這是阿司匹林發現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有趣的是,斯通牧師雖然發現了柳樹皮的醫學價值,但他完全曲解了柳樹皮的功效。斯通牧師一直認為柳樹皮和金雞納樹皮一樣,可以治療瘧疾,但后來醫學界發現,柳樹皮中的有效物質只能起到退燒等緩解瘧疾癥狀的作用,并不能真正殺死瘧原蟲。而斯通牧師治愈的大部分“瘧疾患者”,身患的可能只是與瘧疾癥狀類似的其他疾病。盡管如此,這一誤會并不影響斯通牧師的偉大——就像哥倫布一直錯誤地認為自己到達了印度,但誰都不會否認,他發現了新大陸。
因戰爭備受關注
19世紀初,拿破侖加冕法蘭西皇帝,英法沖突愈演愈烈,英國皇家海軍隨即封鎖了法國與美洲之間的商業貿易。而西班牙由于與法國結盟,也受到了英國的封鎖,金雞納樹皮的貿易航線中斷了。歐洲大陸對金雞納樹皮的迫切需求促使化學家們分離出了金雞納樹皮的活性成分——奎寧。作為金雞納樹皮的替代品,柳樹皮活性成分的提取得到了更高的關注。
1828年,慕尼黑大學藥劑學教授約瑟夫·畢希納從柳樹皮中提煉出了柳苷。1838年,意大利科學家拉法萊埃·皮里亞從柳苷中分離出了活性物質——水楊酸。最初,水楊酸并未得到廣泛應用,因為水楊酸是一種非常強的有機酸,服用后會刺激口腔、食道和胃,讓人十分不適。相比水楊酸,人們還是更傾向于服用柳苷,或是含有水楊酸的柳樹皮。
1897年,水楊酸類藥物已經成為治療風濕熱和關節炎的常用藥,德國制藥巨頭拜耳公司決定嘗試找到水楊酸的替代品——一種藥效類似水楊酸,但卻沒有水楊酸不良反應的理想藥物。這項任務落在了3位德國化學家海因里希·德雷澤、阿圖爾·艾亨格倫和費利克斯·霍夫曼的頭上。這三個人后來被稱作 “阿司匹林三人組”。
青年化學家費利克斯·霍夫曼首先注意到,水楊酸的分子結構是由6個碳原子組成的苯環和連在苯環上的2個基團——羥基和羧基組成的。當水楊酸羥基基團接觸胃壁時,會對胃黏膜產生強烈的刺激,這正是水楊酸對人體產生副作用的原因。霍夫曼設想,如果用乙酰基團取代羥基,是不是就可以減輕水楊酸對人體的副作用。通俗來講,就是把水楊酸上的強酸換成弱酸。遵循這一思路,霍夫曼把水楊酸和乙酸酐放在一起加熱回流,最終得到了乙酰水楊酸——這正是今天阿司匹林的有效成分。
與水楊酸相比,乙酰水楊酸不僅療效更佳,沒有不良反應,而且還增加了一種重要作用——止痛。拜耳公司立即意識到了乙酰水楊酸的巨大價值,并將其名定為阿司匹林(aspirin)。其中a代表乙酰化合物(acetylation),spir代表繡線菊(Spiraea ulmaria,繡線菊屬植物也含有水楊酸,其含量甚至比柳樹中更多),in作為后綴。
1899年7月,阿司匹林投入生產。這枚神奇藥片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大流感”推動銷量
阿司匹林問世之初,只作為治療風濕類疾病和消炎止痛的藥物登場。真正使它名揚天下的是1918~1919年的全球性大流感。一戰末期,美國對德宣戰,并向歐洲大陸派兵。于是,這場起源于美國的流感就隨著美國大兵來到了歐洲。它首先席卷了法國,然后進入了西班牙和英國,最后從歐洲傳到中東,進而侵入亞洲。
可別以為流感只是一種很輕微的疾病,在沒有特效藥的20世紀初,流感病毒如同“死神”一樣。匈牙利稱大流感為“黑死長鞭”,德國人管它叫“晴天霹靂”,瑞士人則稱之為“束手無策”。死于流感的人數在2500萬至4000萬之間,比死于一戰的人數還多。
每逢疾病大流行,人們難免會病急亂投醫。阿司匹林雖然并不能殺死流感病毒,但它退熱止痛的作用可以有效緩解流感病人高燒、頭痛的癥狀,減輕病人痛苦,因此迅速獲得了人們的青睞。沒有患病的人要求服用它來預防,患了病的人則對它產生了依賴,有的醫生甚至把它當作安慰劑開給病人。因此,盡管阿司匹林并不是大流感的特效藥,但它仍在人類抗擊流感的戰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那以后,阿司匹林的市場占有率不斷攀升,一個屬于阿司匹林的時代來臨了。
但是,隨著阿司匹林的廣泛應用,它的副作用也愈加凸顯,即藥物對胃黏膜的刺激作用。盡管與水楊酸相比,阿司匹林出現不良反應的機率低很多,但考慮到服用阿司匹林的人數基數太大,這一現象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1938年,英國赫爾市的一名內科醫生阿瑟·杜斯韋特在給一位剛服用過阿司匹林的病人做胃鏡檢查時,意外發現胃壁上有部分阿司匹林未被消化,而且藥片殘留的部位呈紅色,說明未消化的阿司匹林對胃部產生了刺激。杜斯韋特認真研究了這一問題,他發現使病人胃出血的原因在于阿司匹林在胃中的溶解速度太慢,致使藥物附著在胃壁上,造成胃黏膜損傷。杜斯韋特在阿司匹林里加入了鈣,使阿司匹林的溶解速度大大加快了。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加鈣后藥品容易受潮,使阿司匹林變得不易保存。
戰爭期間需要有穩定的阿司匹林供應。1941年,英國利高曼公司斯克魯頓工程師著手解決這一問題。最終,斯克魯頓發現,添加碳酸鈣作為輔料,再經過機器沖壓,就能制成快速溶解的阿司匹林。這一方法后來經過喬治·科爾曼·格林的改進,生產出了現在不易損傷胃黏膜的易溶阿司匹林。
但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對乙酰氨基酚(撲熱息痛)、異丁苯丙酸(布洛芬)等止痛藥的發現與應用,阿司匹林在市場中的地位從一家獨大迅速跌落成三足鼎立。比起這款在上世紀末發明的老藥,人們更愿意相信新產品帶來的療效。阿司匹林在競爭中節節敗退,它還會再現以前的輝煌嗎?
催生諾貝爾獎得主
阿司匹林的困境因其作用機制的進一步明確而打破,而這要歸功于科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名字:英國科學家約翰·范恩。
在此之前,人們已經知道:生物體內存在一種叫做前列腺素的物質,當細胞受到刺激時,會釋放前列腺素,使機體紅腫、發熱、疼痛和發炎。于是,范恩猜想,阿司匹林的作用是不是就在于阻止前列腺素的合成?在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實驗之后,范恩終于證實了自己的猜想,并于1971年發表了自己的大作《阿司匹林類藥物阻滯前列腺素合成的機制》,標志著人類終于揭開了阿司匹林作用機理的神秘面紗。
然而,范恩這一研究更加深遠的意義在于,他使人們認識到了阿司匹林更加重要的一個作用——抗凝血。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一種細胞,在一滴血中有上百萬個血小板。它在人體中的作用是:一旦血管爆裂,發生出血,血小板就會堵在傷口上,防止血流繼續流出,這一過程叫血小板凝聚。對于正常人體來說,血小板凝聚是機體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但對血栓患者來說,在沒有受傷的地方發生凝血,就會形成血栓栓塞,導致心肌梗死、腦卒中等嚴重疾病。
范恩發現,促使血小板凝聚的介質也是一種前列腺素——凝血惡烷-A2,而阿司匹林可以阻斷凝血惡烷的產生,從而阻止血小板凝聚。如此一來,只要服用阿司匹林就可以預防血栓發生。這被看作是近代醫學的重大發現之一。因此卓越貢獻,發現阿司匹林作用機理的約翰·范恩,發現前列腺素的蘇內·貝里斯特羅姆和發現凝血惡烷的本特·薩米爾松共同獲得了198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預防中風和心血管疾病的奇效一出,曾經的“靈藥”又回到了大眾的視野,成為家家必備的救命藥。但這并不是阿司匹林的全部傳奇故事。隨著人們對阿司匹林的作用機制有更多的了解,醫學界掀起了對阿司匹林研究的熱潮。
1992年,人們發現阿司匹林可以治療因多發性腦梗死導致的老年癡呆癥,幾年之后,人們又發現阿司匹林可以治療阿爾茲海默癥。對于未出生的患病胎兒,阿司匹林也有奇效。先兆子癇是一種妊娠期間可能出現的病癥,發病率高達8%,其原因是胎盤內形成的小血栓,而阿司匹林可以預防胎盤中血栓的形成,使先兆子癇的發病率減少15%。
另外,阿司匹林對牙周炎、白內障、偏頭痛、不孕不育癥、Ⅱ型糖尿病、小兒川崎病、習慣性流產等疾病的防治均有一定效果。
然而,最令人矚目的還是阿司匹林對幾種癌癥的預防效果。早在上世紀70年代,科學家就注意到,有幾種癌癥患者的前列腺素-E2的分泌水平明顯高于正常水平。因此有人提出假說,過量分泌的前列腺素-E2正是導致腫瘤形成的原因。而阿司匹林對各種前列腺素都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可以用于前列腺素相關癌癥的控制。
實際上,已經有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可以將結腸癌與腸癌的發病率減少50%。另外,阿司匹林還能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降低胰腺癌的發病率和胃腸道腫瘤的發生率。但需要強調的是,目前醫學界尚未對阿司匹林的抗癌效果形成定論。服用阿司匹林之前一定要咨詢醫生,不能濫用,否則容易受到副作用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