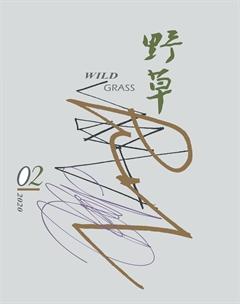冷場
羽瞳
張宇霏的瞌睡是被一陣騷動吵醒的,大巴被碎石頭顛了一下,他迷迷糊糊睜開眼睛,車窗外斜入的陽光晃得人眼冒金星,有那么兩秒鐘時間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兒。坐在旁邊的阿姨正扒著車窗伸著脖子往外看,他轉轉眼珠,車上幾乎所有男女老少都是這么個姿勢,屁股撅著,脖子伸長,扭頸向上,像魯迅筆下的看客來到了古X亭口。
耳機里正唱著《空城計》:“眾老軍因何故紛紛吶議論……”
阿姨回身拍了拍張宇霏,操著一口心急火燎的四川話:“小伙子,你看,太陽!”
張宇霏茫然,太陽有什么好看的。他再一想,噢,這兒是成都。
他垂頭睡太久,一動脖子咔咔直響,張宇霏對四川話的辨識能力要得益于他那當過兵的捧哏搭檔邢天,邢天二十歲之前在部隊水電班燒過幾年鍋爐,班長就是個川軍。邢天是臺方言機器,擅長倒口,修暖氣沒學會,四川話倒溜了個十成十。
大巴駛出成都市區一百多公里,出了隧道,陽光鏟平了四周山巒,筆直而鋒利地刺穿了車窗,洪水一般翻涌而入。乘客們已經坐回座位,在陽光里七大姑八大姨地拉家常。張宇霏重感冒,只能靠嘴喘氣兒,呼吸不暢憋得他脖子以上像灌滿了漿糊,他被耳機里的胡弦兒剌得腦子嗡嗡響,摘了耳機周圍也在嗡嗡響。
張宇霏想,我可真是吃飽了撐的。
他是來成都參加婚禮的,新郎新娘都是頭一次見。來之前他正跟邢天鬧不痛快,那天他上場演出,那家茶樓后臺“入相”的簾子底下有仨臺階,他下臺時正心慌,一不留神踩了個空,崴了腳,片刻腳脖子腫起一指多高,只能推了后兩天的演出。他和邢天搭檔不過一年,還沒有固定的穴眼,整天走穴,哪兒有空缺就去哪兒說,這家茶樓是新找的,本來談好了今晚上來說頭場,連說一禮拜的。
作藝吃飯的人,工夫就是棒子面,你上不去有的是人頂。他倆為張宇霏的腳脖子歇業了一個多星期,窩在廉租房對活,一趟默梆子對了好幾十遍,越對越覺著別別扭扭不順當,嗝。邢天一氣之下去筒子樓的公共廚房煮方便面,張宇霏他媽一個電話進來:“你老姑來信兒說大閨女結婚,電話都打家里來了,你爸腿腳不利索,路費媽給你,你去替你爸跑一趟。”
張宇霏說:“這都二十多年沒走動了,大老遠的,我干啥去啊。”
他媽苦口婆心:“噯,你這孩子不能這么說話,去年你爸腦溢血你拿不出錢,還不是你老姑給匯的錢,你說你成年的可北京天津漂著混,啥時候能把債還上?我跟你說啊,我可跟你老姑說了你在天津的文工團說相聲,有出息,你可別給我說漏嘴了。”
張宇霏最怕他媽翻舊賬,生怕他媽把他剛到北京就被騙了小十萬,沒過小半年又被騙進傳銷窩子,逃出來后流落天津的事兒倒騰出來,他掛了電話,把手機往床上一摔:“您瞧,不定哪腳高哪腳矮,一不留神就出息了。”說完沒人搭理他,才發現邢天沒在屋。
成都的天空不時泛起煙霧般的灰藍。張宇霏到成都第四天了,老姑讓半個成都都知道他是文工團的了,人民的呼聲——婚禮司儀非他莫屬。他套上了那身小一碼的禮服,繃得不敢揮手不敢跺腳不敢即興發揮,老姑也不知道從哪兒淘換來一副快板兒,讓他露兩手喜慶喜慶。張宇霏從小投藝抱四門,學齡前學快板兒,十來歲學相聲,搭伙邢天前他到處給園子打開場板兒,一段《十八愁》下來喯兒都不帶打一個。
老姑招來一干親朋四鄰八舍在下邊坐得滿滿當當,張宇霏花板兒打得正熱鬧,收場一揚大板兒,胳膊底下“刺啦”一聲開了線,鬧了個滿堂碰彩。張宇霏臉上帶笑,心里罵自己病鴨子遭狗咬,倒了八輩子血霉,回了酒店蒙頭就睡,睡到半夜嗓子發炎發起了高燒。
成都是盆地深處的平原一隅,常惹得人翹首太陽。四面環山,一年到頭濕漉漉的,水汽在頭頂凝結成厚重的云層,鍋蓋一般浮行半空,將陽光稀釋成稀薄的霧氣,軟綿綿地往毛孔里滲。張宇霏悶在房間睡了一整天,混混沌沌地做夢,他夢見他還在師父家,師父叫他數玲瓏塔,他急得滿頭大汗愣是一個字兒想不起來,快板兒也不響,師父惱了,罰他在小黑屋關禁閉。
張宇霏在傍晚時掀開蒙住臉的被子,燒退了,他出了一身的汗。窗外黃昏暗淡淋漓,骨縫里沉甸甸墜得發疼,他發了會兒呆,掏出手機搜了搜旅游攻略,給自己訂了張去桃坪羌寨的大巴車票。
大巴又開了快一個小時,到羌寨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張宇霏自己一個人下了車,站在羌寨門口,象征性地對著木欄大門上墜著鮮紅綢緞的羊頭拍了兩張照。他一天一宿只吃了半碗紅油抄手,辣得他涕淚橫流也沒吃飽,這會兒覺著耳機沒音,肚子里在唱空城計了,他在回折彎轉的寨子里迷了半個多小時的路,終于找到一家開門的民宿。
羌寨里都是石砌的碉樓,進了屋又陰又涼,門口的阿婆放下簸箕,連比劃帶說地把同一句話問了三遍,張宇霏連比劃帶猜地聽到第三遍,才明白對方問他是要住還是要吃飯。
張宇霏張牙舞爪:“吃飯,也住。”
阿婆遞上一張壓著塑料膜的菜單,一樓廳里只有兩三張圓木桌,他坐在木頭長椅上,點了份臘肉炒蒜苗,一份雞蛋湯。臘肉是阿婆自家腌曬的,切得極薄,也咸,炒得不精致,大鍋燒灶,家常味兒。張宇霏就著湯泡飯吃了滿滿一盤,暖流順著喉嚨進了胃,他吸了吸鼻子,幾天來第一次體會到用鼻腔呼吸的暢快。
阿婆手里一邊做針線,一邊瞧著他樂,張宇霏打了個噴嚏,豎著拇指:“好吃,味兒像我師父做的。”
阿婆笑得像個核桃:“啊?”
張宇霏說:“夸您呢,您做飯像我師父,我師父您知道嗎,良田千頃,不如一技在身。師父就是教我能耐的人。”
阿婆笑得像個裂開的核桃:“啊!米飯不要錢!”
張宇霏說:“您可真實在。”
張宇霏九歲成了師父的入室弟子,學快板兒書,吃師父的住師父的學師父的,師父寵他,把他當兒子待,師父起得早,他也起得早,師父練完早功要喝一壺茶,靜坐,他坐不住,趴窗臺跟魚缸里的老烏龜練對眼兒。師父端著茶碗瞧他一會兒:“來啊兒子,給爸爸唱一個。”
師父早些年去過西安,會唱陜西快書。師父在廚房顛勺,他在旁邊握著四片瓦打點兒,西紅柿炒雞蛋、韭菜炒雞蛋、蒜薹炒雞蛋,一年到頭三板斧。
張宇霏在北京賣過烤串兒,送過快遞,當過司儀,第一次開張是在人家園子門口打板兒圓粘兒,穿了身亮粉色的大褂兒還是管人家后臺借的。人家給他開了四十塊錢,晚上他揣著這筆巨款請老家來的朋友吃麻辣燙,一邊吃一邊數簽子,人家多喝一瓶啤酒,他得算計著少吃兩串兒,免得結賬時出不來門兒。
阿婆說:“小伙子還在讀書吧,自己出來玩呀?”
張宇霏豎著耳朵聽明白了,沖阿婆擺擺手:“我是說相聲的。”說完他覺著相聲倆字兒黏得太緊,人家肯定聽不懂,他把語速放慢了,拆開了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嚼碎了說:“相——聲,相聲您知道嗎?”
阿婆點點頭,又搖搖頭,張宇霏用筷子蘸著湯在桌面上寫:“相貌的相,聲音的聲,馬三立,逗你玩兒,這總知道吧!”
阿婆笑出兩顆不置可否的門牙,張宇霏自己也愣了一會兒,撓了撓鬢角咕噥一聲:“算了,日他媽的相聲。”
來成都的前一天他和邢天吵了一架,憤怒也是這樣突如其來。他倆從張宇霏下臺崴腳吵到沒錢吃飯成天吃方便面,吵到最后張宇霏指著邢天的鼻子:“甭跟我狡辯,成天你的心思都讓小粉絲拐賣了,就沒擱玩意兒上頭!”
邢天愣了一下,他倆在曲校時就認識,邢天退伍讀大專,張宇霏讀中專。認識好些年從沒紅過臉。張宇霏在上京下衛沒搭檔,不是百分百為了等他,心里也是惦記著有這么個人。邢天畢業后回了老家,在地方臺當了個小助理,今年年初張宇霏回家過年,知道他混得一般,好說歹說,把人從老家勸到了天津。
張宇霏下臺崴腳,一半兒責任也在邢天,張宇霏的女朋友剛跟他分了手,分過了照來聽他的相聲玩,散了場在后臺就把方頭大臉一臉福相的邢天給堵了。邢天樂得和人家談了三個多月,勒緊褲腰帶請女孩兒看過兩場電影,吃過一次吉野家,七夕還送了一捧香水百合。女孩兒送他禮物他想法掉個兒也要加三倍還回去,回廉租房連方便面都是賒張宇霏的。張宇霏說這么下去你倆準得黃,邢天當場就把方便面給潑了。
女朋友和邢天黃了那天,邢天演出時搞得聽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上了臺后還過一眼近一眼向臺下找人。他倆往常都是子母哏,張宇霏語速快,調門兒高,邢天比他還高,話頭攔得住,包袱翻得響。邢天反應一慢,他倆節奏就出了差錯,好幾個包袱一劃拉就過去了,掉地上沒響。偏趕上那天也是寸,觀眾不太捧場,一段《倭瓜鏢》說得太瘟,沒幾個人笑。張宇霏越說越心急,一急嘴里不利索吃了栗子,趟子活說錯了詞,幸虧他反應快,忙亮了個身手糊弄過去。觀眾聽沒聽出來他不知道,自己倒是慌慌張張出了一身透汗。
場上情緒相互傳染,他急,邢天也急,一急就走攢子跑了神兒,張宇霏說:“我騎著牛沖著賊一劍過去,斗大的腦袋在地上滴溜溜亂滾。”邢天本該說:“你把賊殺了?”卻錯接成了張宇霏的詞:“你(我)把牛宰了?”一句話把“底”給刨了。
張宇霏一聽,心涼了大半截,他腦袋發懵,攥著掌心的冷汗扭頭就往后臺走,邢天喊:“你干嘛去?”他強壓著慌亂回了句:“我拿牛肉入伙去!”
補救算是補救回來了,張宇霏一顆心七上八下的,沒到后臺就崴了腳。他倆把這事兒憋著不說,其實心里都系了個疙瘩不大痛快。上不了臺沒飯吃,邢天白天去街上發傳單,張宇霏單腿兒蹦了兩天總算能下地走路,他倆憋在出租屋一星期,憋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看到張宇霏的成都長途客運票,邢天半晌沒說話,翻出旅行包給張宇霏收拾行李,張宇霏坐在床上瞪他,邢天把一條牛仔褲疊了八遍:“正好,你去吧,咱倆都冷靜冷靜。”
阿婆的民宿只有張宇霏這一個吃開口飯的住戶,木頭樓梯咯吱咯吱地響,房門上掛把一撬就開的小鎖頭。張宇霏鎖上門,兜兒里揣著手機和身份證下了樓,阿婆還在做針線,沖他招招手,指指外頭笑著說了句什么,他實在沒心思聽懂。
羌寨曲徑羊腸,高聳碉樓外側的云母石經過千百年日曬風塵,刮在掌心有種肅穆的溫熱。張宇霏七拐八拐,從這家穹頂到那家后院兒,終于在太陽落山前找到了旅游攻略里的瞭望臺。他遠遠看見臺階底下坐著個穿著羌族服裝的老太太,看上去比民宿的阿婆歲數還大,一張臉在肆虐的太陽底下曬成脆黃的古書,又被風煙揉皺成一團,泛起羌寨隨處可見的土黃色。
他突然醒悟出門前阿婆的表情和對他說的那句話,阿婆的眼睛瞇成一條縫,指了指西邊天際沉沉欲墜的紅輪,干癟的嘴唇展開一個飽滿的笑容,每一個字音都透著比陽光還要刺眼的驕傲:“曬曬太陽,成都沒有這么好的太陽。”
張宇霏覺得有人在自己頭頂撞了聲鐘,震得他渾身發麻,他張了張嘴,聽見山風彎折過崔嵬峰巒,岷江蜿蜒,穿過碉樓下阡陌水網,在甬道深處撕裂開一道口子,如同小時候用放大鏡點燃的那張白紙。
他原以為全天下的太陽都是一樣的。
瞭望臺在整個羌寨最高處,越往上走風越急,他順著臺階往云巔走,到了最后,幾陣風吹得他邁不開腿,臺上紅綢烈烈,臺下山坡一道明顯的分界線將羌寨分成新舊兩部分。
張宇霏掏出手機:“喂?”
邢天在那頭扯著嗓子:“你后天能不能回來啊?老徐找咱倆晚上租界茶館挎刀,你去不去?”
“去啊,咋可能不去,”張宇霏一張嘴灌了一肚子風,“后天早上我就到家,給我留門。”
“行,我知道了,”邢天稀里呼嚕吃方便面,“你可哪兒呢?風挺大啊。”
“古戰場。眼前萬丈懸崖,我坐了半天了。”張宇霏說,他望著腳下的羌寨,古道將老城分割成凌亂的碎塊,如同摔碎后黏連成片的陶罐,瓦礫殘垣堆砌出令人驚嘆的、古樸蒼茫的美感。他又說:“現在我覺著自個兒就是諸葛孔明啊。”
邢天沉默了一會兒:“祖宗,啥時跳啊?你要是想不開,我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沒了娘了。”
張宇霏嗆了一口風,咳得眼淚都出來了:“滾你媽的蛋。”
邢天嘴里嚼著東西:“你可別跟我提諸葛孔明,您那前女友說,當初她瞧上我就因為我在臺上來了段空城計,她聽著特像她姥爺。”
張宇霏說:“你就招蜂引蝶吧,還當上姥爺了,我當初就告訴過你吃開口飯的人只要自認自己是姥爺就離當耷拉孫兒差不遠了,你還不信吧?”
邢天樂得像二百只鴿子出籠,捧哏踩逗哏貓尾巴比從自己兜兒里摸煙還容易,他吸溜著方便面喝了口湯,含含混混地哼:“……諸葛亮在敵樓把駕等,等候你到此談哪,談,談談心。”
他尾音散在風里,從遠處來,過近處,又向遠處去。邢天生了一副祖師爺賞飯的好嗓子,柳活使得好,不爭不搶,捧得瓷實,張宇霏一直覺著自己占著塊寶,耽誤了人家。他抹了一把被風吹得生疼的眼睛:“行,等后個兒我到家,咱哥倆兒方便面就燕京,小肚子上弦,彈彈(談談)心,好好兒整兩瓶兒。等以后磨合好了,有穴眼了,進文工團了,出名兒了,掙錢了,我給你買豬頭肉,買好酒,買好茶葉,買好煙。”
“停停停,快把你那二兩貓尿憋回去,別啰啰嗦嗦麻應人,”邢天直唆牙花子,“我先把話說頭里,我來天津漂著是我自己樂意,你別有啥負擔。”
“美得你,”張宇霏的鼻子又堵住了,悶聲悶氣地,“我之前沒找搭檔也不是全沖著等你。”
邢天哈哈一笑:“得了,不廢話了,快回來吧,老徐說他想自己開個園子,這回說好了就考慮簽咱倆,你可別掉鏈子。”
張宇霏下了瞭望臺,老阿婆還坐在臺階上仰著頭,天色漸漸收斂起昏沉迷蒙的光,有種剛剛開天辟地時的混沌荒蕪,大地與天空之間撕裂開一道巨大的縫隙,夕陽西沉,半壁天空熊熊燃燒,如同瞭望臺上紅綢漫天。
張宇霏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天剛蒙蒙亮。他在羌寨門口等到了去理縣的大巴車,大巴開了一夜,混雜著編織袋和二手煙的怪味兒。張宇霏戴著耳機,昏昏沉沉做了個夢,他在師父家樓下那棵柿子樹底下數玲瓏塔,背得口干舌燥愣是數不完,他急得要哭,師父端著茶杯沖他招手:“別急,先過來,陪師父曬曬太陽。”
張宇霏張開眼,一縷晨曦穿過山巒疊嶂,漫過青山遠黛,正巧落在他半邊臉上。
【責任編輯 朱 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