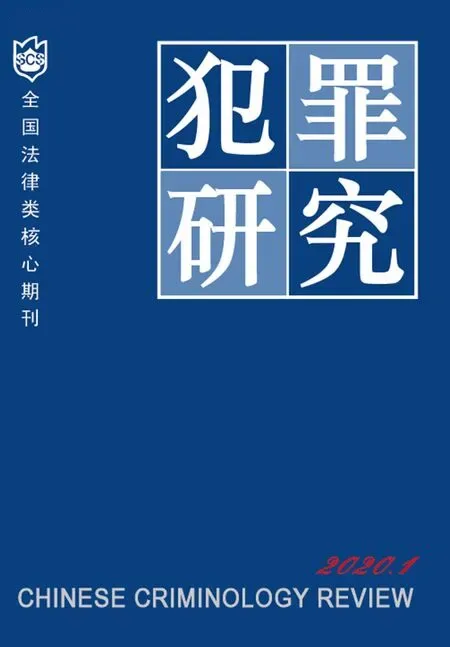我國貪污賄賂犯罪主體特征的“大數據畫像”研究
——基于8133份公開起訴書的大數據分析
金鴻浩 李 凌 劉思敏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腐敗現象也大幅增加。鄧小平曾在《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一文中指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頁。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感嘆,“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2]習近平:《緊密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載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頁。
貪污賄賂犯罪現狀的評估測量是廉政學研究、監察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近年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加大了案件文書公開力度,紀檢監察機關加大了審查調查網上通報力度,基于公開文書的職務犯罪大數據統計分析成為可能。樂云、張兵等分析了2009年至2011年工程建設領域專項治理中的145例貪污賄賂犯罪,發現工程腐敗近80%涉及黨政機關和部門主要領導,近 40%工程腐敗案件為窩案、串案,犯罪嫌疑人平均年齡52.10歲,犯罪潛伏期7.98年,案均金額681萬元。[1]樂云、張兵、李永奎、單明:《基于主體特征的工程腐敗規律實證分析》,載《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年第18期。朱艷菊、宋濤分析了2010年至2014年洛陽市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類犯罪的992名犯罪嫌疑人,發現農村基層組織人員達到324人(占比32.7%),而在已判決案件中,擔任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的又占到基層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犯罪的38.4% ,其中農村土地征用領域犯罪多發、高發。[2]朱艷菊、宋濤:《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實證研究——以洛陽市檢察機關近5年查辦的案件為例》,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王志遠、鄒玉祥分析了2013年至2015年吉林省482份公開的貪污賄賂案件判決書,發現近80%案件發生在基層,賄賂案件中61.90%涉及典型的商業賄賂犯罪,貪污案件中84.19%采取“騙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3]王志遠、鄒玉祥:《吉林省貪污賄賂犯罪實證考察與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載《凈月學刊》2016年第4期。梅錦、徐玉生分析了沈陽、廣州等6個副省級城市2013年至2016年公開的745 份貪污賄賂罪判決書,分析發現6地受賄犯罪的平均犯罪潛伏期在3.6年至6.1年之間,平均作案次數在6.5次至15次之間,平均受賄金額在29.1萬至87.8萬之間,各地職務犯罪特征差異較大。[4]梅錦、徐玉生:《中國腐敗犯罪狀況的實證研究——以新型客觀測量模式的引入為研究視角》,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褚紅麗、孫圣民等分析了2014年3065份公開的受賄罪裁判文書,犯罪嫌疑人中科員級占40.72%,副科級占27.16%,正科級占23.49%,副處級占4.02%,正處級占3.41%,副廳級占0.83%,正廳級占0.25%,副部級占0.11%,平均受賄金額為40萬元,副廳級及以上貪官的平均受賄金額為875萬元。[5]褚紅麗、孫圣民、魏建:《職務級別、法律制度設計與腐敗懲罰扭曲》,載《經濟學(季刊)》2018年第3期。李輝和楊肖光分析了 2015年至 2017年公開的貪污賄賂罪案件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案件共計27691份起訴書,發現2015年受賄罪略多于貪污罪,但2016年貪污罪略多于受賄罪,犯罪嫌疑人的平均年齡為49.89歲,女性嫌疑人只占到10.43%。[6]李輝、楊肖光:《市場化與腐敗類型的地區差異——基于職務犯罪起訴書數據的多層分析》,載《公共行政評論》2019年第3期。此外,劉啟君、崔晶晶和鄧曉梅、王剛、王劍波、王林林、申純和胡桑、文宏和杜菲菲等采用裁判文書數據對人事領域、工程領域、科研領域、涉農領域等腐敗現象也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7]參見劉啟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腐敗狀況實證分析》,載《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6期;崔晶晶、鄧曉梅:《工程項目腐敗交易階段模型的建立與量測》,載《工程管理學報》2014年第1期;王剛:《我國貪污受賄罪量刑存在的問題和完善建議——以200份貪污受賄案件判決書的實證分析為基礎》,載《湖北社會科學》2016年第11期;王劍波:《我國受賄罪量刑地區差異問題實證研究》,載《中國法學》2016年第4期;王林林:《貪污、受賄犯罪后情節適用的規范化研究——基于200例貪污、受賄判決文本的實證分析》,載《法律適用》2016年第9期;申純、胡桑:《科研腐敗成因分析及防治對策研究——基于20個案例的統計分析》,載《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文宏、杜菲菲:《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的演化機理與治理對策——基于2009—2017年鎮街腐敗案例的內容分析》,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十九大以來,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反腐敗進入“深水區”“疲勞期”“膠著期”,系統梳理上一階段的反腐成就,特別是研究腐敗犯罪主體中的規律性特征,對于提升反腐敗斗爭的現代化、科學化、精細化水平,通過從嚴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和民心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在刑法學的傳統犯罪構成理論模式“四要件說”中,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是犯罪的四個基本要素,犯罪主體特指“說明犯罪是由什么樣的人所實施的要件”。在三階層理論中,犯罪構成的該當性也包含了行為主體要素。在貪污賄賂犯罪中,犯罪主體的研究更為必要。貪污賄賂罪屬于職務犯罪,因此往往以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為前提,在司法實踐中,涉案當事人的身份問題更是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1]張春燕、王凱:《受賄案件犯罪主體及涉案金額認定——以孫某某受賄抗訴案為例》,載《中國檢察官》2014年第22期。[2]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某市五年來審結的檢察機關指控農村基層組織干部貪污的110件案件中,辯護人、被告人辯稱是職務侵占的87件,占檢察機關指控貪污案件的79.1%。參見查國防:《貪污抑或職務侵占:農村干部騙取、套取、侵占涉農款項犯罪實證分析》,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年第2期。在政治學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的是哪些人是腐敗犯罪的高發群體,即對腐敗犯罪主體進行“數據畫像”。這是廉政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前者可以就腐敗主體特征與其他因素進行相關分析、回歸分析以探究腐敗成因;后者有助于紀檢監察機關針對性地懲治和預防腐敗,全面提升腐敗治理效果。[3]王希鵬:《廉政學的學科定位與理論體系——兼論紀檢監察學科建設何以可能》,載《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二、研究設計和數據來源
2014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啟動案件信息公開系統開發工作,2014年6月審議通過《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工作規定(試行)》,其中第18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所作判決、裁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起訴書、抗訴書……應當在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系統上發布”,同年10月1日案件信息公開系統(www.ajxxgk.jcy.cn)在全國正式上線運行。
筆者對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通過案件信息公開系統公開的貪污賄賂罪(主要針對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起訴書進行實證分析。主要基于Python程序配置網絡爬蟲軟件,對“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的“法律文書公開”欄目中“起訴書”板塊(http://www.ajxxgk.jcy.cn/html/zjxflws/)同時滿足下述3個條件的文書進行獲取:①文件類別為公開文書中的起訴書;②起訴罪名為《刑法》規定的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介紹賄賂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③公開時間為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通過上述方式共搜集到2016年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公開的貪污賄賂罪起訴書9588件,剔除無關文書后,共篩查出文書8133件10711人。根據《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2016年我國人民檢察院決定起訴的貪污賄賂案件為22202件29640人。本研究采納的公開起訴書為8133件10711人,占到當年貪污賄賂犯罪全部起訴案件數的36.63%、起訴人數的36.14%。
研究樣本數據保存在8133個TXT文本中,總計1283.34萬字。傳統的人力無法完成編碼過程,筆者首先通過計算機,對文本要素的特點字段進行信息抽取。在技術原理上,主要綜合文本檢索、正則表達式匹配、樸素貝葉斯算法等方法,由計算機對文書中所包含的特定字段信息進行抽取,同時通過命名實體識別和實體關系抽取等技術,完成了對所有案例信息點的抽取。例如,提取移送審查起訴時間的正則表達式為:pattern1 = r"d+年d*月d*日w*((移送|進入)審查|告知)",pattern2 = r"同年d*月d*日w*(移送|進入|審查|告知)"。機器篩查的初次結果并不理想,準確率在50%-70%左右。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和編程團隊采取了機器學習的方式,先對1200余份起訴書進行深度學習,使機器篩查準確率逐步提升。先后由編程團隊負責對上述起訴書進行了7次篩查,經人工抽驗,準確率逐步提升,最終準確率在 85%左右,此時進一步通過機器學習提升準確率的邊際成本較高,有一些問題機器很難準確識別。筆者又組建了人工復核小組,對照文書爬取的文本和機器篩選的CSV文件(后轉化為EXCEL表格)進行復核。在明確編碼過程與標準后,筆者根據人工校驗的數據,錄入Stata軟件完成統計工作,并借助大數據可視化工具從多維度展現和分析數據。重點對不同年齡、不同學歷、不同職業的腐敗犯罪主體進行比較分析,增強對腐敗現象的規律性認識。
三、貪污賄賂犯罪主體年齡特征及規律
既往受限于大規模的腐敗樣本數據難以獲得,腐敗主體的年齡研究相對較少。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點是“腐敗主體年齡的兩極化”趨勢。[1]沈遠新:《腐敗主體年齡兩極化的社會心理分析》,載《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持該論點的研究者認為:一方面,腐敗高齡化問題較為突出,“59現象”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一度是媒體、學界的熱詞之一。主要描述了個別領導干部在即將退休之際,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退休之后“高枕無憂”“軟著陸”等心理作用影響,在退休前貪污腐化的現象。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有很多,例如某科研機構基于部分公布的案件數據研究發現,2013年被查處公職人員年齡最大的 64歲,最小的39歲;其中,51-60歲年齡段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53.7%。[2]田禾、呂艷濱、姚東:《2013年中國反腐敗路徑及2014年形勢預測》,載李林、田禾主編:《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2-70頁。另一方面,腐敗低齡化問題也逐步凸顯,有的稱為“39現象”“35現象”“26現象”,版本繁多。上述研究多以媒體報道的個案為依據。也有部分統計數據,例如有部分論著引用200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數據,當年立案的不滿35歲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貪污賄賂案件共7331人,占19.28%。[3]陳聯俊:《論干部腐敗年輕化的成因及其治理》,載《理論月刊》2004年第11期。浙江省2013年查處35歲以下青年干部共454人,占當年立案數的25.8%。[4]胡洪彬:《青年干部“35歲貪腐現象”:特征、成因及其治理》,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還有一類代表性觀點認為,“腐敗與年齡無關”,“年齡只是噱頭”,持此論點的多為實務部門和媒體記者,學術性文獻較少。[5]參見趙晨光:《腐敗與年齡無關》,載《人民檢察》2002年第6期;李克杰:《“80后”腐敗,年齡只是個噱頭》,載《法制日報》2012年3月21日,第7版。
誠然,許多文章中將腐敗犯罪與年齡進行關聯,確有吸引眼球之意。但在筆者看來,腐敗犯罪是否與年齡相關,腐敗犯罪主體的年齡分布是否符合“兩極化”特征,都不是可只依靠研究者的主觀感覺或者部分個案或典型案例可以推測得出的。筆者基于大數據統計得出的結論與上述兩種觀點恰恰相反。
(一)起訴時年齡
2016年公開起訴書的貪污賄賂罪被告人中,已知出生年的9427人,占公開起訴書10711人的88.01%。按照“起訴時年齡=起訴年-出生年”計算,起訴時被告人年齡的平均值為48.46歲,眾數為53歲,最大值為81歲,最小值為20歲。
按照年齡段劃分,起訴時年齡19歲以下無;20-29歲169人,占有效樣本的1.8%;30-39歲1228人,占有效樣本的13.0%;40-49歲3506人,占有效樣本的37.2%;50-59歲3618人,占有效樣本的38.5%;60-69歲846人,占有效樣本的9%;70-79歲50人,占有效樣本的0.5%;80歲以上1人。其中,41-56歲年齡段占總樣本的64.0%,接近2/3。

圖1 2016年公開起訴書中腐敗犯罪被告人起訴時年齡分布直方圖
從圖1可以清晰看出,被告人被提起公訴時年齡符合正態分布,兩頭低,中間高,因此“腐敗主體年齡的兩極化”趨勢不完全正確。至少在2016年,“26現象”“35現象”“59現象”對應的提起公訴人數,均低于每個年齡段起訴人數的平均值。
(二)初次犯罪時年齡
初次犯罪年齡是另一個十分具有研究價值的指標,特別是對于腐敗犯罪預防研究和實務工作而言,有助于結合發展心理學,對干部成長過程進行心理輔導、思想教育,“把好第一道關”,從而有效降低青年、中青年、中年等不同年齡干部的腐敗風險。某種意義上,初次犯罪年齡比起訴時年齡更有研究價值。

圖2 2016年公開起訴書中腐敗犯罪被告人初次犯罪時年齡分布直方圖
2016年公開起訴書的貪污賄賂罪被告人中,已知出生年的9400人,占公開起訴書10711人的87.76%。其中平均值為42.78歲,眾數和中位數均為43歲,最大值為79歲,最小值為16歲。
按照年齡段劃分,如圖2所示,初次腐敗犯罪時年齡19歲以下5人,占有效百分比0.1%;20-29歲560人,占5.9%;30-39歲2613人,占27.8%;40-49歲4362人,占46.4%;50-59歲1671人,占17.8%;60-69歲181人,占1.9%;70-79歲7人,占0.1%;80歲以上無。其中40-49歲人數最多,其次是30-39歲。
30-49歲成為74.2%領導干部初次涉及腐敗的年齡段,這點再次證明了“腐敗主體年齡的兩極化”觀念不完全正確。腐敗的“中青年危機”現象更需要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30-49歲是領導干部工作的“黃金年齡”,筆者推測,實際上也是因為在這一年齡段公共權力、腐敗機會與腐敗動機達到一個平衡點。
一方面,相比30歲以下干部,30-49歲干部大多已經走向了初級、中級領導崗位,執掌一定的公共權力,具備更多的腐敗機會;另一方面,相比50歲以上干部,30-49歲干部面臨著娶妻生子、贍養老人、購房置業、子女教育、個人晉升等更多剛性需求與發展性需求,同時中青年階段也比中老年階段具有更強的進取心,因而腐敗動機更大。如果套用經濟學需求供給模型,筆者的假設是20-30歲干部腐敗需求(腐敗動機)>供給(掌握的公共權力和腐敗機會),30-50歲干部腐敗需求≈供給,50-60歲干部腐敗需求<供給,60歲以上干部腐敗需求和供給均大幅下降,因此在30-50歲年齡段達到腐敗需求和腐敗供給的一個大致平衡點。研究發現,初次腐敗犯罪年齡與犯罪金額密切相關。具體而言:

圖3 貪污犯罪初犯年齡與犯罪金額關系
1.初犯年齡與貪污罪金額存在相關關系。初犯年齡與貪污犯罪金額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100(顯著性P<0.01)。貪污罪的平均初犯年齡為43.56歲。按照年齡段劃分,如圖3所示,20-29歲年齡段初次腐敗犯罪的平均累計貪污金額最高,為70.3824萬元;此后犯罪數額隨著年齡段增長,平均貪污犯罪金額逐步下降,到70歲以上時達到最低值,平均貪污金額為2.164萬元。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年齡分段,45歲作為一個分水嶺,18周歲至44歲為青年人,45歲至59歲為中年人進行分析。分析得出,45歲及以上(中年人)初次犯貪污罪的犯罪金額平均為16.027萬元,是45歲以下(青年人)犯罪平均金額(40.3376萬元)的39.73%。即年輕干部的貪污犯罪金額更大,與王一江等人“35歲以下年輕官員貪污金額明顯較高”研究結論相近。[1]王一江、遲巍、孫文凱:《影響腐敗程度的權力和個人因素》,載《經濟科學》2008年第2期。
2.初犯年齡與受賄金額存在相關關系。初犯年齡與受賄金額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036(顯著性P<0.05),受賄罪的平均初犯年齡為42.26歲。按照年齡段劃分,如圖4所示,40-49歲年齡段平均初次犯罪的受賄金額最高,為86.6863萬元,達到峰值;40余歲之前隨著年齡段增長,平均受賄犯罪金額逐步上升;40余歲之后,隨著年齡段下降,平均受賄犯罪金額逐步下降。與貪污相反,45歲及以上(中年人)初次犯受賄罪的受賄金額平均為85.8606萬元,是45歲以下(青年人)犯罪平均金額(68.1496萬元)的1.259倍。

圖4 受賄犯罪初犯年齡與犯罪金額關系
3.初犯年齡與挪用公款罪金額不存在相關關系。初犯年齡與挪用公款犯罪金額沒有統計學上的相關關系。其中,挪用公款罪的平均初犯年齡為41.57歲。按照年齡段劃分,50-59歲年齡段初次犯罪的平均挪用公款金額最高,為289.9405萬元,達到峰值。45歲及以上(中年人)初次犯罪的挪用公款金額平均為209.6304萬元,是45歲以下(青年人)犯罪平均金額(220.4817萬元)的95.08%,兩者比較接近。
四、貪污賄賂犯罪主體學歷特征及規律
之前已有部分文獻對犯罪主體的教育因素(主要是學歷指標)和腐敗關系進行研究,但是研究結論差異較大。有的學者認為高等教育可以有效減少腐敗金額;有的學者則認為學歷越高,腐敗金額越高;還有的學者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2]參見鄧崧、李目文:《中國省部級官員腐敗問題研究——以2009—2015年50個案件為例》,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周國林:《試論上市公司董事會特征與經營者腐敗》,載《南方金融》2006年第7期。
在2016年公開起訴書的貪污賄賂罪被告人中,已知教育程度的有10653人,占公開起訴書10711人的99.5%。其中受到過高等教育的占有效樣本的61.5%(博士研究生學歷12人、碩士研究生411人、大學學歷3088人、大專學歷3020人),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占38.5%(高中學歷2462人,初中及以下學歷的1660人)。
(一)學歷與犯罪類型關系
1.學歷與犯罪罪名關系。被告人學歷與犯罪罪名顯著相關。在受賄罪中,受到過高等教育的被告人占有效樣本的 86.9%;在挪用公款罪中,受到過高等教育的被告人占有效樣本的64.9%;在貪污罪中,受到過高等教育的被告人占有效樣本的41.7%;大學學歷的被告人最多,占 48.5%。從上述數據不難發現,受到過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學歷)的被告人更偏好受賄方式,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被告人更偏好貪污方式。
2.學歷與犯罪次數關系。被告人學歷與犯罪次數相關,相關系數為 0.234(顯著性P<0.01)。按照作案次數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被告人的作案次數中位數為8次,大學學歷為5次,大專學歷為3次,高中學歷和初中及以下學歷作案次數的中位數均為2次,學歷越高,犯罪次數也往往越頻繁。

圖5 腐敗犯罪被告人學歷與貪污金額(中位數)關系圖
3.學歷與犯罪人數情況。被告人學歷與犯罪人數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319(顯著性P<0.01),受過高等教育的共同犯罪人數(平均1.53人)顯著低于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平均2.55人)。學歷越高越傾向于獨自犯罪,而學歷越低越傾向于共同犯罪。
4.學歷與犯罪金額關系。研究發現,貪污賄賂罪的被告人學歷和犯罪金額存在顯著相關。具體而言:①被告人學歷與貪污金額顯著相關,相關系數為0.276(顯著性P<0.01),如圖5所示,按照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被告人貪污金額中位數為32.545萬元,大學學歷為13.23萬元,大專學歷為7.655萬元,高中學歷為4.445萬元,初中及以下學歷3.31萬元。②被告人學歷與受賄金額顯著相關,相關系數為 0.243(顯著性 P<0.01),如圖 6所示,按照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被告人受賄金額中位數為63萬元,大學學歷為21.025萬元,大專學歷為13萬元,高中學歷為9.16萬元,初中及以下學歷為7.975萬元。但是被告人學歷與挪用公款金額沒有統計學上的相關關系,相關系數-0.030(顯著性P=0.13)。

圖6 腐敗犯罪被告人學歷與受賄金額(中位數)關系圖
這在一定程度說明貪污罪、受賄罪屬于高智商犯罪。當高學歷領導干部走向犯罪道路時,其知識越多、能力越大,犯罪次數、金額也就越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越大,對法益的侵害更加緊迫,需要引起實務部門高度重視。[1]金鴻浩:《高學歷領導干部腐敗的十大特征與廉潔教育建議》,載《領導科學》2019年第19期。
(二)學歷與犯罪時間關系
被告人學歷與犯罪潛伏期顯著相關,相關系數為0.088(顯著性P<0.01)。按照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的被告人犯罪潛伏期的中位數為7年,大學、大專、高中學歷的被告人犯罪潛伏期的中位數均為5年,初中及以下學歷犯罪潛伏期的中位數為4年。被告人學歷也與犯罪持續時間顯著相關,相關系數為0.159(顯著性P<0.01)。按照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的被告人犯罪持續時間的中位數為5年,大學學歷為3年,大專學歷、高中學歷、初中及以下學歷均為2年。
(三)學歷與審查起訴時間關系
被告人學歷也與審查起訴時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11(顯著性P<0.01)。按照中位數統計,研究生學歷被告人的案件審查起訴時間中位數為85天,初中及以下學歷的中位數為40天,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但是,在加入犯罪金額、犯罪類型兩個控制變量后,犯罪主體學歷與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間將不再具有統計學上的相關性。
五、貪污賄賂犯罪主體職業特征及規律
腐敗犯罪主體的職務和職業類型差異,與腐敗犯罪類型、犯罪人數、犯罪次數、犯罪時間、犯罪金額等因素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一)職務因素
2016年檢察機關公開的貪污賄賂罪起訴書中,4932人是普通工作人員(占46%),5779人是領導干部(占54%)。但是由于公開文書的信息屏蔽,導致判斷被告人是否是領導干部的精準度相對較低,被告人職務級別也無法從文書中獲得,這是本研究最重大的一個遺憾。
研究發現,不同職務的犯罪類型具有顯著差異。領導干部貪污賄賂犯罪中涉嫌受賄罪的比例為48.40%,涉嫌貪污罪的比例為45.46%,涉嫌挪用公款罪比例為11.13%(存在一人犯多罪的情況,下同)。而普通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犯罪中涉嫌貪污罪的比例為 53.00%,涉嫌受賄罪的比例為32.81%,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比例為17.36%。就犯罪類型而言,領導干部更偏向于受賄行為,普通工作人員更偏向于貪污行為。

圖7 不同職務的受賄罪被告人犯罪次數、受賄金額散點圖
不同職務的犯罪次數、共同犯罪人數具有顯著差異。具體而言,領導干部的犯罪次數平均為9.34次,比普通干部(平均6.74次)高38.58%;領導干部共同犯罪人數平均為1.68人,比普通干部(平均2.21人)低23.98%。分析得出,領導干部更偏向獨自腐敗以減少犯罪暴露風險,犯罪次數較多;普通干部更偏向合作腐敗以增加犯罪機會。
職務因素與受賄犯罪金額顯著相關,相關系數為0.079(P<0.01),樣本中領導干部受賄金額中位數為20萬元,比普通干部(15萬元)多33.33%。但是,職務因素與貪污犯罪金額、挪用公款犯罪金額沒有統計學上的相關關系。按照中位數統計,領導干部貪污金額中位數為5.49萬元,普通干部為5.5萬元;領導干部挪用公款金額中位數為50萬元,普通干部為45.26萬元,兩者比較接近。

圖8 腐敗犯罪被告人職務與犯罪金額(平均數)關系圖
(二)職業因素
目前,對于貪污賄賂犯罪主體職業因素的研究文獻較少。鄭海、李國華采取隨機抽樣方法對2014-2015年300例貪污和受賄案裁判文書進行分析,發現涉及行政機關的案例數占48.33%,其中62.76%受賄;涉及國有企業的案例數占33.67%,其中59.41%受賄;涉及事業單位案例數占11%,其中69.70%貪污;涉及司法機關的案例數占3%,其中88.89%受賄,研究結論是行政機關、國有企業掌握大量政治、經濟資源,容易成為職務犯罪的侵害對象,但該研究并沒有關注到日益增加的基層自治組織腐敗問題。[1]鄭海、李國華:《貪污犯罪與受賄犯罪的犯罪學特征——基于300例案件的實證考察》,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2016年公開的貪污賄賂罪起訴書中,已知被告人職業的有8806人,占公開起訴書10711人的 80.2%。其中,職業是國家機關(含黨委機關、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政協機關、司法機關)的2977人,占有效樣本的33.8%;事業單位的1856人,占有效樣本的21.1%;國有企業的1446人,占有效樣本的16.4%;基層自治組織的2527人,占有效樣本的28.7%。大致上,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基層自治組織貪污賄賂案件人數各占1/3。
1.職業因素與犯罪類型關系。不同職業的犯罪類型具有顯著差異。具體而言,黨政機關貪污賄賂犯罪被告人中 71.75%涉嫌受賄、25.33%涉嫌貪污、9.98%涉嫌挪用公款(存在一人犯數罪情況,下同);事業單位腐敗犯罪被告人中46.50%涉嫌受賄、32.92%涉嫌貪污、27.26%涉嫌挪用公款;國有企業腐敗犯罪被告人中 59.06%涉嫌受賄、35.34%涉嫌貪污、11.27%涉嫌挪用公款;基層自治組織腐敗犯罪被告人中84.97%涉嫌貪污、9.70%涉嫌受賄、8.82%涉嫌挪用公款(基層自治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犯罪中,多是在以受政府委托身份幫助發放各類補貼等中產生的)。如圖9所示,可以發現,黨政機關的犯罪類型結構與基層自治組織正好相反,前者以受賄為主,后者以貪污為主,事業單位三類犯罪比例接近。

圖9 不同單位被告人涉嫌罪名分布圖
2.職業因素與犯罪金額關系。不同職業的貪污金額具有顯著差異。具體而言,如圖10所示,按照中位數統計,貪污金額中位數最高的是國有企業10.79萬元,大于黨政機關的10.3萬元,事業單位的8萬元,最小值是基層自治組織的3.67萬元。受賄金額最高的也是國有企業23.96萬元,其次是黨政機關20萬元,再次是事業單位14.5萬元和基層自治組織5.4萬元。但挪用公款金額最高的是基層自治組織的57.39萬元,其次是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均為50萬元,最后是黨政機關42.25萬元。分析發現,國有企業的貪污罪、受賄罪犯罪金額的中位數均高于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對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應該引起重視。基層自治組織挪用公款的中位數高于其他單位,一定程度與對基層自治組織的監管漏洞有關,審計署等部門對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都會定期進行財務審計,也建議加強對基層自治組織的審計或委托第三方審計。

圖10 不同單位的被告人貪污(左)、受賄(右)金額中位數條形圖
3.職業因素與犯罪時間關系。不同職業的初犯年齡具有顯著差異。具體而言:按照中位數計算,基層自治組織被告人的初次犯罪年齡為46歲,其次是黨政機關被告人43歲,再次是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被告人42歲。職業與犯罪持續時間和犯罪潛伏期也顯著相關,兩者數值排序均為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基層自治組織。具體而言,如圖11所示,黨政機關被告人的犯罪持續時間平均為4.07年,國有企業被告人平均為3.51年,事業單位被告人平均為3.43年,基層自治組織被告人平均為2.91年。黨政機關被告人的犯罪潛伏期平均為6.20年,國有企業被告人平均為5.87年,事業單位被告人平均為5.59年,基層自治組織被告人平均為5.41年。一定程度說明國家機關干部因為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資源,腐敗隱蔽性更強,犯罪持續時間更長。

圖11 不同單位的被告人的平均犯罪持續時間和犯罪潛伏期
六、啟示
腐敗現象是人類社會的“頑疾”,“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腐敗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多策并舉、協同推進。2005年,黨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將其作為“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對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并先后于2005年、2008年、2013年發布三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當前,對于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等實務部門和犯罪學者、廉政學者等研究人員而言,系統總結和分析十八大以來貪污賄賂犯罪的新特點、新形勢、新規律,有利于進一步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在新的起點,研究貪污賄賂“數據畫像”因而具有更加重要的政治價值、法律價值、社會價值和時代意義。
其一,貪污賄賂犯罪的“大數據畫像”分析,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新時代腐敗懲治的精準化。犯罪現狀的測量評估和研判,是“寬嚴相濟”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執行政策訂立的犯罪學基礎,[1]馬克昌:《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定位》,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4期。也是明確監察調查、刑事偵查的重點領域和優先方向的事實依據。在信息時代,對貪污賄賂犯罪已辦結案件的大樣本、甚至全樣本分析,可以輔助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集中到腐敗的多發高發領域,防止腐敗犯罪的蔓延和擴散。例如,2016年公開的貪污賄賂罪起訴書中,基層自治組織的被告人就有2527人,占有效樣本的28.7%;在挪用公款犯罪中,基層自治組織被告人犯罪金額的平均數和中位數均高于來自其他行業的工作人員;尤其要高度關注的是,樣本中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社區居委會人員54.3%的受賄行為、52.5%的挪用公款行為、44%的貪污行為發生在“十八大”之后,屬于“增量”犯罪,啟示反腐敗專職部門應將腐敗懲治重心向基層傾斜,重點打擊“群眾身邊的腐敗”;在刑事政策方面,可以探索將侵吞拆遷款等行為,通過司法解釋等方式作為貪污犯罪的量刑加重情節,有效體現刑事司法政策對基層職務犯罪新趨勢的及時反應。再如,樣本中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71.75%涉嫌受賄,犯罪持續時間平均為4.07年,犯罪潛伏期平均為6.20年,啟示在針對黨政機關犯罪嫌疑人的監察調查和刑事偵查過程中,特別是對實踐中對抗組織調查、有較強反偵查能力的嫌疑人,辦案人員可以重點同步搜集嫌疑人過去6至7年內受賄犯罪的線索,作為案件調查(偵查)的“突破口”。
其二,貪污賄賂犯罪的“大數據畫像”分析,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新時代預防腐敗的科學性。預防犯罪是治理犯罪的根本途徑,正如孫思邈《千金方》中所說,“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犯罪預防作為“隔斷或者削弱犯罪及其原因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行為體系”,[2]康樹華主編:《犯罪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91頁。可以有效在事前控制、減少、抑制犯罪的發生。在廉政警示教育中,既要圍繞“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做好觀念傳播層面、心理傳播層面、政策傳播層面的腐敗預防宣傳;[3]高紅玲、金鴻浩:《科學防腐的宣傳引導:策略與方法》,載《中國記者》2017年第4期。更要參照“大數據畫像”,提升腐敗預防宣傳的針對性。例如,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公職人員進行差異化的針對性警示宣傳,具體而言:針對20-30歲年輕群體,可以在職前教育和入職培訓中加強廉潔教育,強調慎始慎初,樣本中起訴時被告人年齡小于或等于30歲的,其貪污賄賂犯罪金額中位數為14.85萬元,要引導青年干部通過案例認識到犯罪后果,僅為了多獲得一至兩年的工資收入就可能斷送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大好前途,從而“知敬畏,明得失”。針對30-50歲中青年群體,一方面要堅持“嚴管就是厚愛”,靈活運用“四種形態”,早發現、早提醒、早預防;另一方面要加強腐敗的違法性、成癮性、危害性教育,最大程度降低僥幸心理,對擬提拔人選全面落實“凡提四必”要求,防止“帶病提拔”。[1]中組部2016年修訂印發了《黨委(黨組)討論決定干部任免事項守則》,要求黨委(黨組)討論決定前,對擬提拔或進一步使用人選的干部檔案必審、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必核、紀檢監察機關意見必聽、線索具體的信訪舉報必查。針對50歲以上中年群體,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即將退休的干部保住“晚節”、珍視名譽,同步加強離任(退休)審計。再如,針對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人員貪污賄賂案件更傾向于多人作案(56.87%),廉政宣傳中可以通過揭示犯罪團伙落網后“內訌”畫面,相互檢舉揭發等案例,削弱基層自治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犯罪的合作可能性,從而抑制和降低農村基層腐敗的窩案、串案發生率。
其三,貪污賄賂犯罪的“大數據畫像”分析,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新時代對腐敗研究的客觀性。客觀世界的貪污賄賂犯罪現象是腐敗研究的主要面向。從知識論角度,實然狀態的感性材料和應然狀態的規范形式共同組成康德所說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2]王春梅、李世平:《實然、應然、本然》,載《人文雜志》2007年第3期。腐敗犯罪測量等“實然”研究既為貪污賄賂犯罪相關的犯罪原因研究、刑事政策研究、刑法規范研究、黨內法規研究等解釋性、對策性、規范性研究提供了研究問題和案例素材,同時也是各種“應然”研究有效性、客觀性的“試金石”。在廉政學(或監察學)的“學術大廈”知識體系中,腐敗測量研究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更是起到學科“地基”作用。“腐敗測量是人們認識腐敗的重要手段”,盡管腐敗行為具有隱蔽性和敏感性,但是在掌握科學方法的前提下,腐敗現象可以被真實、科學的測量。[3]過勇、宋偉:《腐敗測量:基于腐敗、反腐敗與風險的視角》,載《公共行政評論》2016年第3期。近年來,司法公開帶來的貪污賄賂犯罪“算據”的增加,大數據分析關鍵技術突破帶來的“算法”的增多,以及“摩爾定律”科技革新帶來的計算機、服務器“算力”的增強,為貪污賄賂犯罪“大數據畫像”提供了相對充分的算據、算法、算力支持,使之可以成為犯罪實證研究相對成熟的全新路徑。與此前的小樣本研究或抽樣研究相比,貪污賄賂犯罪“大數據畫像”客觀性更強,能夠及時、全面、客觀地反映犯罪現象。“十八大”以來,與“全面從嚴治黨”的中央決心、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國家戰略、民眾反腐參與的高漲熱情不成正比的是,我國相關的廉政研究中心和“智庫”機構對腐敗測量研究仍然缺乏足夠的重視。2013年以來腐敗測量研究數量雖有所提升,但與“應然”的規范性研究相比,貪污賄賂犯罪的“實然”研究在數量、質量、連續性、系統性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實證研究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關學科的發展。希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也期冀在中國犯罪學會、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等學會的倡導下,貪污賄賂犯罪現象研究能屢出佳作,揭示更多隱藏在腐敗行為背后的規律性特征,更好地發揮學術研究對懲治和預防腐敗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