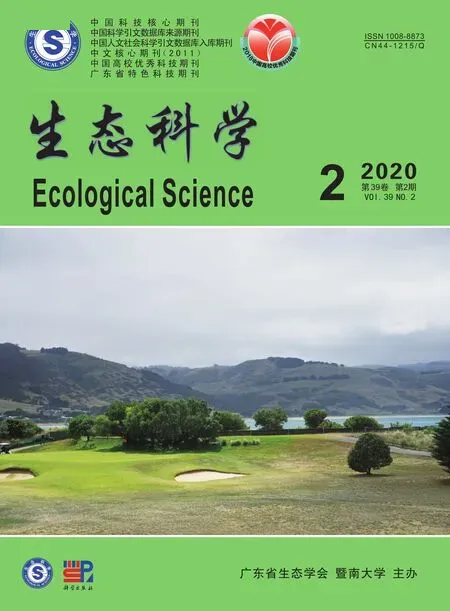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分析及模擬預測
賀清云, 李慧平, 歐陽曉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分析及模擬預測
賀清云, 李慧平, 歐陽曉*
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 長沙 410081
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的特征為城市群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參考。以長江中游城市群28 個城市為研究對象, 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定量分析2006—2017年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的時空演變規律, 同時運用LSTM深度學習模型預測2018—2022年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城市群—城市”的多重視角下,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其中, 長沙、武漢、南昌3 個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具有帶動性作用;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格局形成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個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多中心空間結構。空間格局表現出空間異質性, 尚未形成一體化的耦合協調空間格局; 預測結果表明2018—2022年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整體有所提升, 但整體提升速度較慢; 大部分城市耦合協調度延續了增長的趨勢, 升級為初級以上的協調發展等級。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 耦合協調; 深度學習; 長江中游城市群
0 前言
城市化發展需要生態環境要素提供支撐, 并對生態系統造成深刻的變化[1], 可能導致生態環境質量的下降[2]。其中, 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被認為是生態環境質量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 具有重大的生態風險[3], 如何提高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4]。長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國重點建設的國家級城市群, 其快速的城市化發展導致城市無序開發、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等“城市病”日趨加重, 針對城市群的生態環境問題, 國家提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應該把握城市發展新規律, 探索適合城市群的新型城鎮化模式。因此, 基于耦合協調發展視角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二元關系也勢在必行。
目前, 國內外對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①有關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的理論研究, 基于城市化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復雜線性關系, 方創琳等學者構建“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塊—多智能體”集成的時空耦合動力學模型的理論框架[5]。②生態環境對城市化的響應關系研究, 如運用回歸分析模型[6]、斯皮爾曼模型[7–8]等相關性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城市化過程中整個生態環境系統或分項的生態服務價值變化規律。③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主要是從測度分析[9–12]、變化規律[13–14]、機制研究[5,15]等不同角度對二元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進行了綜合分析, 研究多采用模糊物元模型[16]、耦合協調度模型[17–18]、熵變方程模型[19]等方法對二元之間的耦合規律性進行探討[18–21]。隨著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研究的不斷深入, 研究體系已經逐漸較為完善,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①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時序上的變化研究, 其空間演化研究較少; ②缺乏對研究區未來年份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預測, 通過歷史數據得到的耦合協調度具有滯后性, 不利于“防患于未然”。基于此, 本文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研究對象, 采用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模型和空間相關分析模型, 對2006—2017年協調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 為城市群實現一體化建設提供理論指導。同時利用深度學習LSTM模型預測未來5 年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 探討其發展趨勢并提出提升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對策措施, 為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和參考。
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國家特大型城市群之一, 包括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以及環鄱陽湖城市群三大子城市群(如圖1)。2017年, 長江中游城市群面積為32.61 萬平方公里, 總人口1.25 億人; 經濟綜合實力初見成效, GDP總額達到7.9 萬億, 位居全國城市群中的第五位; 城市化發展速度較快, 城市化水平為59%, 高出全國2.5 個百分點。本文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其中仙桃市、潛江市、天門市三個屬于湖北省的副地級市, 為了對比的合理性, 研究對象去掉了這三個城市)。數據來自2007—201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統計年鑒和相關地市統計年鑒。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內涵分析及其指標體系構建
城市化是多要素組合而成的綜合整體[22–24], 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是城市化最主要的構成要素, 為了更好的量化城市化水平, 本文將從人口城市化、空間城市化、經濟城市化以及社會城市化四個方面表征城市化。人口集聚、城市擴張等城市化發展過程中, 時刻從生態環境系統獲取能量、物質等, 從而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間客觀存在相互作用關系。人口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表現為一方面人口快速集聚到城市, 造成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 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 另一方面人口的需求水平的提高, 將進一步激化人口與環境供給的矛盾, 增加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壓力。經濟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表現為一方面經濟發展需要消耗生態環境系統中的自然資源, 同時產生污染物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 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 將提高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 減少環境污染。空間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表現為城市擴張對土地利用類型進行改變, 導致生態環境質量的下降, 同時空間城市化衍生出來的交通、地產等建設給城市帶來了噪聲、空氣等污染。社會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表現為通過教育、創新等途徑提高生產和生活中節約和集約的理念和方式, 從本質上提高生態環境建設效率。

圖1 研究區域和范圍
Figure 1 Study area and scope
采用指標評價法來評價區域的城市化以及生態環境發展狀況, 需嚴格按照指標篩選的基本原則: ①科學性原則。城市化和生態環境是由多要素組成的綜合復雜整體, 要求選取的指標能夠準確具體的反映研究對象的內涵和特征; ②獨立性原則。選取的指標要盡量避免所反映的信息存在重疊的現象, 保證指標的相對獨立性; ③可行性原則。確保指標體系所需數據便于搜集, 易于理解且具有可比性和可預測性; ④系統性和全面性原則。指標體系需全面系統的涵蓋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各個層面, 綜合反映系統的全貌, 同時也要考慮各組成要素的系統性[25–27]。因此, 根據指標選取的有關原則, 基于對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內涵分析, 結合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長江中游城市群, 同時參照相關研究成果[ 27–29], 構建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兩大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客觀的熵值法計算權重,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觀賦權的局限性, 具體處理過程如下。在獲取原始數據后, 由于各指標的綱量、數量級及指標的正負向取向存在一定的差異, 需要對正負趨向性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具體步驟如下公式(1)和公式(2)所示:


根據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 第項指標的熵值(e)按照公式(4)計算, 第項指標的權重(w)按公式(6)計算。其中為指標數,為評價年數。




根據以上公式處理確定城市化指標體系和生態環境指標體系中基礎指標的權重, 處理結果如表1。
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進行指標標準化, 根據熵值法求得各指標的權重, 采用綜合分析模型, 得到城市化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 再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進行計算[14,22]。

(8)
(9)
其中,別表示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表示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所占和份額下的綜合協調數, 其中+=1, 由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在耦合協調過程中作用相同, 故設定=0.5[26–27]。借鑒喬標[9]、劉耀彬[18]對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的標準, 根據的大小, 對耦合協調類型進行等級劃分, 0<≤0.50屬于失調衰退類; 0.50<≤0.59屬于勉強協調發展類; 0.60<≤0.69初級協調發展類; 0.70<≤0.79中級協調發展類; 0.80<≤0.89良好協調發展類; 0.90<≤1.00高度協調發展類。
2.3 耦合協調度空間自相關模型
本文選取空間自相關模型來檢驗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發展是否沖破行政區劃的壁壘, 形成城市間的空間交互作用。其中, Moran’s表示全局空間相關, 公式為[28–31]:

表1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4 耦合協調度預測模型
深度學習具有3 層網絡結構, 包括輸入層、隱藏層和輸出層, 根據輸入的信號特征, 通過網絡訓練和預測的算法, 能夠挖掘信號潛在的發展規律。隨著深度學習的應用越來越廣泛, 部分模型被于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和預測。其中, LSTM模型在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和預測中能夠提高預測的精度, 適合處理和預測時間序列中間間隔和延遲非常長的重要事件[32]。然而, LSTM模型的應用非常有限, 特別是對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間序列預測這一研究問題, 目前還未發現相關研究。本文選擇城市化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作為實驗對象, 以預測誤差最小為目標, 并設定訓練集和驗證集的比例為6:4(2006—2013年168 個數據點作為訓練集, 2014— 2017年112 個數據點作為驗證集), 提出了一種基于LSTM循環神經網絡的耦合協調度預測方法。
本文采用平均絕對百分誤差()評價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 計算公式如下。

3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時空變化特征
3.1 耦合協調度的時間維度變化特征
利用前文構建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模型, 計算長江中游城市群28 個地級市2006—2017年的耦合協調度, 結果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看出, 城市群視角下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由2006年的0.612增加到2017年的0.678, 呈現波動上升趨勢, 增長速度緩慢, 一直處于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6—2017年, 長江中游城市群處于城市群發展0初期[33], 城市群的發展容易受國內外經濟環境影響, 期間2008年城市群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國內自然災害的短暫影響, 城市化質量與生態環境質量都有所下降; 2013年受國家經濟處于調整和國際金融環境不景氣等因素的影響, 城市群的城市化發展受到阻礙, 生態環境在生態文明理念的背景下各方合力推動其保持上升的態勢。2008年和2013年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有所下降, 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 城市化發展迅速做出調整, 耦合協調發展也相應的發生轉變, 恢復其增長趨勢。與路娟等學者提出的長江經濟帶中游地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度不斷上升的觀點吻合[34–35]。
從圖3可以看出, 2006—2017年, 城市視角下大部分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演化趨勢較為穩定, 長沙、武漢和南昌的耦合協調曲線發展趨勢基本一致, 并且與整個城市群的曲線發展趨勢相似, 表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具有中心城市帶動作用。其他城市的曲線基本為波浪形且上升趨勢明顯, 初級協調發展的城市有所增加, 黃石、荊門、孝感、咸寧、益陽、景德鎮、宜春、撫州紛紛從勉強協調發展加入了初級協調發展行列; 只有婁底的曲線為波浪形且下降趨勢, 婁底作為城市群內具有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 依靠資源發展城市, 導致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同時, 由于資源的枯竭制約城市化的發展, 其耦合協調度處于下降趨勢。針對城市視角的協調度發展趨勢, 梁龍武等學者在對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時空分異研究中也指出, 京津兩市的協調水平為中度協調以上水平, 高于城市群內其他地區, 且各地市存在不同的變化趨勢[36]。
3.2 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維度變化特征
在GeoDa平臺中計算出2006—2017年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Moran’s值, 如表2所示, Moran’s值為負值, 說明耦合協調度具有空間異質性, 其中由于值大于0.1, 表現出空間差異不顯著, 但城市群仍尚未形成一體化的空間格局, 研究區域內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較高的城市周邊是耦合協調度較低的城市。且2006—2017年期間, Moran’s值并沒有顯著的下降趨勢, 表明城市群內這種空間差異沒有縮小。

圖2 城市群視角下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演化
Figure 2 Time series chart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圖3 城市視角下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差異演化
Figure 3 The different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表2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全局空間自相關結果
為了更加直觀的分析市域視角的耦合協調發展空間差異特征, 本文選取2006年和2017年2 個作為代表年份分別作出相應的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情況, 如圖4。整體上看,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形成以武漢、長沙、南昌為核心的多中心空間結構, 且研究期間多中心空間結構基本上處于穩定的狀態。從圖4(a)可以看出, 2006年城市群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格局以武漢、長沙、南昌為核心, 而勉強協調等級的城市圍繞在武漢、長沙、南昌的周邊, 形成多個“核心—邊緣”的空間格局。而處于初級協調等級的城市則分布較為分散。從圖4(b)可以看出, 2017年城市群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格局, 較“十一五”開局(2006年)均衡性上有較大提高。但仍然以武漢、長沙、南昌為核心, 周邊勉強協調發展等級的城市大部分升級為初級協調發展等級, 初級協調發展等級的城市個數增加并趨于連續的塊狀分布。從三大子城市群的層面可以看出, 武漢、宜昌、襄陽3 個城市在武漢城市群內耦合協調度等級較高, 與湖北省“一主(武漢)兩副(宜昌、襄陽)”的空間發展一致; 長沙、株洲、湘潭3 個城市在環長株潭城市群內耦合協調度等級較高, 與湖南省“一核(長株潭城市群)三極(岳陽、郴州、懷化)”的空間發展一致; 南昌和九江2 個城市在環鄱陽湖城市群內耦合協調等級較高, 與江西省的“昌九走廊”的空間發展一致。
3.3 基于深度學習的耦合協調度發展預測分析
利用LSTM模型進行模型訓練和驗證, 城市化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的訓練精度與訓練次數關系, 如圖5。LSTM模型訓練精度與神經元數關系存在最優值, 訓練次數達到200 次后精度達到平穩不再顯著提高。根據訓練得到的最優LSTM時間預測模型進行時間數據預測, 運用公式(7)計算, 精度達到94.2%和94.5%, 證明模型預測精度達到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間序列預測的要求。
在Tensorflow平臺上預測2018—2022年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 結果如表3所示。2018—2022年耦合協調度將延續前12 年的發展趨勢, 整體水平將繼續提高到0.686, 與城市群未來發展基本符合, 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和“生態文明”的戰略持續實施, 耦合協調發展整體將保持上升的趨勢。相比于2017年, 宜昌、株洲、湘潭、九江、上饒由初級協調上升到中級協調; 鄂州、萍鄉、新余由勉強協調上升到初級協調; 婁底和鷹潭仍處于勉強協調。

圖4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格局演變
Figure 4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圖5 LSTM訓練誤差和訓練次數關系圖
Figure 5 The relation diagram of LSTM training error and training times

表3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預測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論
基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內涵分析, 構建符合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模型, 從“城市群—城市”多重視角對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進行分析, 得出如下結論:
(1)2006—2017年,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波動上升趨勢, 上升速度較為緩慢。其中, 長沙、武漢、南昌3 個中心城市在城市群耦合協調發展中起到主要的帶動作用, 呈現出中心城市帶動型特征。
(2)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空間格局存在區域差異性, 具有空間異質性。耦合協調發展空間格局形成了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個城市為核心的多中心空間結構。以三大子城市群的視角分析, 較高耦合協調度等級城市空間格局基本符合湖北、湖南以及江西省的空間發展規劃。
(3)將LSTM深度學習模型運用到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預測。預測結果顯示, 2018—2022年, 28 個地級市中只有鷹潭和婁底未達到初級協調發展水平, 其他城市均達到初級協調發展水平或更高層次的水平, 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整體表現出增長的趨勢, 但是增長速度較慢, 區域差異明顯。該結果證明基于LSTM模型用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間序列預測, 與城市群的實際情況非常吻合, 能夠達到較好的精度。
4.2 政策建議
基于長江中游城市群處于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初級協調階段這一現狀, 根據 “兩型社會”和“生態文明”的建設要求, 對如何實現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化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1)28 個城市需要根據各自城市發展特征, 采取差異性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路徑: 生態環境滯后型的城市需要嚴格控制建設用地規模, 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水平, 降低污染排放, 避免原有生態系統的破壞, 比如降低重工業的污染排放, 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 城市化滯后型的城市需要在保證區域生態環境安全的前提下, 通過建立綠色基礎設施和完善現代化的城市功能, 從人口、經濟、社會和空間四個層面全面開拓高質量城市化發展的道路。
(2)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整體表現出增長的趨勢, 但是增長速度較慢。城市群要依托長江“黃金水道”的優勢, 充分利用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兩型社會”建設的區域政策導向, 逐步調整城市群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產業結構, 做強裝備制造業等產業, 進一步完善現代物流、港口物流、金融業等服務配套產業, 穩步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和有關的政策支持, 推動企業污染減排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以創新驅動城市群城市化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
(3)耦合協調發展空間形成了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個城市為核心的多中心空間結構, 但是區域差異明顯。耦合協調度較低的地區要充分考慮自身發展特點, 在突出本區域優勢的前提下, 進一步借鑒學習武漢、長沙、南昌三市發展模式, 積極融入城市群協同發展。同時, 要從城市群的視角出發, 以行政力量破除區域聯合發展障礙, 達成區域城市化水平協同高質量提升、生態環境聯合治理保護的共識, 創建城市群協同發展機制, 逐步縮小區域間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的差異。
[1] GRIMM N B, FAETH S H, OLUBIEWSKI N E, et al. Global change and the ecology of cities[J]. Science, 2008, 319(5864): 756–760.
[2] TRATALOS J, FULLER R A, WARREN P H, et al. Urban form biodiversity potenti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2007, 83(4): 308–317.
[3] REES W, WACKERNAGEL M. 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s: why cities cannot be sustainable—and why they are a key to sustainability[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8, 16(4/6): 223–248.
[4] 王振波, 方創琳, 王婧. 1991年以來長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區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評價及其空間演化模式[J]. 地理學報, 2011, 66(12): 1657–1668.
[5] 方創琳, 周成虎, 顧朝林, 等. 特大城市群地區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效應解析的理論框架及技術路徑[J]. 地理學報, 2016 ,71(4): 531–550.
[6] 鄧宗兵, 宗樹偉, 蘇聰文, 等. 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及動力因素研究[J].經濟地理, 2019, 39(10): 78–86.
[7] 郭慶賓, 劉靜, 王濤. 武漢城市圈城鎮化生態環境響應的時空演變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2): 137–143.
[8] Li Baojie, Chen Dongxiang, Wu Shaohua, et al. Spatio- temporal assessment of urbanization impacts on ecosystem services: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6, 71: 416–427.
[9] Lyu Rongfang, Zhang Jianming, Xu Mengqun, et al.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ir temporal relations: A case study in Northern Ningxia,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18, 77: 163–173.
[10] 喬標, 方創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動態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區的應用[J]. 生態學報, 2005, 25(11): 3003–3009.
[11] 孫平軍. 1994–2011年江蘇省城市化與生態環境非協調性耦合關系的判別[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4, 23(8): 1051–1056.
[12] 胡振鵬, 黃曉杏, 傅春, 等. 環鄱陽湖地區旅游產業—城鎮化—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定量比較及演化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5, 24(12): 2012–2020.
[13] 李強, 韋薇. 長江經濟帶經濟增長質量與生態環境優化耦合協調度研究[J]. 軟科學, 2019, 33(5): 117–122.
[14] 崔學剛, 方創琳, 劉海猛, 等.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動態模擬理論及方法的研究進展[J]. 地理學報, 2019, 74(6): 1079–1096.
[15] 胡彪, 張旭東, 程達, 等. 京津冀地區城市化效率與生態效率時空耦合關系研究[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17, 31(8): 56–62.
[16] 王新杰,薛東前. 西安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模式演化分析[J]. 自然資源學報, 2009, 24(8): 1378–1385.
[17] 郭月婷, 徐建剛. 基于模糊物元的淮河流域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協調測度[J]. 應用生態學報, 2013, 24(5): 1244–1252.
[18] 劉耀彬, 宋學鋒.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模式及判別[J]. 地理科學, 2005(4): 26–32.
[19] 閆璐璐, 王小梅, 柴彥威, 等. 基于熵變視角的生態脆弱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發展研究——以西寧市為例[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S2): 39–43
[20] 段維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機制與規律性分析[J].環境與發展, 2017, 29(10): 185–190.
[21] 黃金川, 方創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機制與規律性分析[J]. 地理研究, 2003(2): 211–220.
[22] 劉巧婧, 王莉紅.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研究——以杭州市為例[J]. 環境科學學報, 2018, 38(10): 4214– 4222
[23] 姜磊, 周海峰, 柏玲. 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城市—社會—環境耦合度空間差異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7, 26(5): 649–656.
[24] 劉艷軍, 劉德剛, 付占輝, 等. 哈大巨型城市帶空間開發—經濟發展—環境演變的耦合分異機制[J]. 地理科學, 2018, 38(5): 662–671.
[25] 王秀明, 張勇, 奚蓉, 等. 廣東省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的空間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J]. 中國環境管理, 2019, 11(3): 100–106.
[26] 陳肖飛, 郭建峰, 姚士謀. 長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鎮化與生態環境承載力耦合協調研究: 基于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觀思想[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8, 27(4): 715– 724.
[27] 陳曉紅, 吳廣斌, 萬魯河. 基于BP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脆弱性與協調性動態模擬研究——以黑龍江省東部煤電化基地為例[J]. 地理科學, 2014, 34(11): 1337–1343.
[28] 方創琳, 鮑超. 黑河流域水—生態—經濟發展耦合模型及應用[J]. 地理學報, 2004, 59(5): 781–790.
[29] 高楠, 馬耀峰, 李天順,等.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產業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研究——以西安市為例[J]. 旅游學刊, 2013, 28(1): 62–68.
[30] 王毅, 丁正山, 余茂軍, 等. 基于耦合模型的現代服務業與城市化協調關系量化分析——以江蘇省常熟市為例[J]. 地理研究, 2015, 34(1): 97–108.
[31] 劉彥彤,趙爽. 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研究[J]. 江蘇農業科學, 2019, 47(17): 330–333.
[32] HOCHREITER S, SCHMIDHUBER J. Long short-term memory[J]. Neural Computation, 1997, 9(8): 1735–1780.
[33] 路娟, 張勇. 長江經濟帶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特征及時空演化規律研究[J].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45(4): 85–93.
[34] 謝志祥, 任世鑫, 李陽, 等.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效率水平測度及空間分異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15, 24(10): 1705–1710.
[35] 郭慶賓, 張中華. 長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時空演變[J]. 地理學報, 2017, 72(10): 1746–1761.
[36] 梁龍武, 王振波, 方創琳, 等.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時空分異及協同發展格局[J]. 生態學報, 2019, 39(4): 1212–1225.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HE Qingyun, LI Huiping, OUYANG Xiao*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Researc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thesis, taking twenty-eight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ime evolvement rules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2006 to 2017 and then aims to predict its trend in 2018-2022 on a basi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presents an upward fluctuating trend, among which these three cities : Wuhan, Changsha and Nanchang play a leading role with a multi-centers spati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them. Nevertheless, this spatial pattern has not yet been an integrated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one, manifesti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predic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ill have been integrally improved but with a slow speed in 2018-2022, and most of the cities will keep an upward trend, upgrading to primary degree of coordin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deep learn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0.14108/j.cnki.1008-8873.2020.02.022
X22; F290
A
1008-8873(2020)02-182-09
2019-09-17;
2019-11-1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8ZDA040)
賀清云(1955—)女, 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為城鄉規劃與區域發展
歐陽曉(1991—)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發展, E-mail: 1075090536@qq.com
賀清云, 李慧平, 歐陽曉.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分析及模擬預測[J]. 生態科學, 2020, 39(2): 182–190.
PHE Qingyun, LI Huiping, OUYANG Xiao.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J]. Ecological Science, 2020, 39(2): 182–190.